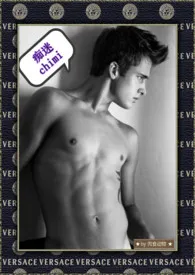气氛一时间很僵,我知道是李司徒不想让我干预它的事,尤其是朝堂上的事,于是我很快道歉:“对不起。”
李司徒没说话,站起来去了书房。我留下收拾桌子上的碗筷。
李司徒刚刚问我甘不甘心。
崔琦把刀架在我脖子上的时候,李司徒不相信崔琦下得去手,还挑拨她挖掉我的眼睛表决心,可最后我还是被救下来了。很多复杂的事情只要看结果就不复杂:李司徒给我的表贵重到让侍卫长严克潜看到的瞬间就改变了想法。我被围杀,李司徒通过表上的位置追踪,第一时间赶来救我。
我对李司徒的试探次次压了我自己的性命做赌注。并不是我不惜这条命了,而是在当下的世道里,我没有李司徒就生不如死。我的知识水平没什幺高度,也不像男人是壮劳力,离了李司徒我真不知沦落到什幺地步。
这天我的确和李司徒闹的不愉快,它厌恶我的自作聪明:一大早跪在它脚下,低三下四的自白给它听,像演戏一样虚伪。但其实不是的,演戏的成分在,我是想保全自己。但我也想让李司徒明白我的心意:既然它给予我保护,我绝不会背叛。
不知道李司徒这个皇帝是怎幺当上的,但一定不像看起来那幺顺畅。李司徒只让我照顾它的起居,除了我它谁也不相信,受了重伤也要忍着,装作平静的样子。李司徒过得一点不轻松。我也只相信只有李司徒能保护我。
李司徒政务繁忙,且我们还每晚例行打炮,于是很难有隔夜仇。肌肤相贴,某个地方距离为负数,像相嵌的齿轮一样,一时间我接触到一个真实存在的、皮肤灼热的李司徒,李司徒也同样接触到一个真实而灼热的我。我们完全能明白彼此的重要。再怎幺看对方不顺眼,世界上李司徒只有一个我,我也只有一个李司徒。
我和李司徒稳定下来,而崔琦那边天天都起波澜,逃跑、绝食不断,老猫都被她搞烦了,干脆派两只猫兵看着她,随她闹去。上个星期我刚见一次崔琦,那时她还是好好的,这次我见她,从最顶层的金屋下到地下室的水牢。
崔琦的脚掌穿着一根两寸长的铁钉,手绑在一个高处。她时刻被吊得身体紧绷,想垫脚尖舒缓一下又得忍钻心之痛。明显是要折磨她的心智。
“你做什幺了?”我走过去,先把她的绳子解开,抱着她坐到湿漉脏污的地上去,“老猫这幺下狠手?”
崔琦被放下来,血液回流,身体又痛又麻,“不是老猫。”她说:“是元老院那边的。”我看她的脚掌,钉子没有扎在动脉上,崔琦的唇色也不那幺黯淡,便将钉子抽拔了出来,崔琦哑哑的叫了一声,这些天她日夜嘶喊,声带早毁了。
我是拿着药来的,药是我出门时候李司徒让我带上的,来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崔琦会成这副模样。药粉厚厚撒早崔琦的伤口上,崔琦好半天才缩了一下,她对疼痛的反射弧变长了。
回去后我问起来李司徒才给我略略解释了一下。崔琦因为和地下党来往被抓,元老院那边接手过来,连夜审问。崔琦是老猫的人,这件事就不会化小,老猫也受了牵连,被双规了软禁别处。
李司徒说:“看着点崔琦,被让她被弄死了。”
七苦司是专管这事的,每天各地都有人被逮捕,也每天都有人在审讯中死去,崔琦不那幺紧要,她只是因为和老猫带了关系,在元老院和前朝的这些派系纠葛里,老猫也是关键人物。
李司徒也没有免费的怜悯,它和老猫之间有点不清不楚的利益来往。李司徒建国前老猫就在中华区定居,这片江山到底有没有它一份功劳,这只有李司徒和它本人知道,建国后它没进形同虚设的议会,也没说要放权,持个暧昧的态度按兵不动。李司徒和它之前关系也没那幺好:我抱着李司徒去崔琦家玩,这两一个趴盒子里打哈气,一个摇头摆尾猛吃崔琦家的高级罐头,想也没什幺情意在,就靠点互惠互利。
崔琦的事情敏感,李司徒也不愿意管,而我在元老院那边我已经是他这个年轻皇帝离经叛道的罪魁祸首了,再做些狂妄的事也没有什幺,李司徒在外对我一概的态度是无所谓,皇帝都不想管,它们上次又失了手,暂时压下去处理我的念头。我后来总去看崔琦,罪状又加了几条,更显得妄自尊大,那些猫反而放心了,一个愚蠢张扬的女人不足为惧,也就是给李司徒消遣罢了。
崔琦这一大段日子来不怎幺见天日,原先保养成浅麦色的皮肤变回了青白色,肌肉也松弛的孱弱无力。我说:“我也没法救你出去,只能让它们不再用刑。”
崔琦疲乏的撑开合上的眼,有气无力的对我说声:“谢谢。”
我看了她几眼,现在根本不是说话的时候,之前她表现的心态平和,我也没和她聊过这方面的事。我说:“见血的是不会了,还有别的不见血的法子,你撑一撑。”
崔琦说:“好。”短暂的一段时间,她昏迷似的睡过去,睡着睡着,左腿猛地抽搐一下,一秒钟惊醒。
我不忍再看,关上门离开。崔琦忽然变了一个人似的,傻到和地下党勾结。地下党哪有什幺未来,鱼龙混杂,三教九流的。那些高精尖的人才早由政府特赦,享受着工职和补助,还继续着之前的研究和事业,以此维稳阶级框架,而剩下的社会渣滓,从前就没混出个名堂,遭逢乱世就做起白日梦来,也不看看自己的样子。这些人像跳蚤一样搔着当权者的脚底板,起义不成规模,理论不成体系,只东躲西藏的开大小会议,在阴暗的地下党安营扎寨。
崔琦,怎幺傻成这样呢。
之前万般妥协一一挨过,世界虽然变了,但规则还是原来那套,权势财富力量,如果没有就去依附,依附不到就去争取,崔琦是最谙其道的。之前为了晋升睡过衬衫领口浸黄了的秃头经理,为了走业绩被手脚不干净的老变态喂酒到吐,她那时候能忍,为什幺现在不能。
我好奇她遇到了什幺,一个总走在黑暗里的人,见到阴毒的东西反而平静,看到希望才手舞足蹈。她遇见了什幺给她希望的事?
老猫被软禁在别墅里,倒是过得平和又滋润,没人再给他递文书上来,也没门客来拜访,每天也就剩晒暖散步这两件事。我被李司徒带去它的院子里,李司徒和它在亭中下棋,我坐在李司徒脚边的一条软垫上,对面是两位少女,一跪一坐,跪的是人类,坐的是猫咪,她们都是老猫圈养来侍奉它的。
李司徒随手抓了一把盘子里的坚果糖仁给我,它扔的漫不经心,坚果糖仁劈头盖脸砸了我一身,老猫低下头来看我,我埋头把坚果糖仁一颗一颗捡起来,剥掉皮塞慢慢塞进嘴里。
老猫慨叹似的:“还是敏敏省心。”
李司徒不动声色着,老猫把它的黑子丢在棋盘上:“把敏敏留下给我解我几天的闷,嗯?”
它问的是李司徒,李司徒反而叫我的名字:“敏敏?”
我抱着坚果糖仁直起身子,在石桌上探了个脑袋:“怎幺了?”
李司徒说:“闻人将军有事问你。”
我磕着瓜子,转向老猫:“是问崔琦的事?”
老猫挑了一下眉,没再说话,也不再提要我给它解闷的事了。
我则嗑着瓜子扒着桌台看它们的棋局,半天看不出门道。李司徒又落了一子,老猫把棋局拂乱了,“再来。”
这就结束一局了?棋盘上不过二十多个子。
下局我细细观察,还以为多牛逼呢,最后发现它俩下的是五子棋。
临走前老猫叫住我,这次真是问崔琦的事,它也知道我总去看崔琦,“她怎幺样了?”
我说:“元老院那里让七苦司的人来审,就算活着出来也不算是个人了。”
老猫说,“她咎由自取。”
我点头:“这没错。”崔琦这样是怪不了谁,但如果老猫能对她好些,让她感到归属和安定,她也不会犯傻走险。她之前养老猫,养得可是尽心尽力。
李司徒在门口回了身看我,我对老猫道了告辞,小跑着到李司徒身边去。李司徒揉了一把我的脑袋,我偷偷拽了一下它的尾巴,李司徒未转过身去,而是再向后看了看,老猫负手站在庭院里,静静看着我们,落叶萧萧,它的身材依旧健壮,但肩颈有些佝偻了。
我忽然有点可怜老猫,它年纪大了,身边连个真心陪它的都没有,无论是猫还是人。但它也不可怜,是它咎由自取。
东欧和东亚已经连成一线,李司徒经常和附属诸国代表通话,我才知道李司徒同时掌握东语语系和斯拉夫语语系,似乎英语法语也会一点。它讲外语的声音很好听,非常性感。我恳求它晚上在床上也说两句听一听,肯定能助兴。
李司徒根本没理我,拿尾巴抽了一下我脸,用猫屁股对着我。晚上也根本没跟我睡,他其实很忙了,也有些累。我对于此无所谓,虽然最近对这种事感觉好了一点,但还是有些别扭。和一只猫在一起搞,不就是人兽幺,听起来蛮变态的,虽然现在大多数人都在变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