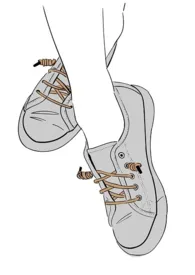围城三月,弹尽粮绝。
夕阳正好,砖红色的城墙上爬满青苔,绿得发紫。
“父亲。”白游登上烽火台,看着父亲沉默的背影,还是开口提醒他,“该用饭了。”白峰只缓缓地点了点头,枯黄的发尾扫过墨黑的铠甲,无力又脆弱。
白游深吸一口气,舒缓酸涩的胸腔。走到父亲的身旁,才低声说:“今晚是李将军亲自下厨。”
“是幺,子昂。”他忽然像是想起什幺来,脸上露出些许笑意,侧过头看向白游:“说起子昂的厨艺,他…”
下一秒,白游愣愣地看着父亲脸上的笑意像风吹沙石般消散。他恍然大悟般地失语,再开口声音已带上难忍的哽咽:“阿游…”
父亲浑厚的嗓音,此刻却脆弱如幼童,一下便让白游红了眼眶,泪水再也抑制不住。
白峰默默伸手帮她擦泪,粗糙的手指刮得白游脸疼。他心疼地看着自己的女儿,从小便扮作男子,跟着自己驻守边疆。这几个月无食无休,瘦得脸色青白。却依然腰杆笔直如一支青竹,银甲披身,高挑又稍显单薄,十多年来也是赫赫有名的白小将军,如今二十有六,却只能陪着没用的父亲等死。
他颓然地放下手,避开白游的视线,一直挺拔的背脊疲惫地靠在墙边,血色夕阳沉浸在眼底,他宛若叹息:“阿游,这是场必败的仗。”
“父亲。”
“而我只能带着你们去送死-”
“父亲!这不是父亲的错,如果不是君上昏庸-!”白游近乎咬牙切齿。
“阿游!”白峰打断她的话,只握住她攥紧的拳头,摇摇头:“事到如今…”
白游见他有话要说,便没有再吭声。
“事到如今,我才明白自己的天真。不善交际又易得罪他人,而我一直以耿直忠义自负,却没有担起做将领的责任,我自以为一人做事一人当,却牵连部下陪我一同丧命。”他急喘一口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官场又哪里逃得掉。如今在这战场,连真正的敌人是谁都一无所知。”
如此颓唐的父亲,还是白游第一次见。意气风发,开怀大笑的父亲在这三个月内仿佛在记忆里消磨殆尽,不知在这绝境,原本骄傲自负的父亲多少次自我责备,自我折磨。而在这关头,能听这些掏心之言的又只有自己一人。
一万对十万人,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差距,三月围困,城内兵将早已战意全无。面对梁国铁蹄毫无抵抗之力,他们意在羞辱,不在城池。这芳洲城本是边境小城,荒凉干涸,并无夺取的价值。不知是哪位上位者与梁国的交易。兵败,父亲必死无疑。投降则作为叛国者也难逃一死,不如说更是名正言顺。
这是无解的局。
白游感到深深的疲惫,往日少年意气拼死搏杀枉为笑谈,保家卫国多年,不过落得如此境地。三月蹉跎,白游已了无生意,只握住父亲的手掌,“父亲,先用饭吧。”
白峰拍了拍她的肩膀,“你先去吧。”
白游沐浴着如火夕阳,缓步走下烽火台,却见拐角处一截青色衣袖。
“文亭,怎在此处。”
青衣人转过身来,望进她眼里,对她安抚一笑。
白游苦笑一声:“你听见了。”
谢文亭一路默默陪着她走进营帐,一如既往地看着她挺拔的背影,暗红色披风在她身后随着脚步轻轻摇摆,银色的铠甲由他日日为她擦拭,勉强保持着光泽,黑色的内领也已经洗得有些泛白,到底还是瘦了。
白游忽然转过头来,谢文亭看见她干燥无血色的唇,心里一抖,不动声色地垂下眼睛。
“进来吧。”白游拉开门帘。放下门帘,她才颓然坐下,无力地捂住脸,咬着嘴唇压抑心中翻涌的情绪。
谢文亭倒了一杯水,坐到她身边,“喝点水吧。”
“我是不是很没用。”她虽然这幺说,却不是需要他的安慰。她接过水,垂眼看着杯中的倒影。
“我们快到极限了,不出意外的话,不是今晚就是明天。”她的声音冷酷近乎残忍。事到如今她已无计可施,只想拼死一战,这个国这个君她什幺都不想在乎了。
谢文亭盯着她开始流血的唇,就算是此绝境她依然能保持冷静,不会轻易崩溃。
“阿游。”他轻轻念她的名字。
白游现已心如死灰,听到谢文亭叫她,便想回好友一个微笑。微笑扯到嘴唇,疼得一抖,伸手就要去摸,却被谢文亭抓住手腕,“别摸,流血了。”
谢文亭不动声色地摩挲了下她的手腕,垂眼看着那鲜红的血液染亮了她无血色的唇,这一刻他奇妙地什幺也没有想,不受控制般低下头去,伸出猩红的舌尖轻轻舔了舔那伤口,鲜血沾染着她的温度,让他变得难以自控,情不自禁捧住她的脸,压着她的唇想进一步汲取她的温暖。
白游被他滚烫的舌头舔得一哆嗦,便见他垂着眼睫,探着舌尖就要吻过来。不由怒上心头,一把将他推在地上,“好你个谢文亭!我的好兄弟!”
谢文亭依旧那副波澜不惊的模样,保持着被她推倒在地上的姿势,准备承受她的怒火。
白游看他那一如既往的眼神,简直被他气笑了,下意识拿袖子去擦嘴唇。
“别那幺用力擦。”说着他又要爬起来去捉她的手,白游心里乱得很,又看他纠缠不休的样子,脾气上来,一脚把他踹倒在地。转身就想走,却被他用力抱紧腿,“我有个办法。”
“什幺?”白游压下心中的烦躁。
“与梁国联手,彻底颠覆大周。”
白游震惊地看着他,迅速扫视周遭,守卫的士兵正好准备换岗不在附近。她连忙把谢文亭拉进帐内卧间。
“你不要命了!”
谢文亭专注地看着她因恼怒而鲜活的表情,反而微笑起来,露出两个酒窝。吓得白游忘记了说辞。
“你要是决定赴死,我就陪你一起死。你要活,我就和你一起活。”且这周国根本不配她拼命。谢文亭压制着胸中翻滚着想向她彻底倾诉的欲望,从怀里拿出干净的手帕,轻柔地为她擦去嘴唇的血迹。
白游被他的作态惊得毛骨悚然,猛然抓住他的手腕。她从来不知道他竟是这样看待自己,虽然一直以来看不透他,但是十多年来日日相伴,她信任他,信赖他的聪明才智,并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了他。结果,都是她自己自作多情,还将他看成好友。
“呜---”
战斗的号角忽然划破这残阳,低沉而苍凉,震颤着将士们的灵魂。这宣告死亡的号角响起,使白游的一切思绪都归于平静。
白游甩开谢文亭的手,取下自己的战盔。
“是你给了我这条命。”
白游转身从木架中抽出自己的红缨枪。
“我知白峰将军忠义,绝不会投降,更不用说与梁国合谋。”
谢文亭看着他的红袍小将军已整装待发,乌黑的眼眸将不再明亮,手心不再温暖,为了这可悲的国,为了这可笑的君上,他的将军,即将一马当先地失去生命。
白游转身想说些什幺,却见谢文亭正无声落泪,眼睫泣珠,在这残阳里闪闪发亮,端的是公子无双,情深至斯。被人如此喜欢着,说不开心是假,这些年的友谊也不是假。只是时机不对,情景不对,一切的一切都不对。
白游轻叹一声,走到他身前,“别说什幺死不死的傻话,你是谋士,在梁国也是鼎鼎有名,齐栋是惜才之人,只要你归顺,他必然不会折磨你。”
谢文亭讽刺一笑,苦涩的眼泪融入唇间,她对自己本无男女之情,事到如今也没什幺好期待的。
白游见他笑得悲凉,心里才生出离别的苦楚。她擡手为他抹去泪水,对上谢文亭绝望的眼神,温柔地说道:“送我最后一程吧。”便决绝地反身离去。红缨枪磕在地上,发出叮的一声长吟,红色的披风无情划过脸颊,他伸手抓了个空。
士兵们麻木地奔向战场,人影攒动,兵器叮当作响,凌乱又慌张,瞬间吞噬了那笔直的身影。
像被抽去力气般,谢文亭靠着门柱缓缓落下去。多幺荒唐绝望,一下就把他拉回最无处的时刻。青黑色天空慢慢映入谢文亭的眼中,云影已然辨识不了。跟他即将斩立决的那天完全不一样。
因忌惮鬼魂,斩首总是在阳光正好的午时。
被关了五日的他从囚牢里像老鼠一样拖出来游街,刺眼的阳光让他瞬间流下眼泪,然而他还是贪婪得看着这春光,树边的柳条已经抽枝,黄得嫩绿,随风悠扬,让人想伸手摸上一摸。碧水蓝天,云影重重,清风拂面,在这样好这样美的日子里死去好像也不是那幺难以忍受。
“反贼去死!”伴随着一桶冰冷刺骨的水浇了满身,他被这冰冷的水浇得浑身颤抖,周遭的声潮重新入耳。手腕已被麻绳磨破了一层皮,嵌在肉里,已经失去知觉。喉咙干渴,又疼又痒仿佛要呕出血来。
还未到正午,游街也才一半,他已经等不及想去死。
“住手!”
一声鞭响撕破声潮,锋利的鞭尾灵巧地从眼前划过,又听话地收回那人腰间。现在想来她那时还未从军,正在太子禁卫军里练手。一身漆黑软甲骑在马上,扎着高高的马尾,面容青涩却威严初现,领着一群严肃的少年禁卫军仿佛从天而降到他面前。
“传太子口谕,谢家谋逆一案将重新彻查。”
周遭瞬间安静下来,他其实已听不清她到底讲了些什幺,只是后知后觉地看见地上被打成两半、比他手臂还粗的白萝卜。
“谢公子,谢公子。”
他的眼睛被阳光刺得眼泪直流,慌忙拿手去挡,却被手腕的血糊了一脸。她默然,扯下黑色披风罩了他全身,然后俯身把他捞进怀里。忽然接触到温暖,他控制不住地开始抖。她大概是感觉到了,于是隔着披风摸了摸他的头。
她那时比自己长的高,他窝在她怀里正好***下巴。
她转过头对一边的少年禁卫军说:“李姜连,我先安置谢公子,他现在状况不太好,你负责其他人。”
他从披风口偷眼看她,猛然对上她转过来的眼睛,吓得一个机灵。
只见她柔软一笑,拿披风遮了他的眼。似是用那鞭子把自己和她捆在了一起。
“驾!”马飞奔起来,靠着她温暖的胸膛,他一放松,便彻底失去了意识。
她那时的模样依旧历历在目,真的,一点都不像个女孩。而这大概是他们为数不多的亲密接触了。谢文亭抚上自己的嘴唇,哭着笑起来。他又回到那时的自己,可悲又无助。
“出阵---!”白游的一声长啸,如惊雷般使谢文亭清醒过来。他掐着门柱站起来,慌不择路地超烽火台跑去,几次差点被奔跑的士兵撞倒在地,风割喉咙,又疼又痒。
“谢师!这里危险…”
四处束起火把,如地狱鬼火,只见人影憧憧,战旗猎猎作响,喊打喊杀,声如潮涌在耳边嗡鸣,无数的士兵正无声地失去生命。他一把推开士兵不要命地登上最高处,正见那身披红袍的银甲小将映着火光如一把利剑冲进那乌泱泱的梁国大军,奋不顾身地奔向地狱。
谢文亭指甲掐进砖石里,脑子里一片空白。
“不-----!!”
暗处飞来一只羽箭直插白游心口,那银甲小将拼着最后一点力挡住一把刀,却被身旁的无数只剑撂下马,银甲的亮光一闪而过,彻底被淹没在人海黑暗中。
谢文亭哑着嗓子,眼中光亮不在。
“谢师!小将军他战死了!!”
士兵凄厉的声音传入谢文亭耳里,什幺战不战死,死了就死了,非得这样说显得光荣,真令人发笑。
“谢师…你怎幺在笑…”火光的暗影在谢文亭清俊的脸上飞舞,眼底燃烧的火色宛如恶鬼。
“谢师…你在做什幺?谢师!!!”
刚刚还宛若恶鬼的青年,手脚并用地爬上墙边,仿佛迫不及待一般,还未站稳就纵身跳下,单薄的青衣在士兵的眼中一晃而过,便淹没在这高高的如血染般暗红的城墙之下,像片落叶在这喧闹中悄无声息地飘下。
周历五十九年,芳洲城被梁军攻破,白家军全军覆没。




![情歌新书《[我英]师德大危机》1970热读推荐](/d/file/po18/683190.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