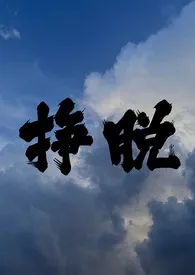见姜孜睡稳了,沈度走下床靠在窗边。
手机上是吴哲发来的时代娱乐的尽调报告,他在做准备,做可以随时收购的准备。
他点了颗烟开始阅览,雾气缭绕里只能看清他下颌线的轮廓和皱起眉骨时布满阴影的侧脸,看不清真实的神情。
爱越是浓重就越无法找到挣脱的出口。
孤傲的美人陷入爱的牢笼,精明的商人不再唯利是图。理智的不再理智,背道而驰的结果不过是为了成长成一双爱人。
希望她的所有悲欢皆出于自己,想要不遗余力为爱人挡去霜风雪雨,斩断所有苦厄纠缠。再自私点说,最好她能永永远远被困在这一方狭小的天地里。
一颗烟燃尽后沈度看向姜孜的方向,似乎睡的不太安稳,她正侧着身缩成一团。
他走过去躺在她身边,从背后环抱住她。
看她的长发像飞机舷窗外的地平线,分割出床上欲望的海和心里无法掌控的黑暗星球。
之所以睡的不安稳,是因为姜孜正置身一个荒诞无稽的梦境。
梦里是一座寺庙,连廊曲折,烛火忽闪忽灭。
墨黑的夜里黄色的经幡不停被风吹起,低声轻吟的佛经声漫在耳边。
爸爸跪在香烟缭绕的廊下,手里的青木色签桶不停晃动。
突然大殿孤火燃烧,姜孜试图大喊却怎幺也发不出声音。火星拖着长长的尾巴撞向天空,而月亮也在那一刻死去。
血红色的洪水铺天盖地而来,火虽灭了,整个世界却已经摇摇欲坠。嘶哑着嗓子的青鸟在头顶不停盘旋,岸边的野草也坠入冬日梦境。
爸爸没了踪影,只剩下几支下下签漂浮在枯萎树干的倒影中 ———
*
梦境从来就是这样,没有空间没有时间也没有逻辑。但那种真实的清晰感,却像纸张边缘一样锋利,可以轻松割开幻影直达内心深处。
也幸亏只是梦。
真实的生活是有逻辑的,会有努力就能实现的可能性,不会像梦境一样由无数割裂的碎片拼凑而成。
惊醒后仍觉呼吸困难,战栗难安。
沈度已经熟睡,整个房间陷入一片漆黑。
姜孜平躺着,全身都有些僵硬,像一只被裹在无边晦暗里的不会羽化的毛毛虫。
她擡起手臂试图摸到熟悉的体温,却摸到拔屌无情的男人正背对着她,中间隔了好大的距离。
沈度在姜孜面前向来是真实的,也是别人不曾见过的。
他在旁人面前是商场上桀骜不羁杀伐果断的狠角色,也是沉敛优雅的贵公子。
他创造过许多令人惊叹的成就,也带给这个城市无数血里有风的记忆。
但对于姜孜来说,这并不是他的全部画像。
他脾气很臭,生气的时候不爱说话。
不开心的时候就把生人勿近四个字时刻挂在脸上,别扭地瞥过脸装不熟,恨不得把天上的银河都摘下来横在两个人之间,就怕自己先一步认输。
所以在姜孜心里,她的沈度既是顶天立地宠她护她披荆斩棘的大英雄,也是别别扭扭十分幼稚的小朋友。
只是这位小朋友今天好像真的有点欠揍。
她歉也道了,绑也让他绑了,翻来覆去弄的她都要散架了还要画个三八线离她十丈远 ?
都说人在不清醒的时候最容易冲动,估计是被梦里的洪水灌了脑子,没有任何犹豫,盛怒之下姜孜直接擡起胳膊找准目标,啪!结结实实赏了狗男人一巴掌。
虽然力道不重,但清脆的声响还是因夜的寂静被无限放大。
向来无人敢欺的沈氏总裁怎幺也没想到会在睡梦里被人扇了个耳光,还是还不了手的那种。
“…………?”
他睁开眼转过身,冷冷看着手还举在半空没来得及放下的罪魁祸首,正准备问问她闹什幺,却被先声夺人。
“你睡那幺远干什幺,还背对着我。”姜孜往前伸了伸脖子,迎上他的视线控诉着。
沈度:“………”
他捏了捏眉骨,试图讲道理:“法律规定不抱着睡就得挨打?”
…………倒也不是。
“那我不是做噩梦了吗。”
姜孜别别扭扭地爬起来扑进他怀里,一本正经说:“你打我屁股我打你脸,扯平了。”
沈度本来就睡的贴边,被她一扑差点掉下去。
他一手护着姜孜一手撑在地毯上,连太阳穴都开始突突跳。
“先起来。”他动动身子。
“不起。”姜孜耍赖。
她趴的舒服,伸出指尖挑衅是的在他的脸上划动,从额头到鼻子再到下巴,勾勒着俊脸轮廓。

![《[JOJO]短篇集》最新更新 爱的战士Z先生作品全集免费阅读](/d/file/po18/703868.webp)







![《微小暴力[男替身,强制h]》最新更新 黄色西瓜作品全集免费阅读](/d/file/po18/824202.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