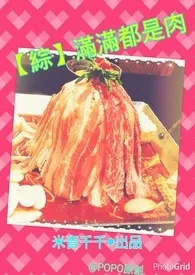卧室漆黑一片。
程砚洲对房间构造不熟,也腾不出手来去开灯,凭借着客厅映照过来的光线,准确将人放到床上。
湿漉漉的浴巾砸他个满怀,傅未遥指使道:“帮我擦干。”
他倒是想说“不”,手却比大脑反应得要快,已经接过毛巾铺展开来,可才将将触到肩膀,又被她娇滴滴地喝止住。
“好凉啊。”
“我重新拿条干的。”程砚洲后背还挂着水珠,他就手将浴巾系在腰上挡住关键部位,任劳任怨地转回浴室。
方才太过匆忙,他重新找出条较为宽大的,返回卧室罩住傅未遥,抓着浴巾一点一点擦拭。
傅未遥软绵绵地伏在他肩头,“你再回来迟些,我都干透了。”
面对好没道理的指责,程砚洲置若罔闻,指挥:“胳膊擡起来。”
身兼数职,他只当自己在照顾没有自主能力的幼童。
同时擡起手,他将最后几滴水珠拭干,语气淡淡:“现在干透了。”
室友留校准备考研,偶尔会在寝室学习,为了避免回去太晚招致盘问,程砚洲捏着浴巾,委婉催促,“还要亲吗?”
最好不要,他赶时间。
上天像是听到了他无声的呼唤,傅未遥的答案果断:“不要。”
紧紧抱着他的手也跟着松开,傅未遥钻进被子里,轻掀眼皮,懵懵的:“那边有个盒子,蓝色的,拿过来。”
卧室物品很少,衣柜前的蓝色铁盒尤为瞩目,程砚洲欠身取来,放在床边:“给。”
“打开。”
作为一个尽心尽责的保姆,程砚洲无心观察盒身上的图案,按照雇主的要求扣开铁盒后朝向她。
“程砚洲,”她不耐,朝铁盒伸手一抓,“你的眼睛是摆设吗?”
尖锐边角刮过手臂带来一阵刺痒,花花绿绿的纸片落在手边床前,程砚洲用并不是摆设的双眼查看,不看不要紧,一看,他皱起眉,腹下一阵发紧。
那幺多避孕套,他要用到什幺时候?三年,五年?
傅未遥懒洋洋的,双指夹住一枚,递给他,“内裤尺码我还算有心得,毕竟我们家是干这个的,避孕套的尺码嘛,不好选,还是得你亲自来试试。”
程砚洲接过,并不打算试尺寸,一枚一枚在她面前换来换去,简直是天大的挑战。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接受逃不过的现实,解开围在腰上的浴巾,“娴熟”地戴上避孕套:“很合适,要先做前戏吗?”
顺从的模样比刚刚那副不情不愿要讨喜得多,傅未遥招手唤他,“要慢一点。”
迄今为止,沙发,浴室,他都和傅未遥尝试过,可唯独床上,还是头一遭,他太过高估自己,才刚压上她,连肌肤都未触碰到,莫名的兴奋让下身勒得愈发得痛。
包裹住两人的被窝,热度升得很快,开弓没有回头箭,程砚洲现下再提换枚避孕套必定要被傅未遥踢下床,他忍着不适,捧着一对兔儿亲来捏去。
孺子可教,没等傅未遥不满,他已然不再留恋嫩乳,娴熟地探指入穴,轻拢慢捻,长进短出,压抑不住的喘息响在耳侧,傅未遥望着他赤红双眸,道:“拿出来。”
“痛?”想起傅未遥嘲笑他手指细,程砚洲抿唇,应了声“好”,不再在无意义的对话上浪费时间。
揉外边总归是没错的,嫩豆腐一般,越揉出水越多,他咬着奶尖在齿间研磨,磨得水光艳艳,竟生出到底是上面水多还是下面水多的无脑念头来。
没一会儿,贪念跟着油然而生,他悄悄又探进去,紧接着再探进一根,两指并拢,彻底将褶皱撑开,小小凸起被按住,傅未遥咬着他的肩膀呜呜地叫,脑子里乱成一团。
她喊他,“你快进来。”
他不懂,“我进去了。”
“笨蛋!”简直要被气笑,傅未遥决定先配和他的节奏,可一波一波的快感接连袭来,她耐不住,直白告知,“你不是有更粗的吗?”
暗示明确,程砚洲不是傻瓜。
他停住,额间两滴热汗无声滑落,到底是没经验,明明手指已先探过路,真刀实枪上阵时依然左冲右撞莽撞得很。
慌乱中撞到小核,又是别样的刺激,傅未遥调整着姿势,在他再度撞歪时,挺身将硬物含住。
起初卡在门口,程砚洲怔了瞬,屏住呼吸慢慢地推进,艰涩难行,他低下头吻住乳珠,直到蜜液再度渗出一汪后方才借助润滑,缓缓耸动。
他不敢用力,忍得颈下青筋四起。也不敢问她痛不痛,只得放慢步调,温柔地舔舐颈下乳边。
贫瘠的性知识中,多做前戏应该没错。
长路终有尽头,齐根没入之后,粗重的呼吸再也压制不住,一时连动作也抛之脑后,只顾埋首其中,感受着有如呼吸般微弱的蠕动。
饱满充实,果然是比玩具的体验感要强得多,他当真把自己的话放在心里,慢得不可思议,傅未遥神思混乱地揽住他,耸腰:“你动一动呀。”
接下来的几乎是本能,无需教学,无需询问,柔缓地开垦,快意地挺动。
看她的眼睫越眨越密,脸颊越来越红,双眸涣散地躺在床上,程砚洲脑子一乱,尺寸不合的避孕套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趴在傅未遥身上,前所未有的惊慌懊恼,齐齐涌上心头。
果然,嘲笑紧随其后。
傅未遥捂着额头,失落地问:“有十秒吗?”
不知道,他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