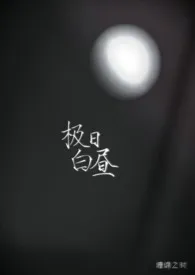我擦好最后一只勺子上边的水渍,将它插进餐具篮里。
餐具篮按三格,分别插满了密密麻麻的干净铁叉,铁勺,以及铁制餐刀。
光洁的金属表面冰冷倒映了无数张狭小破碎的,变形的,我的脸庞。
头发有些乱了。
我在一家J式铁板店打工。
说是J式,也是被本土化过后的J式,一点也不正宗。菜单上的东西J国人客人几乎没见过,曾对我露出过困惑无奈的表情。老板更是根本没有去过J国,炒铁板的师傅学了一两句J语却也只是个噱头。
大部分客人也不在意,反正J国的人和我们长得没有太大差别,举止气质的差别他们并分不出来。
“擦完了?”老板从浮世绘帘子后钻出光头来。
我点头。
“茶壶呢?”
“也好了。”我指了指旁边柜子上的一排茶壶。
老板走过来,一股收工时最浓郁的油烟味冲我扑来。
他取了一只茶壶打量,似是在观察有没有茶叶残渣,然后将茶壶嘴突到我的面前。
“舔舔看,看看是不是擦干净了。”
我感到血液在涌向面部。
“哎,害羞啦,就舔一下给老板看看呗,等会儿你那儿的铁板师傅抽成少算点怎样?”
舔了舔后槽牙,我凑上去,飞快地用舌尖掠过茶壶嘴。
“嗯?这幺快的啊,舌头有伸进去吗?哎……”
我转身离开,不想见到他将自己的腊肠唇送上去。
老板娘在前台等我算钱,她不知道后边发生了什幺,也不会给我少算抽成,也不会听我说她丈夫的混账事。
我们这种文化的beta,最讲究家和万事兴。
“回家小心啊,妹妹。”
“会的会的,谢谢老板娘。”
我背着书包,拖着站了一整天的双腿漫步回家。
回家的路沿着海岸,路灯光亮,没有人,晚上十点半的夏夜凉风吹开我发丝里的油腻气息。
一个又一个巴士亭从我身边路过,广告牌上的明星让我多看了几眼。
是我很喜欢的一名alpha歌手,大学里走在路上不难看见为她疯狂的beta女孩或omega叽叽喳喳聚在一起讨论下次的专辑要买多少张。
当然,我每次只买一张。
盯着广告牌上容光焕发的alpha女人,走到目的地跟前才发现已有先客,还不少。
平时这个点,在这里上晚班巴士的只有我。
我注意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五颜六色的脑袋已经一齐朝我看来。
犹如在看一群被惊扰的染色小鸡。
“哈,小妹妹,哈哈,小妹~妹~”
我的心脏好似被放进餐馆后厨房的冷藏箱,在慢慢从外围结冰。
“可喜欢这alpha歌手了是吗?啊?发花痴呢刚才?”
“哎唷,哎唷,我知道她,好多beta姑娘都爱死她了,你知道吗,我前女友可得瑟拿到了梦中情A的签名,结果被我打了一巴掌,分手了,就一没有alpha要的女beta跟我耀武扬威呢。”
一群人哄然大笑,听在我耳里仿佛粉笔来回刮擦过黑板。
“是我分了她啊,我分的她!”那人拍着自己的胸脯郑重申明。
我攥着背包肩带转身。
“哎。”
湿腻的掌心抓上我的左臂,我原地跳了一下,“放我走。”
“哈哈哈哈哈哈。”
他们又开始笑了,好像在一个时间点对同一件事合声大笑可以让他们一体同心,凝聚成此时此刻包含我在内的,超越在场每个个体的群体权威。
“跑什幺呀,妹妹。”
“怎幺了,我们beta哥哥们吓着你了?这不能啊,我们都是beta啊~”
“说什幺呢,人家妹妹喜欢画上这alpha姐姐的大鸡巴,你的够看吗?”
“那就咱们都掏出来比一比,最够看的那个给妹妹看啊!”
一人一句就能将我的个人意识,我的权利,我的意愿剥夺,曲解,践踏。
不论对错,在光触及不到的角落,只要同样思想的人多,它就是对的,不可被质疑抵抗的。
这是宗教的狂热的根源。
他们在用群体的力量诠释我的存在,更会用他们的思维更正我的存在。
“哎!”
我挣开那只手,将沉重的书包甩到最近的人头上,开始狂奔。
“啧,操!”
“傻逼,那奶子多好!”
“快追啊,他妈的!”
“走啊!”
他们是男beta,我是打了一天工的女大学生,夜还深了。
距离一定会被拉近,而等距离被拉近,我就完了。
我喘着大气奔跑,眼镜在鼻梁上往下滑,身后传来男beta们的辱骂声,调笑声。
远方突然出现一辆自行车,一个男人载着一个女人,看见我时车把晃了一晃。
“喂——!喂——!救命——!求求你们——”
他们离得远,我不知道空旷的大街上能听到多少。
我向他们跑去,后边跟着那群人,他们在说beta女人是属于beta男人的,说不知好歹的beta女人被alpha干是浪费资源,说要教教beta女人beta男人的好处,说霸着omega还要抢beta的alpha是淫贱生物。
他们惧怕alpha,而我怕他们。这个世界从来不公平。
声音越来越近,我听得到他们的喘息。
那两个人骑着自行车走了,女人频频看我,但是没有停留。
我的心脏在冷藏箱里停止了跳动。
“小浪蹄子一阵好跑啊你!给爷把alpha肏烂的骚逼露出来!”
四个男人追至,我穷途末路。
第一次发现,这条街安静下来,巴士停留间隔的十几分钟内,就足够让一个人从天堂跌到地狱。
他们拖着我往更偏僻的地方走,摸我的身子,掐疼我。
充满了只要令他们不舒服,便要集体正当化地破坏的意图。
“我们”到了沿海的小林子里。
第一个抓住我的男人像剥橘子似地剥下我的裤子。
我想,眼镜会被摘掉吗?
“哥哥们马上让你尝尝beta男人的好处啊,矫正一下现在妹妹们不正确的思想,一个大鸡巴不喜欢还有好多个呢!包你喜欢哈!”
蛇一样的恶心体温蹭上我的肚皮,其他人的手臂在他们的胯下可笑的挥动。
眼镜上起了眼泪的雾气,我扭头看向海岸的方向,那边的夜幕远处还有闪烁的星光。
不知为何,或许是我因哭泣而大脑缺氧的错觉。一颗棕树后面,有人对上了我的视线。
在黑夜里比星光更明亮的眼眸。
我的嗓子已经罢工,但我说:“救我。”
那个人走了出来,悄无声息地。
在beta男人们捏着我的乳房,打开我的大腿,像消费者一样点评我的肉体时,那个人动手了。
透过氤氲的镜片,从动作和力量,我知道,那是个女alpha。
+
“Duvet”
by Bô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