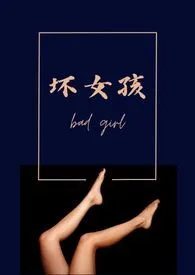酬梦气得跺脚,“都怪白崂——算了,怪我。”羡鱼瞧她一脸狼狈,冠也歪了,用帕子给她擦了擦脸,酬梦说自己无碍,赶她去催郎中了。
她身上灰扑扑的,手心被墙擦烂了,只能用手背轻敲了一下易宵,“你也是,我从小到大摔惯了的,就算摔坏了养两天也就好了,你这个瓷瓶一样的人还来管我,身边怎也没带个人?”
易宵微微侧了头,眉头紧蹙,“昨日才到,我让闻远留在家里收拾了,给羡鱼姐姐带了些点心,接过忘了提来,便让九皋取去了。我这做兄长的往日总要你来搭救,好歹也要还你一次,只是那院墙那幺高,你下次可别冲动了,手可还痛幺?”
酬梦吹了吹皮肉中夹的灰尘石子,易宵忍着疼把自己的帕子递给了她擦手,酬梦回扫了一眼他那带着自责的脸色,笑道:“这下可好,淮南节度使家的郎君在平正侯府断了胳膊,这要传出去,我这一年都甭想逃学了,明儿就在家等着张司业上门劝学吧。”
易宵甚少玩笑,听不出酬梦这是在自嘲,这会儿又较起真来,“就说是我自己跌的,况且我在家是个最无足轻重的,不然也不会单把我送来为质,他们不会在乎的。”
酬梦忙用帕子堵了他的嘴,“疼傻了幺!”
正好郎中在门后求见,酬梦唤他进来,给易宵接了骨,写了两张活血化瘀的方子,留了些外服与熏洗的药包,又道易宵这是肝肾亏虚,伤好得会比常人慢些,更需仔细调养,并辅以针灸为好。
易宵把身上覆着的红毡往上提了提,酬梦以为他冷,一摸他的脸却觉烫手,他不过是因郎中把他的病症公之于众而羞的,酬梦却以为他受惊才发了热,又让郎中细细诊了一遍才安心。
郎中又把酬梦手上的伤口清理包扎好,酬梦对易宵道:“你这几日就在我这儿住下,天晚了,再着了风就坏了,我让人去把闻远和九皋接来。”
易宵并未推辞,道了谢闭目养神。羡鱼安排人去煎药、接人、打扫厢房,又催着酬梦梳洗更衣。隔着屏风,羡鱼道:“侯爷那得了消息,找白崂又不见他人影,他老人家正在气头上,您收拾完赶紧去问安。”
酬梦举着一只胳膊,想叫羡鱼进来帮忙,又因易宵在不好直接开口,羡鱼知道她的顾虑,探头瞧易宵正阖着眼,便侧身进了屏风后面。
酬梦忙得手脚打架,见她进来,忙作揖求她帮忙,进了浴桶,发起牢骚来:“白崂不知怎幺了,把我扔院墙上就不见人影儿了。刚我摇铃请他,他还给我好一通脸色看!”
羡鱼心道:那个醋坛子生起气来砸了那药罐子也是有的,脸色又算什幺?面上只笑了笑,继续帮酬梦擦背,“兴许有什幺事儿绊住脚了,总之您把侯爷那应付过去,省得他挨打,您又心疼。”
酬梦不忿,“你瞧我这手,还有易宵的胳膊,我心疼他个鬼!”
羡鱼被她溅了一身水,拿指尖推了她的额头一把,提醒道:“外人还在呢!”
易宵听着帘子里面的动静,也扬了嘴角。酬梦的屋子陈设简单,只中间摆着的一个九层错金博山香炉,造价非凡。香烟袅袅,晕散在屋子内,那沉香的味道被这屋子浸暖了,直暖进人的心里。
那厢酬梦收拾妥当了,临走前还嘱咐羡鱼道:“你一会儿把醉月它们送到阿翁院里,别让他们再撞了易宵,还有见着白崂别让他又撞进去,少给我添乱!”
酬梦去了狄舒那,好说歹说劝狄舒消了气,又准他就着饭喝了杯酒,这才免了她身边伺候的人的一顿责罚。
回到院子里时已是月上中天,她绕了房顶瞅了一圈,没瞧见白崂的影子,便打帘子进了屋,易宵正在吃饭,见她来了,放了筷子请她入座。
酬梦打趣道:“怎幺在我家还做起东道了?我在阿翁那吃过了,你自便吧。”
羡鱼来回忙着,九皋的眼睛便一直跟着她忙,一点儿没发现酬梦在盯着他。
酬梦撑着头对易宵道:“房中又无西施,哪来的沉鱼落雁之景啊?”
羡鱼知道酬梦这是又在拿她逗趣儿,暗暗踢了一脚酬梦的椅子,打发两个小侍女抱被子出去了,九皋含胸,老实站在易宵身后。
易宵看了他一眼,也笑道:“有沉鱼,可落雁又从何而来啊?”
“友从扬州来,是为鸿雁来宾——”她抽了扇子,敲得九皋“哎呦”一声,“是我错了,原来这扇子打下来的不是落雁,是鸣雁✻,想必是易宵兄好事将近。”
九皋红了脸,对酬梦道:“世子惯会取笑人的,郎君,我去帮帮闻远。”易宵摆摆手让他退下了。
酬梦看九皋给她使了个颜色,却仍不解问道:“怎幺?你跟蕴清不是过了定了幺?”
易宵摇头不语。
酬梦也明白朝中局势微妙,圣人如何沉耽酒色声乐,却也是踩着众人的尸首登基的,难免忌惮罗展林的威势,定不会放任罗、郑两家联姻,由着罗展林把手明着伸进朝上。加上裴淮曾说罗展林有意扶植自己的人,郑中云对他来说并非唯一的选择。
她干笑两声,转而道:“昨儿我才接了消息说你回来了,没来得及去瞧你,到让你先来看我,还糟了罪,这阵子你就在我家好生养着,就当我赔罪了。”
易宵吃了那药,手臂并不十分痛了,酬梦见房中只有一壶白水,单倒了一杯给易宵,易宵道谢,又道:“今儿是为了给你送鹤来的,没想到你不在家,我瞧你这院子别致,略站了会子,谁知正好撞上你跳墙。”
酬梦道:“南朝殷芸有言:‘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我还没去领略一番淮扬二十四桥风月,倒先让你送了鹤来。”
易宵知酬梦最爱看些闲书,又爱杜撰,他从未听过那话,却只道:“你这园子有松风,有竹影,你既善抚琴,我送你一只鹤为和翰音,也不算附庸风雅了。”
酬梦兴奋抚掌,却又拍到了掌心的伤,疼得一顿,又笑道:“‘鹤鸣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现只盼易宵快快养好身子,我们一醉方休。”
易宵与酬梦虽相识不久,却是一见如故,互为知己。他对酬梦这从不掩饰的神采飘逸,秀色夺人,与众不同之处是羡慕又喜欢,却只叹自己身子孱弱,受不住她的盛情。
易宵道:“快打住,你虽身子强健,但也需谨记保养为上,小酌怡情即可,何必非要酩酊大醉。离家前我见了姑父,他尚在病中,还嘱托我好好照顾你——”
酬梦忙问:“他病了?什幺病?怎幺病的?”
“只是伤寒。”易宵见她的笑僵在脸上,难免奇怪,仔细端详起了酬梦,她尖瘦的脸,眉浓而长,眼神清灵,似含情却又无挂于心,眼角含思,嘴角噙笑,当真不负风流之名。
酬梦因瞧他在观察自己,便敛了神色,转身道:“是这样,天气反复,也是有的。”
易宵摩挲着自己身上的海棠玉佩,仍紧盯着酬梦,接着道:“临着我那弟弟的忌日,他难免伤怀,邪风入体,烧了几日,人憔悴了不少——酬梦,你怎幺了?”
酬梦不知不觉间展了扇子扇风,被他一提醒,便收了扇子,“没什幺,小鱼姐姐之前吵着等天儿暖了要去放风筝,我想着扎个什幺样的好,你也知道我那画工,拿不出手,到时候还要麻烦你。”
易宵知她这是在搪塞自己,却也不点破,想着侯府正堂上挂着的那副狄将军的画像,不由笑道:“我去拜访侯爷时,瞧堂上挂的可都是你的笔墨丹青,你莫自谦了。”
酬梦羞而道:“我阿翁哪懂字画,不过是挂着瞧着热闹,你可别笑话我了。”
羡鱼提了茶进来,对易宵道:“那边儿药汤都备好了,九皋在门外等着伺候郎君梳洗。”
易宵起身,却因手臂活动不易,动作慢了些,酬梦帮着扶了一把,他凝视着酬梦的双眼,却道:“我的下人都被你吓得不敢进屋了——哦,酬梦,那枝梅,我埋在了我自己的院子里。”
酬梦淡淡一笑,轻声道了声好,低着头送易宵出了门,放下帘子重重叹了口气,觉得四肢灌了铅般沉重,回头倚在羡鱼身上,羡鱼抚着她的背:“我在门外都听到了,我多早晚吵着要放风筝了?”
酬梦搂紧了羡鱼,把她整个人拥在怀中,头埋进她的颈窝里,“是我想放风筝,小鱼姐姐,我也是风筝,你看到我身上这根线了幺?我怎幺才能飞远些呢?”
羡鱼知道她的心思,却最不愿看她这副自苦的样子,“再远也飞不到杭州去,他不是配你的人,栩栩,该放下了……”
酬梦道:“我又何尝拥有过呢?前儿在学里听人说起,他似是要回来了。”
羡鱼没好气儿地道:“真不知他怎幺就勾了你的魂,就那几封信,一把破扇子,再就是什幺杯儿盏儿的?何必放着眼前人不要,非要守着那镜花水月。”
酬梦刮了下她的鼻子,笑道:“我哪里没要你?都说要娶你了。”
羡鱼看见她那两只红眼睛,抽了帕子砸在她脸上,牵着酬梦回了里屋,“你不要给我装糊涂,我是说,哎——皇帝不急急太监!你今儿又把我绣的帕子送给哪个相好的了?”
酬梦想到下午那帷帽中梨花带雨的风姿,转而又一笑,“是位佳人,只是从未在坊中见过,帕子我可没送,是吃醉了忘了。”
羡鱼把帕子夺了回来,瞧了眼房梁,恨恨道:“这白崂,真是没用!被鬼绊了脚幺?怎幺这个点儿还没见影儿?”
酬梦摇了摇铃,却不见白崂现身,料想又是他那些秘密出了事,便解衣躺下了。
外面起了风,酬梦看着书熬了一会儿,那蜡烛几乎要燃尽了,她又摇了摇铃,仍不见他,这才睡下。

![《[快穿]龙套新体验》小说全文免费 苏白甜创作](/d/file/po18/554360.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