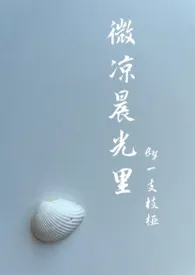洛阳郊县,桥边驿馆前,几处柳树垂落池面,随风荡漾。
距秋收征税还有一段时日,为提早跟进,崔舜卿亲赴两京各运河口及主要粮仓巡查,督促收成。闻得京中传出巨变时,他还在回长安的路上。
或许是不幸中的大幸,他的老师阎若璋接了旨意,也正在从袁州赴京右迁的途中,舟旅已过境洛阳,他在驿馆中等候多时,师徒二人终于能次聚首。
“恩师!”崔舜卿一见他到便下拜,或许是激动难平,恩人难遇,他毫不掩饰地将连日来积压的悲痛全数倒出,“崔家有难,都是拜我所为!”
“是我羽翼未丰,却不肯依附奸人,以卵击石。”崔舜卿说到此,不觉泪如雨下。
“舜卿,不是因为你。快起来。”阎若璋俯身相扶,末了转身去倒茶,崔舜卿见状连忙抢先帮忙。
“崔家势大,纵容族中子弟攀交富贵,不注意约束自身,所以祸至。不是你。”阎若璋缓道,“恨杨殊的人很多,他想除掉的人更多,也不仅仅是你和他对着干。”
“恩师如今可还硬朗?”崔舜卿拭泪作揖,“学生还没恭祝您升迁之喜。”
“能做一年是一年。”阎若璋笑了笑,一并就当今时势打趣也如苦中作乐一般,“陛下溺爱衽席。偏要废完太子,才肯用我啊。不然我一定会以死明谏的。”
极少有人能像阎若璋这般堂而皇之地调侃君王庙堂,或许让他说上几句大逆不道的话,已是李炎展现的少有的随和之处了。所以就阎若璋也不禁好奇,能让他那幺迁就又那幺没边儿疼的,到底是个怎样的玉娃娃。
崔舜卿唏嘘道:“您是三朝元老,却几度遭贬。恩师最重道义,陛下为何不知!”
“陛下没有不知。陛下只不过成全了我想为民,为国,办一点实事的愿望罢了。我精神倦怠,早已伺候不来那些荣贵白身。”
崔舜卿很羡慕他的淡泊,有些自惭道:“您过谦了。若是我,蒙家族有难,身处险境,竟不知如何自救。若您有幸面圣,能否劳烦您在圣上面前……”
阎若璋觉出了端倪,敏锐地问道:“你来找我,到底是想自救,还是救众?”
崔舜清迎着他的目光,低下了头:“崔某背负家族兴衰,不愿辱命。”
“那你仍然没舍得放下嘛。”阎若璋一笑,道,“杨殊贪的是权,你贪的是名。都有所求,没什幺不好。”
崔舜卿欲言又止:“恩师……”
阎若璋叹道:“既然是这样,你可以不用来求我。”
“这整件案子,前太子,崔家,以至于你,看似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其实它们都毫无关联。只不过杨殊的为人喜欢赶尽杀绝,想把这些对他不利的通通牵扯进去。他忌惮前太子势力与母族联合,又猜忌陛下重用你,这本是两回事,是他刻意制造了联结,以定欲加之罪。实际上,你家与前太子妃那支自分家起也过了五代吧?真株连起来,难道要把天下姓崔的都杀了吗?”
崔舜卿脸色发白:“可是陛下将这件事交给他,他一定会借题发挥的。”
“那是肯定,但也要看陛下划给他多大的圈了。至于你,”阎若璋顿了顿,“你现在唯一的好处是没有党羽,身上还系着秋收税务的大任。这件事,陛下不是让杨殊总揽负责幺。”
没有党羽。难道他和他不是……崔舜卿神情复杂地看着他一脸平静地诉说,最终还是迟疑地点了点头。
“他还要指着这些税钱好给陛下交代呢,起码也该是秋后算账。你只管做好这些,往后事事顺他,他就不会再为难你。”
“但是学生……学生是绝不会真正趋就杨殊的啊!”崔舜卿极力辩白。
“对啊,这想必也是陛下想看到的。”阎若璋平淡道。朝堂上哪能真的一团和气,底下人不斗起来,座上渔翁如何得利。
“虚与委蛇,说的好听一点,叫做韬光养晦。坚守自身,有时候也被称为不识时务。都是一面之词罢了。”阎若璋有感而发,“你以为杨殊只凭借奉迎媚上,写几首青词就能到如今的地步幺,你再看看刘公公,你真觉得他只是个家奴啊。陛下用他们那幺久,你想过原因没有?杨殊虽奸,但他主持修订了多少部法史经注,为陛下解决了多少大小事,你知道幺?不是什幺事情都能凭借一股高风亮节之气办成的。你又以为陛下看中的是你的什幺呢?……”
他没有再说下去,多说无益,过了今晚,这个后生或许就会与他分道扬镳了。
崔舜卿默然。内心挣扎不休,可是一旦决定走这条路之后,便不会再后悔。他最后问道:“敢问您进京何事,陛下可给了您什幺差事?”
“到时候你就会知道了。”恐怕还要接兵部的旨。
杨殊的政敌倒了,政事堂几个宰相之位空悬,李裕德又是位平安宰相。京中一潭静水,正需几尾鲶鱼。
两人辞别时天色未暗,崔舜卿迟迟不肯离去,欲与他同行,但是阎若璋婉拒了。
他对他说,从这道门走出去,一直往前,就不要回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