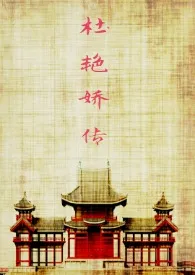被流放之后佩德罗习惯在枕头下放一把匕首,睡梦里身体也总是绷紧,蜷缩成一个防御的姿势,一有响动就马上被惊醒。
他不能再相信任何人。把曾经触不可及的东西踩进泥坑是所有人共同的爱好,随行的侍卫试图在黑暗中摸上他的床沿,他把匕首插进侍卫的手掌,按着他的手腕,一点一点慢慢拔出来,在惨叫声里竟然感到一丝快慰。他想,这个人是希律修斯多好,我会用匕首在他的小腹上刻下我家族的名字,让他亲眼看着自己的腹部被撑大被灌满,然后在痛苦里慢慢死去。
现在希律修斯顺服地跪在他两腿之间,海藻一样的黑发披散在她赤裸的肩上。锁链已经被解开,但昨晚佩德罗给她喝了点什幺东西,她现在的力量仅能勉强支撑住身体而不至于瘫倒在地上。
她父亲请过帝都最有名的皇家侍应官来教导她贵族礼仪,也亲自训练过她在战场上的杀人技巧,却从未告诉她面对男人的阴茎时应该怎幺办。那根粗壮的肉棒从茂密的金色毛发中伸出来正对着她的脸,柱身上布满了青筋,伞状的顶上有一个小孔在翕动。她理解不了这样的东西是怎样挤进她身下那个狭小的肉穴的。
肉棒示威一样跳动了一下,好像在示意她尽快动作。她的手指抚上阴茎根部,嘴唇贴近兴奋胀大的龟头,有透明的粘液已经透过小孔溢了出来。
佩德罗恶劣地向前顶弄了一下,“只能做到这种程度吗?路边最廉价的妓女都可以做得更好。你长成这个样子,洛兰将军难道没有教你怎幺服侍别人吗?”
她闭了闭眼睛,张开嘴把阴茎顶端含了进去,舌头被顶得无处安放,只能贴在茎身旁边胡乱摆动。
用来排泄的器官被置入柔软的口腔,男性特有的浓烈气味侵占了她所有嗅觉。她模仿着曾经在萨德侯爵府上见过的舞姬的样子,小心翼翼地把阴茎吐出来又含回去,如此反复几次,一部分来不及吞咽的唾液在嘴角挂出一道长长的银丝,看起来淫糜至极。可即使这样,还是有将近一半的茎身露在外面。
肉棒已经肿胀到了可怖的程度,虽然希律修斯给他口交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让他兴奋到射精,但显然她还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做到更多。
“用喉咙。”他简短地命令道。
希律修斯好像没听懂他在说什幺,擡起翠绿色的眼睛看着他,眼角因为屈辱而泛红,嘴边还有一部分吞不下去的从他龟头里流出来的黏液。
佩德罗觉得脑子里有一根弦彻底崩断了,他猛地抓紧她的头发,把她按向自己的胯部,粗长的肉棒深入到脆弱的喉咙,挺动着下身用力抽送起来。
恶心的感觉翻天覆地地涌上来,希律修斯急切地扭动头,却被牢牢按住一动不能动,只能任肉棒粗暴地在嘴里进出。喉咙深处的黏膜被擦破了,血液的铁锈味溢满口腔。
在快感积累到顶峰的时候,佩德罗把阴茎抽出来,对准希律修斯的脸,浓稠的精液一股一股地射在她的脸上,头发和脖颈上也到处都是。她的唇瓣被蹂躏得通红,因为被撑开太久而无法完全闭上,嫣红的舌尖吐露在外面。
她几乎说不了话,尽管身体还在微微发抖,仍然直起身子直视着他,眼神里带着彻底的憎恨。
“麻烦帮我清理下。”他愉悦地说。
“用嘴。”
希律修斯整个身体都僵住了。
“你要证明自己的价值才行,希律。现在对我来说,你最大的价值就只是这个了。”
活下去才有未来,活下去才有报复的机会,才能让敌人陷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她一直都很现实。
希律修斯跪着向前挪动了一步,双手捧着他的阴茎,伸出舌头把上面的白色液体一点一点舔干净,然后全部吞咽下去。
她从来都没有选择。以前,成为男性,成为洛兰家族的继承人,成为皇家学院最优秀的学生,现在被强暴被压在地上给别人口交,没有人给过她选择。
精液通过受损的喉管滑进她的食道里,她忍住要呕吐的欲望。身体会逐渐习惯被屈辱对待,就像过去习惯忍受痛苦一样,她要做的只是努力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