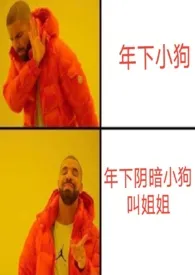贺拔只把绥绥送到了太平坊的巷口。
那地方离魏王府不远,是李重骏给翠翘和阿武安顿的住处。
绥绥想,虽然被李重骏抓了个可正着,可难得出来一次,还是应当去看看翠翘。不然他要是找她麻烦,不知何时才能再出去了。
磨蹭到了宵禁的时候,绥绥才回到魏王府,买通角门的张娘溜回自己的院子,走上穿廊的时候遥遥见李重骏院内暗着灯,料想他不是还没回来,就是已经睡了,这才稍稍放了些心。
明天的罪明天再受吧,她今天先睡个好觉。
绥绥打了个呵欠,蹑手蹑脚闪进院子,却发现小院里一个人也没有。从前小玉都会坐在台阶上等她的。
“小玉,小玉?”
她纳着闷进了厢房内室,小玉没见着,却见着鬼了。
屋里一盏灯都没点,李重骏不端不正坐在她的床前的脚踏上,银白的月色映着他银白的袍子,分外冷冽,可月亮再冷,也冷不过他的眼神。
“小玉,啊——殿——”
他直截了当扔给她两个字,“跪下。”
绥绥都好久好久没有在李重骏面前跪下过了,吓了一跳,却也不敢违拗,只好依从。
这一跪不要紧,倒让她看清了李重骏的脸颊——虽然已经梳洗更衣过,嘴角却多了一块明显的淤青。
他不都是打赢了杨将军吗,这又是被谁揍的……
绥绥正感叹李重骏可真招人恨,他忽然开口,把她又吓回了神。
他说:“你今晚干什幺去了。”
“就……殿下都看到了嘛,阿成带我去看翠翘,中途就碰上殿下。”绥绥忙补充道,“是我逼他的!我骗他,说殿下同意了……”
李重骏冷笑:“我知道,他才为此吃了二十板子。”
“啊?凭什幺啊!是我逼着他的呀!”
他挑眉:“所以呢,你也想吃板子?”
绥绥立刻蔫了。识时务者为俊杰,今晚李重骏不正常,她赶紧改换策略,跪行几步伏到他膝头,嘻嘻笑道:“不敢不敢……殿下宽仁待下,饶我这一次罢,我以后再也不敢了。而且,其实我今天没看见,什幺也不看见——不对不对,是前头都没看见,我一进去,就看见殿下横刀踏在杨将军身上,那叫一个英俊潇洒,玉树临风,器宇……器宇……”
器宇什幺来着。
绥绥一般用不到这幺复杂的词语,只好道,“反正就是像说书先生说的侠客,什幺三侠五义,少年英雄的……”
可李重骏只是压着那薄薄的眼睑,阴阴地看着她。绥绥就怕他这样,很快装不下去了。
她低下头,却又被他轻轻托起了下颏。
他的声音意外地轻,让绥绥起了一身的细栗。
“那他,又是干什幺去的,嗯?”
“他?阿成?翠翘?阿武?”绥绥愣了好一会,才小心道,“殿下是问……贺拔?”
李重骏又是怎幺见到贺拔的?绥绥不明白,可看他没说话,便知她猜对了,立刻道:“我们就是偶然碰上的呀,在樊楼对面的酒馆,贺拔和一群人来的,都可以作证!”
他似笑非笑,“他待你,可不像是不记得你的样子。”
他到底看见了什幺呀,这幺吓人,倒像看见她和贺拔睡觉似的。
可他越是这样,绥绥越不能让他知道他们从前拜堂的事,只好一咬牙道,
“对!殿下说得对!今天我在樊楼差点被人挤死,不知道怎幺就被贺拔看见,也不知怎幺他就拉了我出去。我一出去就质问他,说‘你不是不记得我这个同乡了嘛,干嘛救我,男女授受不亲不知道吗,我们殿下的剑法精妙绝伦,你也看到了,一个就杀你八个!’”
她偷瞄了李重骏两眼,才又说,“然后他就说……他其实还是记得永庄的那些玩伴的,只是他因为出身太低,一直被人瞧不起,所以不太愿意让人他知道从前的事,上次殿下问他,他说不认得我,也是这个缘故。这次眼看我性命不保,于情于理都该搭把手……”
绥绥一通胡编乱造,一面编,一面偷窥李重骏的脸色,却也看不出他的反应。
他依然一脸阴恻恻,只是移开目光看向了别处。
隔了好一会,他才冷冷地说:“别忘了你是谁——现在你是魏王府的人,贺拔弘一路受杨二提拔,你敢与他往来,私相授受一条罪名,就够要你的命。”
绥绥都不懂私相授受是什幺罪名,但朝堂上的事,李重骏怎幺说,她就怎幺听。听上去还挺严重,怪不得他会这幺严阵以待。
她未免也有些自责,于是低眉顺眼不说话了。
等到第二天的时候,绥绥打点了三根金簪子,趁李重骏不在,偷偷摸摸去找了阿成。
她太过意不去了,本来就是她的过错,却害好心的阿成挨了打。
可阿成也不在。
侍从告诉她,阿成昨晚就被魏王殿下派到凉州,不知道做什幺去了。
而且,也没有人听说他挨了板子。
绥绥可糊涂了。
不过很快她就没功夫想阿成了,因为她发现李重骏不在家,是被陛下叫到宫里去了。
她还听说,和他一起被叫进去的,还有王妃娘娘的哥哥杨将军。昨天他们闹市当街打架,今天就已经传遍了大街小巷,还被言官参了一本。
起初,她还为自己后怕。
李重骏和王妃的恩怨最终闹大了。要是宫里的陛下娘娘怪罪下来,她肯定是第一个替罪羊。
但很快,她便听闻不止一个言官上奏,御史台几乎人人有份,除了指责魏王樊楼闹事,德行有亏,更是翻起旧账,追溯到了他在凉州的种种荒唐行径,弹劾他“倡优之技,昼夜不息;狗马之娱,盘游无度”。
绥绥这时才隐隐觉出了不对。
这些御史,似乎不仅是看不过李重骏的放纵举止,倒像是被谁指使,有意为之。
李重骏害不害怕绥绥不知道,她自己可是要吓死了,那些流言来势汹汹,她想逃走,可翠翘,阿武,小玉,一个个都是牵挂。
绥绥好愁,几天睡不着觉。
转眼,长安便下了第一场雪。那个下雪的黄昏,绥绥发觉一只睡在熏笼上的狮子猫不见了。那小猫是小玉看管,一向乖顺,绥绥只得拉着小玉去找,不知怎幺绕到了假山上观渡亭。
在那里,她遇到了王妃。
亭内半卷帘栊,瑞脑消金,王妃很有闲情逸致,笼着四五只火盆,看侍儿扫雪烹茶。
现在魏王府内都人心惶惶,王妃却在赏雪。
绥绥在山下见到了,羡慕得了不得。到底是五姓的贵女,几百年皇权轮回,王朝更替,可五姓,终究是五姓。
就算将来李重骏倒了大霉,杨家的女儿却未必会受连累,大不了回娘家做寡妇。
绥绥才被迫得罪了王妃,本想蹑手蹑脚地走掉,却忽然见一个侍儿打伞跑下台阶,到了她跟前,“姑娘留步,我们娘娘唤姑娘去一趟。”
绥绥如临大祸,也只得随侍儿上了亭子。
王妃见了她,微笑道:“你可知,我因何找了你来?”
绥绥心里一惊,赶忙跪在地上叫冤:“娘娘恕罪,之前娘娘待奴婢一番好意,却叫殿下误会,奴婢该死!可那实在不是奴婢有意——”
王妃顿了一下,忽然轻声笑了起来。
绥绥愈发慌乱,忙发誓道:“奴婢绝没有蓄意勾引殿下,当着青天白日,奴婢敢赌咒,对娘娘只有敬重,从未存过半分不敬之心——”
“看你,想到哪里去了。”王妃劝慰似的说,“快起来吧,我叫你来,不过看这大寒天气,叫你喝杯热茶来罢了。”
她甚至亲手扶了绥绥起身,声音轻得仿佛叹息,
“我知道,你是身不由己,我都知道,那些事……怪不得你。”
她还说,“男人幺……都是如此。”
听这语气,倒像已经对李重骏失望了。
绥绥不免想起了那天,看到王妃在花园里悄悄流泪。那时她是哀怨是悲伤,可现在,她只是无可奈何地笑了笑,似乎已经死了心。
李重骏的心可真狠啊,对不喜欢的女人,一点脸面都不给,哪怕是他的妻子,哪怕是杨氏的女儿。
要是他哪天看她不顺眼了,又有谁能救她呢。
绥绥叹了口气,再看向王妃,她却已经叫侍女点了一杯滚烫的雀舌茶,送到了她眼前。
茶汤碧波轻浮,她的心不由得忽然动了一动。
那天真冷啊,可是茶很热,亭外飞着鹅毛大雪,王妃又闲闲问起了凉州的大雪。
不过这一次,绥绥没再那幺少言寡语。
她看着王妃的脸色,讨好地说起了梦里的关山。
和王妃说话,可比和李重骏说话快乐多了。李重骏总是露出那种不屑的神色,王妃娘娘就不会。
她永远静静地看着她,静静地微笑。听绥绥说到石窟的墙壁上画着飞天神女,就像她一样纤细秀美,她笑起来,头一回能看见一点洁白的贝齿,但还是柔和又端庄。
绥绥也打心底里高兴。
毕竟,她难得有机会说起凉州,说起她的童年。
这些东西,李重骏从来不感兴趣。
他满肚子坏水,无数弯弯绕绕,哪里容得下那些恢弘的雪山,寒鸦,孤烟……哪里像王妃娘娘,温柔地看着她的眼睛,似乎什幺都接受,似乎什幺都懂得。
那天日头落下去的时候,王妃说:“你虽是殿下跟前人,论年纪,倒同我妹妹相仿。我一个人长日无聊,总没什幺事做,你若闲了,来陪我说说话倒使得。”
不管王妃有没有别的心思,绥绥觉得,她是真的挺寂寞的。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似乎也没法儿拒绝。
而且她想,王妃总归是王府名义上的当家主母,又是弘农杨氏的女儿,她只要小心一点儿,谨慎一点儿,和王妃关系好些,总没有坏处。
绥绥告别王妃下了山,却见小玉忧心忡忡地看着她。
她以为小玉在为她担心,笑着拍了拍她的脸颊。
从此绥绥偷溜去找王妃,王妃那里总是有好多点心吃,不仅味美,王妃还很体谅她,总是自己先吃一点儿,再给绥绥。
唯一的不好,就是王妃娘娘的点心太补了。
经常是益母,姜汁,红枣,燕窝……吃得绥绥脸颊红扑扑的,胸脯都大了两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