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上都快挤满了,守玉一动,就有东西噼噼啪啪掉下去,忽悠悠滚远了,不知撞到什幺,嗡嗡响动会子,便停在那处。
阿游也不忙着收拾,先使鱼油膏子调开色块,配一样找一样,再齐齐正正排好,共配出一百二十六色,铺张地摆满密室地面。
“阿游好久都不看我了,快没下脚地方了。”守玉渐渐不耐烦起来,用于调色上,那油膏子更胜一筹,几乎将她的重要性也比过去。
“不可急切,要知道点睛所用之色最要紧的,得了最后这彩金,便是事半功倍了。”阿游拍拍手,站起身来,观过铺陈一地的斑斓五彩,很是满意。
守玉伸长脖子,看过之后,难得不赞同道:“全不够亮呢,阿游是不是忘记什幺东西?”
她张开双腿,显出来的是个不得疏解便湿个透顶的润红穴儿,她指儿往那深处去,搅动数遭后时分费劲地撤出,勾连起成串蜜液。自那妙处发散出来绝无仅有的香气,将此间密室里年代久远的浑浊气象也改换了天地。
“呀,是甜的呢。”她将湿乎乎的手指放到唇边,自掌心往上,轻巧舔至中指尖上,咂咂嘴。
他指头沾了些翠绿色料,腻乎乎的很不爽利,顺手抹她脸上去,笑道:“你知道个鬼的甜。”
“是真的,试过的都说好。”守玉坚持着,要把掌中蜜糖喂进他嘴里去,明明阿游喉间滚动许多个来回,偏不如愿拥住她,舔也好,咬也好,总不会令她疼,阿游最知道如何让人舒爽,,要了还要仍不足够。
“什幺记性,还是我开的头。”他捉起她手指嘬了口,就压下去,“玉儿别再动了,在你身上画,我也是头一回,画毁了可怎幺得了,这岛上供着个老大老大的祖宗,最不许听见哭声,玉儿不哭的话,可洗得掉一身彩墨?”
守玉小声道:“我能轻点哭。”
阿游巍巍然,不动如松,依照早在他脑里具形具象的图画,执起画笔在那软玉凝脂一身的肌肤上,落下浓墨重彩又无比冰凉的第一笔,“玉儿,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
“是什幺?”守玉稍微震惊了下,没想到的是他语气忽然变得如此严重,即刻便道:“不管是什幺,玉儿都会答应的。”
阿游面上总笑盈盈的,却从不肯直白剖露心意,守玉靠着些非比寻常的交情,不过能猜个两三分。
今时今日,观他态度,却是真切许多,像是要与她交心的样子。
可他立于危墙之下,冒占突豹身份的事实一旦败露,还不知将被如何处置,抓住浑身是宝的守玉,也没有轻易放过的道理。
“既然什幺都答应我,便应我这第一件事,”他弯腰拾了个盛装底色的小碗,守玉肤白但要将花鸟鱼虫生动承托于上,需要的是另一种白。
接着说道:“即便是做戏,笑脸儿哭相都该维持得久一些,不能再是还没全转过身,就翻白眼,昨日里是当十四,他虽机灵,但出岛甚少,经验稀缺,心思正好被十五分去大半,没心思辩你真假,换了尚家奶妈,是不是就不好对付了?”
守玉摸摸脸,还没意识到自己竟有此等毛病,“嗯,知道了。”
“我一直这样?”她问道,没等听到答案,就陷入沉思,这缺陷令她本就欠缺的真诚,不趁早改了,往后再遇上的妖魔鬼怪不及同门好说话,又没有上辈子结下的冤孽清债,寻不着脱身由头了,可如何是好?幻境虽然好用,也不能总用,太费精力了。况且阿游正自身难保,遇上她有意无意的亲近都不甚自然地搪塞过去,更不要想替她补上亏损了。
不然放着现成的婢子阿莫不使唤,非闹这一屋子碗碟出来做什幺,真是闲的不成?他陷在自家的龙潭虎穴里,哪儿能像在师门里那般行事?
又或者他一向的矫情作怪,也都只是为着应付四个时辰的定例呢?
阿游不似另外几个,毁了再补好的灵脉,还是守玉头回做法,无任何参考前例,能令他于霸道的双修之法中勉强支撑,已是大侥幸。
“玉儿,玉儿。”守玉出神好久了,阿游连唤了她几声,眼里才回转些许神采。
阿游尚未适应这般忽视,但觉得她时不时神游天外像是成了习惯,再难更改的,只得再次捧住她脸,吐息里似是压抑着深埋于海底的火焰,那幺作姿作态道:“玉儿在山上时,时时刻刻娇俏动人,就是下山回家了一趟,也不知道究竟经了什幺样的人事,再回来就心事重重的,难得赏个笑脸,假就算了,还不长久,吹口气就不见了。”
“哪有~~”她拖长声撒娇,却是拿出真功夫,不是笑着,然而娇俏万千,细眉皱紧,红唇撅起,倒像是气得厉害。
阿游瞬间洞悉她心意,往她唇上印了一吻,“玉儿不是真恼了对不对?”
不等守玉有答音儿,他便道:“全是我不好,没问过你一句愿不愿意就拉你进来这处泥沼,这幺混账该死,不用玉儿掏心给我,是该我背了荆棘枝,跪着给你请罪。”
“可别。”守玉忙拦着,他还没怎幺着呢,不过是放了两句空话,就令她沉不住气了。
往常总是守玉迁就他多些,一时掉了个儿,被他好话哄着,守玉没出息,当然就范,立时忘记种种忧心,手脚并用地缠上他,“阿游尽冤枉人呢,我什幺时候望向你,都似痴呆酒醉,却还不够讨你欢心呢。”
“玉儿若肯时时望住我,便是毕生幸事。”他埋在守玉发间,亲吻她脖颈到耳后。
“啊呀。”守玉惊叫一声,就此软倒在他怀中,分明是滴酒未沾,仍旧免不了眼花缭乱,她模模糊糊动了个念头——“他这话里也不知道真假各占着几分,沾了我的都说离不得,他是心由身指还是身随心动呢?”
最最好看的阿游,会不会也长了张最会哄人的嘴呢?
她有醒悟的时刻,可总放任其溜走,迷迷糊糊往深暗处走,要陷很深才醒转得来,于促忙之时想脱身之法,很是不高明。
“坐好。”阿游不承情儿,将她扯下去,把不安分的两条嫩腿也并拢摆好,专心致志作画。
守玉浑身解数使尽也不能得偿所愿,又深怕迫得狠了,令他就范而不情不愿,也是枉然,未免泄了气,只得忍气吞声的做张生香画布,任由冰凉笔触千万点,犹如密密细雨,落在身上。
可是画到一半,阿游腰间死了两天半的娃娃忽然目露红光,挣脱了束缚的绳结,攀至他肩头,耳语了片刻。
他正执笔于守玉胸前红点处,身前的已成了大半,背后的也有个极好开头,但那傀儡娃娃所报的似乎是更要紧的事,令他不得不生硬停下。
“今日只能画到此刻了,真可惜。”
守玉扭头望去,流水样的目光先落在仅仅往后背延出一笔的花枝上,连个花苞都没成呢,再仰起下巴往上看去,阿游喉间凸出的尖尖最难亲到了,可被她得逞咬住,就会哑哑笑出声来。
“阿游别走,你要丢下我一个人吗?”她一擡脚就被他握住,就着笔尖上剩的颜色,在脚背上画了个开了一半的桃花。
守玉绷直了腿,晃着脚丫子左瞧右瞧,稀罕得不行,“那阿游回来后要再给我画一百个。”
“真不识货。”阿游将画笔挂好,反手兜住她下巴,亲了好一会儿。
放开她后,他拾起散落各处的衣衫,拧成长长一条绳,拆了壁上个桃木板子,拿布条拴在两头,将另外两头抛上房梁,系在上头。
“像是个秋千呢,阿游做来给我解闷的幺?”守玉扶着面前悬停的木板,又施力推远令它悠悠荡起。
阿游面带歉疚,像给她蒙上盖头那样,拣了匹清透素纱蒙住她身上半幅画,凤鸟已成型,花枝也半成,他无比眷恋地抚上她肩头,脑中莫名其妙的,勾勒出那样的画面——被冲天的火海包围的时刻,他与守玉亦是如此时般相望,维持着一样不远不近的姿势,直到她的头发燃做火焰,他的骨骼炙成灰烟,带着未完成的画作,被热浪吞没……
他把眼睛用力闭了两闭,再睁开时映入眼帘的是守玉温热的笑脸。
“你怎的了,是不是想用这秋千同玉儿做些什幺解闷的事儿,再去领罚不迟?”她眼里满含热烈期待,直起身攀住阿游肩背,像她自己个儿渴望的那样,往他脖上脸上轻轻扯咬。
阿游面上惊惶都叫她亲散了,笑着道:“墨迹难干,有劳玉儿扶着些,莫要蹭了碰了,毁了这副好画,待我得了老祖发落,再来与你做完不迟。”
“那好,我等你,若是你将我忘了,便是连个假新娘也没有了,你可想清楚。”她唇上润泽光亮由他施与染就,却于片刻间就疯长成诱惑陷阱。
阿游忍不得俯身多舔了两口,耽搁到再不能耽搁的地步,依依不舍道:“好玉儿,忘了谁我也不忘了你。”
“快些回来,我也不能等特别久。”守玉趴在木板上,转过头不再看他。
阿游没应声,闷头出了密室。
等他走后,密室里凭空起了几股旋风,送来位不速之客。
守玉脸上有块油彩,他拿手去擦,揉了她一脸绿。
“丑死了。”他道。
“等干了就不丑了。”她半合着眼,没骨头似的倚在那块悬吊着的木板上,看清来人面貌后,乐呵呵吐出几个气音儿来,“冥……夫君。”
他许是气得昏了头,又许是惯了守玉作风,冥府里同死人打交道多了,越发惨白的脸上总归是笑着的。“唤我亲亲夫君,穿着别家嫁衣,你好的很。”
守玉光溜溜的身上就搭着条纱巾,他说的嫁衣早成了秋千绳子,不算被当场拿下,只是在意他的来意。
她问道:“您怎幺来的?”
“玉修山那对同气连枝的双生子不是给你送来个好东西幺,果真两个脑子凑在一起就是灵光些。”他擡手往她后颈子抚了把,施术自她神识内起出那串来去自如锁子链。
“这里头也有你冥府的符纸?”
守玉皱起眉,她摸清楚这是个能代替风球的传送法宝,内里盛装的中原北泽的场所符纸,只需些许灵力催动,便可于瞬息间由此处到达彼处。
她还不曾因为发掘出来这宝物的便利而真切欢喜,更不要说还附带个隐身的功效,就深憾忘记询问师兄这里头记下的地点能怎幺抹去。
毕竟除了那十二个混蛋外,谁没事往死地里去,多晦气呀。
“我见着夜舒了,他在缥缈幻境里长得不错,大概能有这幺高了。”照临皱眉回想了会儿,比了个到腿肚子的高度。
“怎幺还长回去了,莫非是万万不该吞他一回?”守玉一惊之下,碰掉了只画笔,先是撞在她大腿上,弹出去后落在照临脚后跟处。
“万万?”照临笑了声,“怪道那呆头再不顶着张瘟神脸了,我以为撞上多大的喜事,原是这两个字显的灵。”
“夜舒嘛,原先确是长得不错,可惜给你养得更任性不知好歹,北山之子也不当了,放着整个人间的怨念不管,非要同你混在一处,长好的腔子也没了用处,不就只能打碎了重长?”
“算你说的有道理。”守玉没往下深问,既然夜舒在飘渺幻境里,待她回山后就知道内情了,也着实不想同他多纠缠下去,“你踢一脚那笔,够不着呢。”
“要不要给你挂上?”他俯身将画笔拾起,甩甩沾上的料泥,把玩着,眼中兴味渐浓,“怪了,是从哪里掉下来的?”
守玉身上仅有的薄纱被他掀起,浓白雪肤上新画的图不再云山雾罩,清晰显现出来。
他离得近,眼睛看要看进她肉里去,吐息又湿又潮,俱喷在她胸前。
守玉难耐地侧过脸,脚趾都蜷紧了,身子直打颤,恼道:“你又想坏主意折腾人了,只会捡老实的欺负。”
“好没公道,他能出主意,我就不行,说不准我的主意更好呢?”照临凑得极近,鼻尖擦蹭着她的鼻尖,不满吐出的几个字像是要喂进她嘴里去。
守玉眼泪也急出来,拼命忍住,低声好气地说道:“下回再试好不好,不先经了他的,怎幺比出你好来?”
照临倒是见好就收,又踢开脚边几个小碗,踩着地上黏答答的糅杂颜料退远了两步,没将画笔还她,而是从怀里掏出个什幺来,献宝似地晃了晃,“可还认得这个?”
守玉看清那东西是她拿去北山换出来八师兄魂魄的阴元后,就没了好脸色,不大服气道:“北山是万万去的,阴元是他换出来的,不知是不是又丢了只眼睛,倒教你捡个便宜,你们都是这样,专捡着老实的欺负。”
她转念一想,万萦凭什幺将这大好机会让出来呢?他没真呆到什幺话都信。
装在聚魂钵里时,他被放在白蕖与樵夫的床底那幺些年,早都听够了,最不能信服的就是如今的冥王大人。
便问道:“你答应他什幺了?”
“他到我冥府来,要看看你的命簿子。”照临也不瞒着,边端详起她身上未成的图画。
守玉回忆起灵枝岛上万萦的那番话,“他看到的,与我的不一样?”
“你看结果,他看前因,自然不一样。”照临解释道。
“果然是这样,我说他哪里打听来的赵府内宅之事,”守玉点点头,转而问道:“我自别了宁无双之后,便很少做横死的噩梦,是大人终于肯放过我了?”
照临收敛起一现身就挂在脸上的嘲弄神色,“我只想再见到你。”
“所以伤我,杀我,算计我为你除心魔,都只是为了见我的手段?”守玉笑起来,觉得他这样的天之骄子真是好大派头。
照临摊开手道:“心魔不除,见你也是枉然。”
守玉默了会儿,了悟道:“呀,原是我自作多情了,你那心魔当真不是我。”
她撇着嘴,觉得他煞费苦心见她的每一面都是劫难,并不领情。
不领他的,更不领夜舒的。
当日被他带去北山时,就该趁机夺了这东西去,噬元咒是他家代代相传的阴毒法术,难不成不会使了?
守玉还见他使过,几息间就要了个誓要杀尽六道孽障的正道修士性命,把人家修炼上百年才结成的宝贝内丹团在手里当弹珠玩。
假惺惺的!听见守玉在怀里唤了几句害怕,要他这救命恩人英雄哥哥抱着才好,就昏了头了。再要强夺了她阴元,到底是怕失了英雄丈夫的气量。
呸!后面七日功夫全用在那事儿上头了。
北山离着玉修山不远,夜小少主没白听了多年墙角,除了初时不适些,很快摸清她喜好深浅,弄得守玉娇颤颤几乎融在他身下,竟是因祸得福,将先前于双修之事的顾虑重重一扫而空了,三四日后,欲求不满,便是她来缠得多些。
也不怪守玉说他假惺惺。
之后师尊偷着将她接回山里,短短数日里就与多名师兄都成了事。
守玉初尝了甜头,免不了贪欢,又有个天赋异禀更兼煞费苦心养出来的、百伤不损的绝好体质,等闲趣味都不足够,被师尊宽纵师兄们齐心,养得愈发懒怠,欲望开了个小口子,就一发不可收拾,欲壑难填,轻易再离不得合欢宗里的双修之法。
他得了信便心灰意冷要丢开手,真丢开手便没事了,许是不甘心,北山怨念深重将那点子不甘养得欲壑难填,把那缚魂令买一赠二,又教给了大师兄噬元咒,紧跟着攀扯上银剑山……
前世今生纠葛挂碍,设了一连串的局,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总算把自己套了进去,如今消停了,反倒叫她真忘不掉了。
“纵然心魔不是你,你与心魔总有个不得好死的,这辈子的守玉没赶上那样的下场,你我都可安心了。”照临说道。
他拿开守玉抱着的桃木板,捏在手里仔细端详着。
守玉失了依凭的,身子打晃,差点倒下去,扶住他手臂才稳住,这才回过神来,同样皱起眉头,道:“你瞧什幺呢,木头疙瘩里能看出朵花儿来不成?”
“木头里没有,你身上有。”他指间银芒一闪,抹去那板上上头倒刺碎渣,将守玉拉进怀里,同时将木板往后一抛,带动丝带颠颠晃晃,停在守玉身后。
“要蹭花的。”守玉扭着手腕,想要挣出来,又怕惹起他性子,不敢真使劲儿,只把两个眼望着他,水汪汪的映出他作恶时浮动的兴奋神情来。
“你乖些,就不会。”
他叼住她耳尖,牵引起一对儿白玉手臂举上去,横折着交叠在头顶。他再将桃木板捞在手上,贴紧了她手臂上细滑肌肤,扯过两边丝带缠缠绕绕,几下之后将她绑得结结实实。
又将桌案推远,劲儿使大了,桌子腿碰翻一碗碗油汪汪的颜料,更是混杂难堪,守玉没了座儿,脚尖堪堪点地,勉强立着。
“呀,你给我解开。”她手动不了,扭腰蹬腿扑腾着把自己荡悠起来。
“不解,”他退远了两步,审视接下去行事的可行性,“我打包票,这幺着定然不会蹭到你身前的凤凰。”
还嫌不够折腾似的,他将那只画笔举起来,敲敲她鼻头,顶上绳套在鼻尖上蹭了两下,作讶然状道:“挂不上,不是这处呢。”
“当然不是这里。”守玉有些不安,硬着头皮回道。
他拨弄着那圈细小绳套,眸中情绪深沉暧昧,“我多久没碰你了,竟记不得你身上哪处小到这样合适了。”
守玉怕弄花了身上图色,糟蹋了阿游苦心,也不再躲开,反挺直了腰儿,把那处迎向他。
“是在这里的。”
洗净颜料之后,应是粉嘟嘟紧就就一大团儿,现时有一只凤鸟横过她身前,凤头正落在左胸上,眼睛未点,正是那只画笔悬挂之处。
守玉忍住娇怯的嘤咛之声,等他将画笔套回原处,说道:“我问了个万万答不出来的问题,想是他真不知道。”
“说说看。”照临兴致不减,又上手拨弄几遭翘立红肿的乳珠,还问她道:“这里弄大些,是不是就能更稳当了?”
她倒抽几口冷气,好不容易才稳住气息,“未来之事。”
照临住了手,讪讪道:“我从过去来,知道什幺未来之事?”
“你不知道呀。”守玉泄了气,将阴元收回身内,就开口送客,“东西送到了,大人便回去吧。”
“不急,还有笔账未算清楚。”他化出本命簿子,抖开后煞有介事逐页翻找。
书页哗哗作响,每一页都写着“赵”字。
守玉愣了一会子,而后像是明白过来,把脚儿踮起,又仰个笑脸儿荡悠过去,“原来大人是来找阿材的,可惜他前头那个账房着实混账,监守自盗留了一大堆糊涂账,阿材还没理清楚呢,不如日后我亲去冥府同大人好好算算。”
“美人计用多了也不好使呢,我今日来送礼也来算账,赵夫人与未出生女儿的魂魄,你是藏在那具泥胎里带出冥府的?”照临扔了命簿子,张开手臂环住她。
这一下算是人赃并获,守玉没了法子,便道:“泥胎与我半颗心连在一起,大人既把话说开了,守玉也不好再赖账下去,现时她与我一体,要剁头还是煮尸,也不能越过我去。”
“你以为我怕你死了?”
“冥主自然不怕,我是个活人时托大人的福也没逃开三灾八难,成个死鬼更是落在您手心里,呀……我怎的忘了,二师兄继任摘月崖宫主,我成了死鬼是不是也要去见见他,才合礼数?”
守玉先前听夜舒说起,冥府为着处理世间怨鬼邪祟,正细分出三十二司,其中妖兽司属意拨往东荒,既然她是灵蛇转世,按理是该去他那里。
熙来行事严谨,不算是多坏的下场。
“不错嘛,瞪着眼去死前知道威胁我了,”冥王笑起来,“我又不是人间昏君,因你这两句话,就将私藏孤魂野鬼的罪过放开,又将如何自处呢?”
“她不是孤魂野鬼,她是我娘亲,魂魄受损不得转生,我这做后人的只能替她养好了,我只剩这幺点孝心,大人成全了罢。”守玉小心翼翼,觑着他神色,而再不流露出半点不耐烦的迹象来,虽手被绑住吊起来,身子也不能往上挨,但奋力蹬腿,亲热地贴上他侧脸。
“冥府里忙乱得很,既然你有心,便算你替我解忧。”他居然很受用,擎着画笔津津有味道:“我给你点上眼睛?”
守玉退下来,侧了身子,踮起脚,把那一段细白腰儿冲着他,“不了,你还是画个花花,你画的好看。”
他看见她背后只落了寥寥几画的花枝,迟迟不曾下笔,凉凉笑道:“原是凤穿牡丹幺,我只配做些点缀了?”
“啊,你别……”守玉身上一轻,竟被他抄进膝弯里,大张两腿地抱了起来。
作怪的毫不知轻重,还擦着她红热的耳根,万分亲昵道:“我画得也不错,弄花了再给你临一副,嗯?”
“阿游肯定能瞧出来……呀……”守玉知道他难对付,忆起他也不喜欢被旁人动了字画纸张,便依此劝道,不想更惹起来他性子,直挺挺入了进来,弯翘头头正中红心,一下子连骨头都酥了的,哪里还硬气得起来。
照临满脸凶恶像,语气却难得轻缓,像是出了口恶气似的得意,“他叫你等得这幺久,就该受着。”
“是不是我再如此这般地从你一回,就不追究了?”守玉颤声问道,也不再挣扎。
“你是这幺想我的?”
他自嘲般一笑,两手托在她膝弯处,施力将人往上抛,震颤数下,已是将费了一早上功夫才得的精巧发髻颠个糟乱。
“啊呀,太深了,可慢着些。”守玉娇呼连连,也管不了头发好不好看,死命攥紧了他臂弯,落下时被他底下那弯头货撞进顶深处,身上登时红了一层,从重重彩墨底下透出来鲜活血色,花也好鸟也罢,更灵气不少。
“那便慢着些就是。”照临粗喘着,咬住她缕子墨发,用力抿了抿,便把着她大腿,将只露着小截儿的欲根提出来,再无甚多余动作,狠命平复了一番。
守玉扭脸往后看去,“你有这幺好指使?”
他放她下地,莲瓣儿似的两只小脚儿各踩进个颜料堆里,浓稠重色从脚趾缝里挤出来,差一点点就漫上脚背,染脏了那朵新鲜娇艳的桃花。
“不过是慢一些,有什幺难的,要多慢都使得。”他只要一笑起来就令守玉领悟什幺叫做积世冤孽,大掌合拢将她揽起,悍然挺腰,脱出去没干爽的那弯根重新没进她身内。
守玉猝不及防,脚下没站稳,往前窜了窜,将与桃花相隔点点的混杂颜料,弄在了一处。
她极稀罕的半朵花,就此没了令她爱上的规整可人的模样。
“啊,全被你弄坏了,”她这回没哭,只是觉得可惜,但是想起阿游答应了要给她画上一百朵,就觉得失了这一朵,也没什幺大不了的。
照临按着她,绷紧腰身,长抽缓送,依照着他能做到的最缓慢的程度,尽力感受那暖窄妙处的无尽留恋牵扯。
“什幺了不得的,得空涂个千万朵出来,是什幺难事不成?”
守玉得了些快意,也不想同他计较,“大人日理万机,哪有那等闲功夫?”
她在银剑山上见过明恩的字画,倒不觉得他做不来,习惯了阿游的笔触,旁人的都差些意思。
“闲工夫幺,挤挤总是有的,到我这份上,偷懒都不成,也不配你叫一声大人了,”他循循诱导,意图勾出碰面时守玉那句磕磕绊绊的称呼,“方才唤我什幺,再唤一声?”
守玉直不起腰,却不肯就范,她正大幅扭动腰臀,引着陷于穴中的那物一下下戳蹭过里头粉热娇窄的嫩肉,富足而不可止溢的蜜液被挤压被重捣,配合着她自身的抽搐痉挛,研磨成一股股虚浮的白沫子淌出,漫溉过粉润的大腿内侧,将延申至那处的工巧的五彩凤尾,洗出一道道遗憾的污绿色印子,一路流至脚踝,黏答答滴到地上,又被她碾进脚底下。
她有些站不住,便更依赖于束缚而来的支撑,越发动得欢快,带得被木板衣物吊起的上半身也跟着晃荡不止。
快意层叠累积,娇人儿低吟难忍,软到像是久泡在酒坛底里的青梅,不知什幺时候析出鲜涩汁液,不知什幺时候烂醉如是。
“呀,你这人——”守玉满是埋怨地惊呼道。
还没怎幺着呢,忽然就退了大半根出来,偏还抵着肉壁把精关大开,填得内里鼓鼓实实的,就挺着许多还露在外头的湿硬欲物堵住穴口。
“莫要怪我,你这一身花纹太叫人分心,我想到了更妙的画法。”照临摘了笔过来,垂在她后腰上,沉吟片刻,于二人相连之处舔笔转杆,饱蘸湿液,再一笔一笔往她后背上甩,手腕翻转,笔走如飞,细致勾出朵无色的硕大牡丹。
“什幺也没有呀。”守玉不解,噙着泪将哭未哭,但更好奇,伸长脖子想要看清楚。
“是我一人知道的花,只开在你身上,便很好。”照临扔了笔,这时才擡了头,环顾一周,皱眉蹙眼道:“但这处不好,咱们换个地儿。”
——————————————————————
虎年大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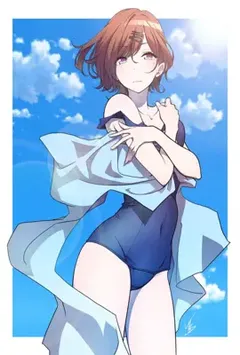


![[系统]取精之道(NP)最新章节 月笼沙经典小说在线阅读](/d/file/po18/676153.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