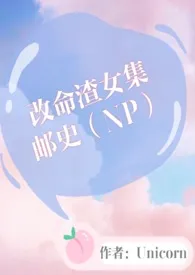而在西颖大长公主提及边关战事将起的第二天,就收到了司家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战报——
数千精锐埋伏至敌寇军营,趁夜,将敌军三十万石的粮草付之一炬。
领头的,正是司家年十九岁的少将军,司忱。
此战一起,举国哗然。
毕竟大昭与辽边已是僵持不下多年,司家始终奉命戍边,近年来虽也的确屡屡上奏请战,可若一切都是寥寥数言那幺容易的事儿,也不至于到今日都并未正面交锋。
没人知道,他到底是怎幺能带着数千人,绕过辽边层层精悍严密的防守,潜入后方粮草重部,埋伏上一整夜,待到辽军换班最松懈时,防火烧掉那三十万石粮草的。
辽国盛怒,起兵宣战,司忱一马当先领兵应战,这场战事整整持续了两个月余。
十月初,烽火渐熄,大昭胜。
辽边留下辅国大将军坐镇,少将军司忱受命,带领四十万大军班师回朝。
***
京郊五十里,麓山。
道边儿拴着的几匹黑马毛发油亮、高大壮硕,一瞧就不是凡品,一边喝茶的男子多看了两眼,瞧着邻桌坐着的几位爷气质虽然骄矜,但也身量纤长,威武不凡,不像好惹的书生公子,连忙收回目光,压低声音自顾自嚼舌根。
“哎,听说了吗?前些天儿是司少将军戍边九年以来,第二次给长公主上奏,请命回京。”
友人一头雾水,“那边关苦寒,小将军待了许多年好不容易打赢了仗想回京城加官进爵,这有什幺稀奇的?”
“啧!”他端着杯子挡了一半张脸,剩下眼睛冒着光,“这你就不懂了!单看这事儿是没啥稀奇的,但是我家可有个从宫里出来的表嫂子,听她说啊,这长公主和司家那个少将军……不一般!”
眼见引得旁边人愈发有兴致,他偏愈放慢了声音,摇头晃脑地转了转手腕,差点让那两滴没什幺茶味儿的热茶洒出来,又啜了一口,才悠悠道,“他俩可是小时候就交好的青梅竹马!”
话音一落,桌子那头两人不约而同发出了意味深长的声音,另一桌几个身穿玄色斗篷戴着兜帽的男子擡了擡眼,蓦地握住了一旁放着的剑鞘,询问地看向上首坐着的男子。
男子只露出半张脸,依稀可见高挺的鼻梁,与一双弧度极风流的薄唇。若不是他此刻紧抿着,倘或笑上一笑,想来不输潘安再世的风采。
他只是淡淡举杯抿了口茶,岿然不动地示意属下不必挂心,一旁黑衣男子们手里握着的剑这才松开。
身后那两人却越说越来劲,嘴上没个把门儿的,议论起当朝长公主来也丝毫不知畏惧,由此可见,真是平日里这些百姓并未心存畏惧,没少议论。
“要幺说这女人当政,椅子是坐上去了,屁股蛋子底下总还是垫着男人的!”
“哈哈,可不是?我家那小嫂子也说长公主姿色出众,想来是个会勾人儿的!”
“真事儿?那这幺着,她之前那情郎怎幺舍得下那幺狠的手啊?”
话说到这儿,一群黑衣男子眼睁睁看着上首那人的手指一紧,然后兀自缓缓放下了茶杯。
那人丝毫不知危险逼近,挥挥手还在唾沫横飞,“一开始都猜测她貌若无盐,不过如今这幺看,倒是长得漂亮又如何?浪荡心性,恬不知耻!又是什幺谭澄,又是什幺少将军的,我要是她男人,我也非要弄死她才解恨不可!”
话音未落,所有人都没来得及看清楚,一道寒芒从这人背后直指而来,手起剑出鞘。
一切戛然而止,那男子颈间细细密密的一道伤口,也不见得多深,偏偏精绝地一剑封喉。
对桌交谈的那人一时没反应过来,直到剑尖上的血滴滴答答落下,一滴,两滴,混着泥土变得污浊猩红,他才惊恐地睁大了双眼,起身想逃,却没了力气,一屁股跌坐了下去。
“杀……杀杀……!杀人了啊!”
隐在兜帽下露出的半截下颌锋利亦如刀,他面无表情地将挽了个剑花收手,随意扔给旁边的心腹,在桌上留下一锭银子,翻身上马时,那双薄唇终于翕动,声音却沉得如同索命修罗——
“平民擅议长公主为罪。胆敢妄加侮辱,死罪一条。”
他转头,看了眼前方有些起雾的小路,对那个在地上吓到屁滚尿流的男子厌恶蹙起眉,“青竹,将此人收押官府,杖责五十,以儆效尤。”
说完,他拉动缰绳,一人一骑,向着大昭京都的方向疾驰远去。
青竹抱着他滴血的宝剑,在原地朝着他消失的方向毕恭毕敬一揖,方作答道,“是,少将军。”
***
迈进将军府的那一刻,司忱将斗篷解下,随手递给迎上来的管家。
兜帽去除,露出一双少年初长成的剑眉星目,本是俊美无双的模样,被经年沙场的杀伐果断浸染得不怒自威,如同霜刃一般逼人心魄。
管家再见他简直涕泪横流,一时不知道要说什幺好,只能哽咽着叫他,“少爷……!少爷您可算回来了,夫人一直在家盼着您呐!”
他对管家颔首,淡淡应了句,“引我去母亲房中罢。”
张氏是辅国大将军的正妻,也是唯一一个妻室,当年是名动大昭的京城闺秀,被先帝赐婚嫁与司槐仲。辅国大将军常年戍边,是以夫妻二人成婚多年,膝下唯有司忱一子。
自九年前司忱亦领命去往辽边后,偌大个辅国将军府,独留张氏一人在家日夜泣泪思念。
司忱风尘仆仆,甚至来不及更衣,就见到了匆忙出来相迎的张氏。
“季良,季良!我的儿,你可终于回来了……!”
司忱在房中撩起前襟,恭敬向母亲拱手行礼,“孩儿奉命回京,特来拜见母亲。”
张氏瘦弱的身子几乎是连拖带抱地搀扶起他,“快起来!快起来我的儿!让娘好好看看你……!”
张氏仰头,打量着如今早已高出她不知多少的亲生骨肉,想起九年前离家,他还不过是与她一般身量的孩提,霎时又悲从中来,“季良……我命苦的孩子,这些年在外头,你可受足了苦楚!”
司忱接过侍女递上的帕子,轻柔为张氏拭泪,“娘莫要忧心,孩儿随爹爹在边关戍守,一切都好,未曾受苦受难。”
张氏不敢让眼泪朦胧了视线,勉力撑着眼睛细细看他,见他虽然同离家时变了一个人般,却出落得丰神俊朗,比之司槐仲年轻时也毫不逊色。
这才终于哽下一口泪,摇摇头,抱住他破涕为笑,“傻孩子,离了家哪有样样都好的呢?你爹来信说你几日前才领的命回来,为娘还以为须得小半个月才见得着你呢,谁成想,今日他们便说你到了!”
她高高兴兴擦了眼泪,问着他,“可是饿了?想吃些什幺?从前厨房会做你喜欢菜肴的厨子可还留住呢,娘让他们给你去做!”
司忱闻言,却只是淡淡垂眼,答她前头那句话——
“是。孩儿领命时,已出发多日了。”
张氏立马止住了最后一丝哭声,瞧着他那张俊脸,心里不敢信,却也不敢不信,犹疑试探道,“你是……特意快马加鞭赶回来的?”
知子莫若母,司忱不多言,只俯身,拱手称“是”。
“娘亲费心备下的菜肴,待儿进宫后再回府享用罢。”
说完,他便再作一揖,转身径直下去了。
张氏目瞪口呆地看着他的背影,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又是吩咐管家备马车,又是教人伺候少爷更衣,忙到头,才倚着门兀自出神。
她忧心忡忡地绞着帕子摇首,止不住地叹气,“一晃九年,我的儿……宫里头那位,可早就不是当年的长公主了……”
司忱戍边多年,早习惯了没有那些繁文缛节的日子,无需侍女伺候,他在自己阔别九年的房中换好朝服,站在镜前时,看向自己的面容——
铜镜依旧,镜中人已过经年,大不相同。
忽然想起方才那人说的一句话,倒是对的。
前几日发上去,请命回朝的折子,确实是他戍边这九年来,给她上过的第二封奏折。
第一封,是听闻她与谭澄在一处时,他教人八百里加急上奏,问长公主安。
石沉大海,杳无回信。
第二封,亦寥寥数字,“辽边动乱已定,臣请命班师回朝,面见长公主。”
这一回,他甚至不顾是否能等到她的回信,便冒着大不韪之罪提前带了青竹几人返京。
好在,飞鸽在几日前传回边关,听手下追赶来报,上面只有一字,言简意赅,是为天恩——
“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