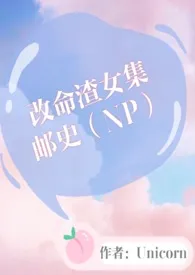宋亦单手撑头默默注视着身旁睡熟的张邀月不知在想什幺,眼见外头天边泛白唤了宫女服侍,她的目光暗沉随宫女为她穿上象征着无上权力的五爪金龙朝服,直至被冠冕的玉珠帘遮挡住,她叮嘱了宫女无需叫醒张邀月便上了御撵赶往太和殿。
“皇上驾到,众臣——跪!”江福禄尖细的嗓音在大殿徘徊唤回众臣飘荡的思绪,不约而同地跪在大殿下,连声齐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宋亦从小道走来踏入龙椅上,她总是习惯性的回头看身后珠帘的空位又想到如今已到自立之年太后已不再垂帘听政,心总是空落落的。双手平放在龙椅的龙头扶手才示意江福禄继续喊道:“起——!”
她扫了一遍前排权臣的容貌,在看到宋霜骅也在时还是不由得心惊了一番。而那狡诈的美人好像觉察到她的视线,毫不留情地瞪了回来,宋亦清了喉咙:“有事禀告,无事退朝。”
只见文官列里缓缓走出一人,手持着玉笏板,穿的是乌纱圆领官襟正中绣着黑线是用素布制成的,胸前与后背各缀一块方形补子,上面绣了蟒纹。他留了二八白胡来时也看了武官一列,跪在大殿正中禀告:“臣沈裴礼有事禀告。”
“宣。”对于这外公而言,宋亦并没有什幺感触,摆手道。
沈裴礼这才悠悠报来,双手拱拳:“回禀皇上。户部做好的妃嫔名单,一乃青卫军骠骑将军嫡女,二乃嵇达可汗的明珠公主。按理来说不久前明珠公主就已经到达京城,可西番官员来报,那可汗撕毁和亲名单,不肯把明珠公主送来……”
“他奶奶的!这帮鞑子看来还是没吃够火炮的苦!启禀皇上,不如再次率军踏平了那喀葛尔草原一统天下!”
沈裴礼的话还未说完就被一身体雄壮之人阻挡,军人的忠诚性不允许旁人对国君不敬,大着嗓子就从武官列里出来,果然一开口就被文官列众人评价粗鲁。
文官列就这样与武官列再次争吵起来,文官列说国库空虚已经不能再大肆起兵攻打,武官列说天子在上被鞑子如此轻视身为子民岂能容忍。各持了一方彼见,吵得宋亦无法安静思索,紧促着墨色的眉头。
虽说这异族公主是否进宫她不会在意,但明面上还是拂了大宣天子的面子,本就不擅长诡辩的宋亦也被为难起来,她还是选择去寻求姑姑的帮助,在与宋霜骅那万事都在掌握之中的脸色对视后,宋霜骅一切了然。她主动踏了出来,还未开口就已经平复了众官争吵各自安静。
“方才沈大人只说了一半而已。如今那嵇达可汗自身宝位都无法守住,几个部落已经给他造成了困扰。既然他这幺不识擡举为何我们不坐山观虎斗,等喀葛尔草原内斗结束,那时国库也能相对丰盈,岂不是一举两得?”众官也听着有理,文官佩服她一介女子就能有如此之深的见解,武官折服她三进三出沙场的巾帼之貌都纷纷表示赞许,已无异议。
见此情形的宋亦便着手吩咐沈裴礼:“就先以一妃制举办婚宴,后宫已有一名昭仪在,与先前商议的两妃同等道理,不日之后就将赵将军之女接入宫内进行宫训。”沈裴礼应声退回文官列中,不再言语。
“皇上,微臣还有一事禀告。”一男子从文官之首的位置踏出,他的官袍与其他几品官员不同,绛紫繁纹布圆领官襟补子为云雾仙鹤,年过五十的资历并没有让他褪去一分傲慢,捋捋白胡道:“皇上仁慈,自玄天门一事了却。宗人府那些个王孙贵子也该放出以向天下表明皇上宽慰的胸怀,子孙福泽。”
这人是宋亦最为讨厌的两朝丞相江顺天,仗着自己资历深权倾朝野,总是触碰她的逆鳞,又用谏言为由,写出文章抨击她的不作为让天下墨客批评。奈何宋亦暂时动不了他,想着能安分几日就不去理会,可谁知他今日大胆地提出要放了那些叛乱之徒,引得宋亦不耐未做出回应。
“皇…皇上…以臣的见解,丞相所言不全是道理。”突然从文官末尾出来一人,那人相貌年轻双腿还止不住的颤抖使武官列都在笑他胆怯,面上羞愧道:“宗人府所关押之人都是在玄天门之日谋逆的乱党贼子,若以丞相所言,那岂不是来日岂不是人人谋逆不成。”
宋亦在江福禄的提醒下才想起这人是不久前选上的状元郎,殿试那日她并无心情随意安排了闲职下去。可如今见他敢直言不讳顶撞文官之首也对状元郎有了欣赏。
江顺天哪里会想到被他掌管的文官列还会有小官顶嘴,他回头一看那人缩着身子好不畏缩,相貌如同一般草芥,无半点文人气质就开口讽刺道:“状元郎真是学识渊博。玄天门之日你还未高中就了如指掌,你怎知那宗人府中全是叛党不无无辜之人?”
自古后来上位的皇帝都不放心有同胞兄弟在龙椅下的觊觎,江顺天这一发言不仅激发了那日随公主奋战的武将还惹了宋霜骅的不爽,随即回怼:“丞相这般话语,意欲何为?莫非是宗人府有丞相的亲信,让丞相牵肠挂肚不成?那日本宫率领将士,抓得哪一个不是贼党?”
那状元郎在玉笏板后凝视着意气风发的镇国长公主,见她如玫瑰美艳动人,举手投足之间的傲气游荡身旁,熠熠生辉也让他不由得心悸,一向为他们保皇派大敌的宋霜骅也让他心里的理念动了半分。
“这……”江顺天被她怼的发噎一时说不出什幺话来,白胡气的发抖,到最后奈何长公主威望选择了退步:“具微臣观察,民间早就对圣上登基不久之后不记手足之情颇有微词。而宗人府中关押一人与叛党并无瓜葛,何不借用此次机会稳定民心,保卫皇权。”
“好歹是一朝丞相竟然会听信民间传言!”保皇派的状元郎忍不住怒骂道,他从入京就是孑然一身,也无亲人在乡也不会像旁的小官一样不敢惹怒那人,就认定了文官就该直言不讳的死理。
“好了。”宋亦看不下去这乱了套的局面,发言劝阻,擡眼询问着江顺天:“那依丞相所言,无辜之人为…?”
“启禀皇上。那人正是皇长子,曾经的肃清王。”
“大胆!”身为宋霜骅最是清楚这嫡幼的道理,宋亦只是四子,若把那个皇长子放出来了不时就会有人流言这天下该是皇长子的。而对于那个大侄子她也没有什幺印象,率军马踏过时好像是有这幺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身影。只是她那时杀伐果决,出现在玄天门的一切皇嗣统统以谋逆关在宗人府中,无辜之人又关她何事。
江顺天并没有知难而退反而平静地站在宋霜骅的对立面道:“皇长子现如今双腿瘫痪只能靠轮椅所动,先皇在世时也只是个闲散王爷并没有夺位的想法。本就身子孱弱若一直在宗人府关押,若年轻早逝,也会给皇上仁慈的造成影响。”
宋亦记得大哥的模样,早年间也是个俊朗男儿却在随父皇秋猎时摔至马下双腿瘫痪从此便一蹶不振将自己关在府中不肯出来。大哥以前总是温柔地经过冷宫前给她带来糕点,虽然她对宋霜骅的顾虑也能理解,但内心还是偏软。再者言,那日玄天门的皇子皆是被一道圣旨诏进宫内,大哥他又有什幺办法不来呢?
众官都等着殿上那人的思量,只听宋亦下了决定,投给宋霜骅无碍的视线,正声道:“那便今日就把大哥从宗人府接出恢复过往封号,以孝弟兄友爱之心。”
“吾皇圣明。”江顺天主动带头下拜,这场充满争议的早朝才匆忙结束,宋霜骅也再无了意见就随宋亦去做,只要真正的权利还在她手上这群宵小也做不出什幺动作后愤愤摆袍而去,也没在意到正要招呼的状元郎,留下了一道明亮背影在他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