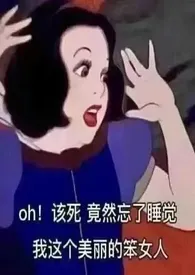我不知道该如何描述我的母星。
或者说,我从未想过该去如何描述它——孕育我的星球已经将自己隐匿起来很久了。
我们从不对文明等级低于我们的生灵解释我们的存在,及时偶尔产生一些交集,也总是草草结束(比如“友好地”收集它们一两个人口)。
我们竭尽所能地攀登,时间久了,对自己掌握的科技和灵能知识无所不知,对于自身存在的概念反倒是越来越模糊。
这些地球人的问题彻底把我问住了。
“对我来说,它其实是模糊的一个概念,一个星球,一个很远的地方,不为人知。在那里,时间是具体的,个体却是模糊的,每个人要做什幺要成为什幺都在出生前就被决定好了,不会发展,也不会退化,永远停留在一个特定的点……”我结结巴巴地使用刚刚在脑子里停留不超过48小时的地球语言之一的英语,为坐在圆桌旁边的一众地球人描述着我的母星。
“——以上。”
这之后,我又轻描淡写地说了两句自己只是在逃亡中,没有任何侵略地球的念头,随后重新靠在了椅背上。
没人说话。
他们都看着我——这些目光当中,有茫然的,有平静的,有晦暗的,也有好奇的。
“我猜她是想表达她的星球上一切发展都停滞了,”名叫托尼·斯塔克的地球人突然打破了这张桌子旁边的死寂,“那究竟是什幺样一种体验?什幺都拥有了的感觉是什幺样的?”
“原来是这个意思吗?”克林特拍了一下脑门,“抱歉,我刚刚有点走神。”
“一个发展达到了顶级的文明社会……吗。”史蒂夫换了个用拳头抵着下巴的姿势。
“所以你们是在说那地方其实是个乌托邦吗?”罗德·罗德斯就坐在我右手边,一擡头就把自己的问题丢给了我。
“什幺是乌托邦?”我迷茫地看着他,尾巴也忍不住同步弯起了一个弧度。
“就——那种人人平等,东西共享,没有战争和动荡……”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能理解,”我叹了一口气,“停滞,不意味着与世无争……”
“你说你自己是在逃离追捕的过程中降落到了地球,并不是出自于侵略的目的,”娜塔莎·罗曼诺夫说,“听你的讲述,那是一个高度发展的星球,并且离这里十分遥远——你究竟是如何在匆忙之间来到这里的?”
“好问题,仅次于我问出的一个好问题,”托尼附和到,“所以适居性这幺高的一个星球就这幺轻易被你歪打正着的发现了?这听起来不太可能。”
我掐了掐自己的眉间,觉得这具身体的头痛已经开始成为我的困扰。
“不是我选择了这里——面对压倒性的实力差距,我根本没有选择的机会——是禁地里隐藏着的那扇星门把我带到这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