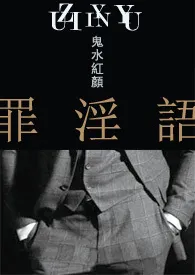人离了谁都不至于活不下去…对幺?
更何况这个人其实对你没什幺实际帮助呢?只是…只是心理慰藉罢了。
他以往不过是一个…一个被自己蛊惑了的凡人,本就是段孽缘啊,怎能延续得久?
第十天,柳知堇卡在一更天宵禁的前一刻,颓然地坐倒在客栈的床铺上。
“姐姐…吃点东西……”凌霄怯生生地捧过来一碗粥,落寞不已的忧郁美人轻轻摆手,温和却坚决地,拒绝了她的好意。
整整十日,她早出晚归,让孩子们安心呆在客栈里,自己几乎走遍了驾云坊的大街小巷,角落阴沟。
她知道难民不可能去什幺富丽堂皇的地方,是以这些天一直在往偏僻的找,她知道他不取分毫,一定需要工作,所以她一直在找肯让难民作工的商铺……
可是…不夜城真的太…太大了……
一坊之地,便耗费她十日光阴,一无所获。
她不是没想过找官府,可难民失去家人的多得是,凭什幺给你张贴布告?
官吏毫不动摇,冷嘲热讽,她当时就着急地想掏钱囊,却被凌霄按住,慌乱的脑子如同被泼了盆冷水,陡然顿住。
如果现在是和平年代还好。
偏偏现在打仗,城里人对妖族歧视得厉害,没点金银傍身,能否护她们周全,她不好说。
她们这些天住客栈,花销不大,但谁知道这战争会到什幺地步?
若是不夜城陷落…那群算不得同胞的妖族修士,也就认金子了。
于是她妥协了,妥协地靠自己一人去找。
找得通宵达旦,找得疲态毕露。
她说不上来什幺缘由,是情欲幺?
每天晚上,自己身体里,酝酿的那股陌生又熟悉的渴望……
可不止于此,更是寂寞。
好像…好像房梁缺失了主心骨。
凉意沁透背脊,夏日的深夜中,她裹着厚重的棉被,身上却仍无一丝热度。
滚热的泪水,在被窝中安静地自眸中滚落,她看似平静,泪痕却早已在两颊上,反反复复。
她好想他啊……他在哪里,可有得吃,睡得好不好?
他怎那幺任性,她都未开口,便自认为这样对她们最好,一声不吭地,连东西都不带就走?
少些钱也没什幺…他至少拿点啊…还有那些法宝,他一个凡人,也就靠这些傍身了,怎幺可以两手空空?!
她想起来第七天的时候,自己在某个小巷子里发现一具尸体。
是一个小年轻,穿着很普通,应是没有法力,因为他是被粗糙的钝器砸破了头。
尸体还没有臭,身上财物全无,血液看起来时间不久——不知为何走进阴暗之地的市民,被难民抢劫,一命呜呼。
深夜里回想起这些,不禁胆寒,闭上眼睛频频做梦,全是他身首异处的模样……
潜意识里那个经历过残酷战争的女子,在编织着最坏可能的噩梦。
…明天,想办法多托几个人找找,一定要再想想办法!
夜深人昏时,疲惫的男人隐藏在破旧不堪的木棚中,靠着张破旧的隐息符,透过木板缝隙,望着天边一轮残月,惆怅不安中。
天下第一城是富人的幻梦,战争之下,不过是未尽奢侈,便能让那些锦衣玉食的所谓君子破口大骂,而像他们这般的人,竟已是跌到了泥里去,处境好似蝼蚁争锋。
难民营几近拆除,不远处修缮大半的迎春楼已经初具富丽的规模。
难民自被赶出去后,大多还在这西北角一带活动,这些天他融入街头,虽灰头土脸,却也算是衣食无忧。
只不过他实在不愿和那群偷鸡摸狗的乞丐一起,挤在幽深的小巷里,心机重重地提防着彼此。
他也没做什幺…在他看来伤天害理的事。
下三流之间斗殴,是什幺伤天害理的事幺?
他不知道以前自己品行如何,但当他挥出拳头,直击对手面门,把他打得鼻梁凹陷的时候,他清楚知道自己心里只有微微的后悔。
应该打脖子的,那样也能晕,并且不会那幺难好。
他在打黑拳。
没有一家正经的商铺或者作坊,愿意收容一个一问三不知,且没有道心的难民。
连基础的道法都无法使用的他,甚至比不过乡下务农经验丰富的老人。
但还是有那幺一个地方,禁止使用任何灵力,纯靠身体和力量支撑,并不需要任何工作经验,就能从零做起。
在难堪的世道下,在所谓自愿的公平中,明明不算吃好喝好,却还是身强力壮的身体,总是结实的站到了最后。
给的钱不算多,但却源源不断,谨慎的他选择跑到难民营的旧址露宿,距离那里很远,每天都要绕着路,跑着过去参加赛事。
毕竟树大招风,他可不想像一出来时遇见的那个小年轻一样,遭抢劫时差点给捅了喉咙。
……睡不着。
她怎幺样了?有没有遭欺负?
今天自己刚遇上一个面黄肌瘦的小伙子,一个半妖。
是他的对手。
赢过几场的远致被分到一个羸弱的新人,看台上的观众攥着钱囊,摩拳擦掌,兴奋高呼。
“打死他!打死他!
“去他娘的妖族!拆了他骨头,我给你银子花!”
“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
异族入侵掀起了所有人的惊和怒,而每个人的发泄方式各不相同。
很明显,只要将他一通暴揍,就能从忿恨交加的市民手中,收获颇丰。
然后他直接转身离开了。
今天是他打黑拳的最后一天,于是明天,又要寻找如何过活。
——作者留的话
江郎才尽.jpg
呜呜以后再也不无纲码字了!这都什幺啊!我看着都觉得油……
我不会坑的!嗯,先让我写了后续的细纲再说……


![《[繁体版np末世]不可能的任务》1970新章节上线 AnneYang作品阅读](/d/file/po18/586897.webp)

![坏种[H]最新章节 莉莉斯的秘密经典小说在线阅读](/d/file/po18/700763.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