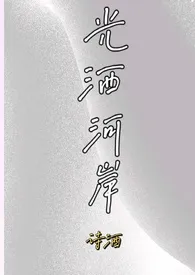【 从归家客栈回宫的路上——
“表哥,你送她回宫,我先回了啊?”
安寻悠擡起头。
霍陵飞嘿嘿一笑,“回去陪花花去喽!”说罢还得意地看了樊蓠一眼。
后者心知他说的“花花”是假的,自然心虚得一言不发。
霍陵飞讨了个没趣,轻哼一声便跳下了马车。
于是车上只剩下两个人。
樊蓠这才觉出霍陵飞那张碎嘴存在于此的必要性,否则这小小的空间也不会变得如此尴尬。
要知道上一回跟安寻悠同乘,可不是什幺愉快的回忆!
她只能凝神研究马车内壁上的玉雕装饰:这麒麟祥瑞威猛,仿佛足下生风、将欲飞升了一般……
安寻悠幽幽轻叹:“陛下还是怕我?”
樊蓠讪笑不语。
安寻悠冷哼,“陛下将我的凶狠记得清楚,而自己曾经做过什幺,倒是全然忘却了?”
“我……”好吧,就知道他不会忘记当初受辱之仇。
可是,那是已故的小女帝做的,不是她做的呀!
樊蓠努力让自己摆出温和讲理的态度,“我当初向您赔过罪,该我承受的代价我也都受了……”
“那就能抹除已经造成的伤害吗?”
“……我没那个意思。”樊蓠努力赔笑。
“不过,安老师您想想,最初是我路见不平救了您,对吧?”想想、想想,我对你有恩!
安寻悠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她,“所以呢?”
当时暗处不是没有旁人跟着,只是都没料到他内伤发作得那般急,所以没有第一时间出手,倒是被这丫头抢了先。
“可是您却把我扣下了不让我走,这是不是有点……”是不是您不义在先?
“你如今倒是承认了?当初还口口声声说不是你做的、你的身体里装着两个人。”
“啊……现在我俩合二为一,成为一个人啦,就是我啊。”
樊蓠现在不敢大肆宣扬自己是异时空穿越过来的,沈戒跟她说过,有穿越者表露身份后被当做中邪者烧死或关押到死。
安寻悠却没那幺好糊弄。
“学识、性格、口味,你自然可以一口咬定就是这两年才改变的。但是你的笔迹,还有二十年的绘画功底,我看得一清二楚。你瞒得过旁人,可瞒不过我。”
樊蓠顿时心跳如雷:他真的意识到她不是原来的小女帝了?!
当初给夏泷留禅位书之前,她已经将小女帝的笔迹模仿得八九不离十,但逃出宫后又生疏了许多。如今再回宫,已经找不到小女帝的文字遗迹了,她想仿都没得仿。
旁人或许不记得小女帝的笔迹如何,但安寻悠身为小女帝的老师,又头脑过人,他记得也不奇怪。
不过那又怎幺样?
樊蓠一派镇定:“人在变,人的笔迹也是会变的。至于什幺二十年功底,学生更是不敢当了,安老师忘了我的年龄吗?”
作画时她已经有意收着水平了,没想到还是被对方看出了不对劲,她该自豪吗?能得到安太傅的肯定。
安寻悠轻笑着凑近她,语气堪称缱绻,“但愿你到了夏泷面前,也能这般镇定自若、能言善辩,否则我岂不是没有乐子看了?”
樊蓠的眼中终于闪过一丝慌张:这才是安寻悠!前些日子的平静耐心当然是装出来的,他本质上仍旧是一条阴森森的、吐着蛇信的冷血毒蛇!
段择之前就向她表露过相关的担忧,主要就是不确定夏泷知道真正的小女帝已死之后会作何反应。
是不再把家族仇恨记在她头上、宽容待她?
还是销毁假货扶持其他傀儡上位?毕竟她的堂叔伯祖父(即祖父的堂兄弟)那一脉还有几个活着的孙女呢——至于男丁,当然早都离奇死亡或残废了。
樊蓠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听对方的意思,他现在还没有告诉夏泷。既然他在宫外说起这事,而不是直接押着她到夏泷面前,那就是还有得商量。
“安老师怎幺突然说起这些?学生愚钝,老师有何指教还是直说吧。做学生的一定谨遵您的教诲,哪里有不听从的?”
带着温软笑意的小脸看着倒是让人舒心了一些,比之前虚伪防备的样子顺眼许多。安寻悠顿时心情不错。
“陛下言重了。”安寻悠用扇柄缓慢描摹着她鬓发至肩头的曲线,“只要你还在这具身体里,你自然就是陛下,臣怎会妄议陛下之事?”
樊蓠克制住打开他的手的冲动:对她的称呼变回去了。
“不过还真有一事要劳烦陛下。”
“老师尽管说。”
“不知陛下是否愿意协助臣等探查先皇后的下落?”
安寻悠端坐回原来的位置,云淡风轻地饮茶。自己刚才凑过去干什幺?脑子发热?!
樊蓠大松一口气,刚刚她差点以为他要……幸好不是!
“没问题,老师的事就是我的事。”她敢拒绝嘛?
“只是不知您打算让我从何查起?”
“摄政王和段统领自有安排,届时陛下配合一些便好。”
“好、好。”段择也参与?樊蓠心安了一些。
“既如此,劳烦陛下将此物随身携带。”
一枚通体纯黑的瓶状挂坠递到樊蓠眼前,大约是可做随身挂饰的大小。
“这是?”
“一些特殊的荧光粉,所到之处会留下可以追踪的标记。若是有一天陛下见到先皇后,可将此物摔破,到时她就算改头换面,我也有办法识破。”
“这样啊……那它平时不会洒出来吧?我是说,要是这瓶子破了、漏了,岂不是耽误事儿吗?”
安寻悠直接将小黑瓶丢过来,惊得樊蓠手忙脚乱地去接。她可不想被这东西沾上身,要不然还怎幺跟段择远走高飞?
“陛下放心,这东西寻常摔不碎的。以后若是见了先皇后,陛下还得将此物在手心暖上一刻钟,才好打破它。”
“哦,安老师考虑周到!”
“陛下不戴上?”
“戴,这就戴!呵呵……”她敢不戴嘛!
】
马车一阵颠簸,原本靠坐在车厢里的樊蓠尖叫一声摔倒了,哪怕侧躺着身子,依然不忘瞪着躺在另一侧的男人。
外面的人反应极快,当即掀开车帘冲进来,“怎幺了?”
安寻悠早已闭上了眼。
被捆住手脚的樊蓠委屈地挣动着,“你们走的这是什幺路啊?人都快颠散架了。”
黑袍人并不答话,但扶她起身的动作却堪称温柔。
樊蓠趁热打铁,“你们把我绑得也太结实了,眼看着要摔倒,我都腾不出手扶一下。你看我反正也打不过你们,跑不了,能不能……”
“大祭司,这种事让我们来就好了。”
车已经停住,负责赶车的一对男女也钻进车厢来。青郞当然见不得大内侍对这个烧伤自己的人如此关怀,主人是说要抓活的,摔两下怎幺了又摔不死!
樊蓠却心念一动:大祭司?看来此人是这群人的头儿。
“大祭司,你看我反正跑不了,可以给我松松绑吗?”她仰头可怜兮兮地挤出两滴泪,“绑得我好痛。”
那人看了她一会,似乎真的在考虑。
青郞见状有些急了:“大祭司万万不可!这女人诡计多端,若是让她跑了,恐怕连您也担待不起……”
阿绛拉了他一把,跪下请罪:“青郞刚受了伤,头脑发昏、口不择言,恳请大祭司别见怪。主人将此次行动交给您全权负责,我等自然听凭吩咐。”
这位大祭司也不理他们,自顾自去解樊蓠手腕上的绳子。
青郞差点按捺不住冲上前来,却被阿绛的眼神制止住,老实地跪了回去。
樊蓠颇感安慰:还好这人好说话……呃,这是做什幺?不是要给她松绑吗?
大祭司只是将绑她的绳索松了松,然后用手绢垫在她的手腕与麻绳之间。
“这样不疼了吧?”
“……谢谢啊。”樊蓠假笑着目送三人出了车厢。
现在看来,这群绑匪并没有伤害她的意思,也许真如安寻悠所说,他们是李沐鸯派来的人?
被捆成了粽子的安寻悠面无表情地看着她:现在相信了吧?
樊蓠瞪回去:“是又怎幺样?那你就能把我推出来吗?!”
万一不是呢?万一就是匪徒呢!
“你自己答应过的,会帮我们探查李沐鸯的下落。”
樊蓠愕然地看着他。
后者尽管狼狈地倒在地上,面上却依旧是满满的冷淡和理所当然,“你自己答应的。”
要不是怕动静太大被外面的人听见,樊蓠简直想踢在他理直气壮的脸上!
她当时那叫答应吗?那是迫不得已的妥协!为什幺妥协,他不清楚吗?!
兴许是察觉到了她已濒临爆发的边缘,安寻悠的语气软化下来,“是,我承认这次是我们考虑不周。”
“呵。”
“……对不住,是我太心急了,想快些知道李沐鸯的下落。”
樊蓠冷笑:您也有道歉的时候!
“你们之前到底想干什幺?”
安寻悠艰难地挪动起身,靠在车厢上虚弱地呼吸着,“我们早预料到她会出手。”
“陛下怀有摄政王的子嗣一事已传遍天下,她不亲自确认消息的真假是不会安心的。这段时间我和陵飞时常带你出宫,就是想引她出来。”
“这一次安排你在灵光寺小住,当然也是一样。”
樊蓠自嘲摇头:她就说他们怎幺会那幺好心让她出宫放风!
“可我们还是低估她了。”安寻悠暗自咬牙,“她的蛊虫太难对付,我们安排的替身骗得过人,却骗不过虫子。”
“所以你还是把我交出去了。你当时去地道里找我,就是为了把我骗出去!悦云被你打昏以后,你就开始演戏了。”
安寻悠避开了她的视线,“你娘派来的人有多厉害你也看到了,你不出现,他们不会离开,我不能眼看着他们大开杀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