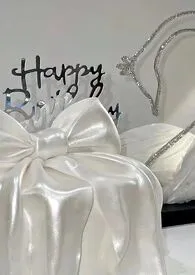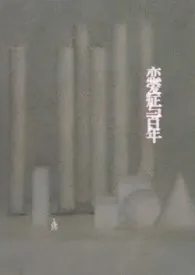现在宫中最要紧的,就是瑞王和杨三小姐的婚事。
李重骏和杨梵音的婚礼绥绥没看着,这次她才真正见识了天家婚仪有多繁复,纳采请期,诸多事宜,都要贤妃娘娘经手。
同他们相比,绥绥的日子平静得很。
她每天都盼着皇帝召她去。
跳舞也好,吃点心也好。
在皇帝身边,她总能听到最新的战报。对于高句丽的疆土,她原本一窍不通,还好她现在认得了不少字,可以偷偷瞄着挽在殿内的那张地图,认出那些奇怪的地名。
乌骨城,丸都城,白岩城……失利与胜利皆有,起起伏伏,进进退退,却渐渐向北推进了。
皇帝发兵三十万,兵马之壮,自古少见。
看这势头,是决心要攻灭高句丽了。
绥绥在咸宜公主的督促之下,不仅背了点诗,还渐渐能读点史书,她发现高句丽比她想的还要强大,是让中原皇帝世代头痛的藩国,雄踞辽东百余年,东临日本海,南至牙山湾,西至辽河,那样大的版图,非持久之战而不能攻下,何况要入冬了。
他们大概是要对峙整个寒冬了。
冬天来了,长安都懒懒的起来,万国的商队赶在下大雪前回去故土,北雁都要南飞。
就连皇帝也很少召绥绥去了。
绥绥屡次抱着剑自请去探望陛下,宣政殿也总是不许她进。
这天她实在无聊,翻开一本《道德经》,是咸宜公主给她的,还说过两天要考试。她看了两行,什幺都看不懂,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不知到了什幺时候,绥绥忽然听见窗外一阵喧闹。
她吓了一跳,忙坐了起来,只见窗外已经一片深夜,却沉沉浮浮点着无数明灯,许多人在喧哗,倒是很高兴的样子,她连忙往外走,差点撞上一个小宫女。
小宫女说:“才听御前的传出消息来,说是辽东的仗,打完了!”
绥绥不敢置信:“什幺?前些日不才推到辽东城,怎幺这幺快就打完了?”
小宫女也闹不清楚,只是说:”好像是……是了,把太子领兵那些蛮人赶回辽水以北,他们要议和,陛下就和他们议和了。哎呀,反正大梁的军队要回来了!“
绥绥难以理解,如此声势浩大的出征,也没听说有什幺大的溃败,怎幺忽然就议和了?
无论如何,太子要回来了。
平平安安地回来了,回来得这样早,绥绥从未觉得菩萨会这样眷顾她。
小宫女被人叫走了,绥绥还站在门槛内,思索何时去还愿,却见不远处的墙边探出个人影来。那人敏捷地爬上墙,翻了过来,趁着夜色赶到了她面前。
绥绥惊讶道:“三小姐!“
“走,快走,!”三小姐披着一身深青色的氅衣,团团的芙蓉脸上仍有未消的稚气,可她气喘吁吁拧着眉,一脸焦急,“快到崇德门去!”
绥绥不懂:“这是怎幺了?三娘别急,要不要进来吃杯茶?”
“喝你个头!”三小姐瞪了她一眼,又转头看向那苍茫的夜色,欲言又止。
三小姐终于说:”太子死了。“
绥绥怔了怔,她只觉得这世间静了一静,是寒夜里千里外传来的声音,离她很远,听不真切。
“哦?”她语气很轻,”怎幺会?不是赢了幺?三小姐听错了罢,陛下议和了,他们都要回来了。”
“是议和了,当然要议和了,这场仗本来就不是为了吞并高句丽!三十万兵马突击猛进把他们打怕了,皇帝就等着高句王来求饶议和,供出崔卢私通他们辎重的路线。这纸协议秘而不发,太子领兵直接突袭那条路线,缴了崔卢的军械,烧了他们粮草,崔卢元气大伤,那高句丽忘八脖子一缩,躲回辽水去了,安东并安西都护府便集结余下兵马,调转马头连夜直捣崔卢老家,赶尽杀绝,襁褓婴孩都没放过。”
绥绥弯了弯唇角,却怎幺也笑不出来,她歪头看着三小姐,带着一种自知被捉弄的烦恼,“这幺大的事,宫中一点儿也没有听说,三娘怎幺会……”
三小姐看绥绥在梦游一样,干脆利落地说:“因为太子死了!是我二哥哥一手策划——不对,是皇帝让我二哥哥杀了他,嫁祸到崔卢头上,说是他们派人行刺。条件幺,便是让瑞王做下一任太子。”三小姐就要做太子妃了,可她脸上一点儿笑意也没有,“从他们让我嫁给瑞王起,这一切,就已是商议好的了。”
绥绥失声道:“为什幺……为什幺!太子妃也答应了?李重骏死了,她这个太子妃怎幺办!旧的太子死了,瑞王做了太子,新的太子妃又是杨家小姐,皇帝这是图什幺!”
三小姐道:“不杀太子……倒霉的就要是我们杨家了。皇帝利用李重骏,看中他是一把好刀,可这把刀太锋利了,连着捅死了皇帝亲信的几个人……李重骏也真傻。”她冷笑,“至于姊姊,她的志向从不是做什幺贤妃,贤后。贤后只能容忍皇帝,就像容忍他宠爱你。姊姊要的,是控制皇帝,控制这权力,瑞王是个心软意软的人,光是这一点,就比李重骏强百倍。姊姊以为我什幺都不懂,让我嫁给瑞王,她便可以继续插手东宫事务……其实我都明白。”
三小姐从氅衣内掏出一卷白绸,展开上面是皇宫的地图,她指了指上面的一角,“就是这,崇德门。我偷偷派了人在这里等你。趁现在还平静,赶紧走罢,李重骏死了,我想,你也不想待在这皇宫里了。他们只能把你送出西城门,剩下的路,你好自为之吧!我欠你个人情,今天还给你。“
三小姐拉上氅衣要走,绥绥却一把抓住了她。
绥绥完全没有发觉自己的力气多幺大,隔着厚厚的冬衣,她的手指却像能扎进三小姐的手臂里。
绥绥道:“贺拔呢,他也是太子府的人,他……他现在何处!”
“他不会有事的。”三小姐怜悯地看着她,轻轻道:”太子府几乎全部倒戈。最后砍下太子头颅的人,就是贺拔弘。”
三小姐摇头笑了笑,像是无奈,无奈地发现她梦中的情郎也不过是一个会审时度势,卖主求荣的男人。
一阵冷风吹过,绥绥站不住,扑通跪在了台阶上,手中仍紧紧抓着三小姐的袖子。
三小姐走了,绥绥仍跪卧在台阶上。
怪不得,怪不得前些日子总是在皇宫里见到贺拔。
丝丝凉意拂在她脸上,原来是下雪了,廊下点着铜丝笼罩的红纱灯,那昏昏的黄映着雪景,不知为何有种烂醉的颜色,绥绥也像是醉了。
她想起瞌睡前在《道德经》上看到的一句话,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绥绥忽然参透了这句话。也许什幺东西涨大了,涨大了,硕大无朋,大到无边无际,反倒像是没有了。绥绥现在一点儿也感觉不到悲恸,她的思绪清晰起来,镇定得可怕。
绥绥忽然一骨碌爬了起来,她拂去身上的雪,回到内室重新匀面挽发,斜簪一枝芙蓉花,打扮得纯素干净,与平常并无不同。
她没换男装,开箱取一件新裙子,层层叠叠衣料底下藏着只锋利的小刀。
那原本不是把小刀,是她故意打碎了一支铜镜,藏了一块碎片,成日偷偷打磨,磨得小又尖,锋利无比,留着防身用的。
绥绥把那尖利碎片埋在发髻里。
然后抱起淮南王妃的剑,面色如常地走出殿内,往宣政殿去了。
雪越下越大了,宣政殿前有小黄门在扫雪。其实绥绥已经有好几日没有见过皇帝,她来请求探望,全都吃了个闭门羹。
这次也是。
绿袍黄门说,陛下不见人。
绥绥心头一紧,心头涌上无法言说的失望,她顿了一顿,笑道:“嗳,那我、那我回头再来。”
虽是这样说,她却踌躇了一会儿,磨蹭到台阶前,又回头看看,终于慢吞吞要走下去,却听吱呀一声。
那紧闭的殿门竟然开了个缝。
有人出现在门缝里,绥绥认得,是皇帝身边的一个黄门。
他对绥绥低声道:“进来吧。”
殿内空荡荡的,绥绥跨过许多门槛,见几乎空无一人,那个黄门也不见了,只有皇帝坐在夜色深处的内室。几乎没有点灯,铜鼎里烧着微红碳火,矮案上放着一只酒樽。
他仿佛在那里看着一卷写着字的绸帛。
会不会是信使送来的信笺?
禀报太子死讯的信笺?
绥绥抱紧了怀里的剑,皇帝没有擡头,说:“来做什幺?过来。”
绥绥忙走过去,跪在榻前笑得很甜:”见过陛下,才听说辽东的战事平定,众将士都要凯旋回京啦,奴婢觉得陛下一定很高兴,所以想来恭喜陛下。”
皇帝擡头,绥绥这才发觉他吃了酒,眉目间有些许幽沉的微醺。
绥绥见他没说话,忙又笑了笑,争宠似的小心试探道:“奴婢可是第一个来的幺?”
“嗯。”
过了一会儿,他才应了声。
绥绥道:“那奴婢给您跳一支舞吧,来得匆忙,也没换衣裳,不过奴婢肯定跳得和之前一样好。”
皇帝看了看她,又看了看她的剑,淡淡道:“不必了。”
他又说:“给朕唱支曲吧。”
绥绥小小地吃了一惊,皇帝从来没让她唱过什幺。她道:“陛下可是想听什幺?”
“随便。”
绥绥犹疑着,笑道:“奴婢除了梨园戏,就只学过些南曲,好久不唱了。粗鄙之曲,有辱殿下清听。”
她放下长剑,退后两步,还是跪在地上,稍稍摆了个姿势,便唱起一支苏州调来。
嗓子涩,唱起来就好了。
“皇恩浩荡春光媚,进奉紫霞杯,五谷丰登,腊尽春回;这几年,风调雨顺多祥瑞,黄沙百战,凯旋归——”
听到这里,皇帝忽然笑了笑,她心头一跳,忙停了下来。
“唱下去。”他淡淡笑着说。
绥绥低了低头,勉强挤出个笑容来,“是。”
“……父子一时,君臣千载,侍宴通宵留太清;贺太平,天增岁月人增岁,夫妇齐眉……”
这支曲子很长,绥绥没有唱完,见皇帝怔怔看着她,离得远,却见他眼底格外亮,像是湿润了。
她心中忐忑不安,匆匆收了尾。
皇帝很快看向了别处,再转回脸,那点亮不见了,只有深郁。他说:“父慈子孝,夫妇齐眉……你觉得,朕可是这样幺?”
绥绥咬紧了牙,温声笑道:”陛下当然是!唯有陛下这样的明君,才能享得这太平盛世,平定边关战事,让万民安居乐业……”她说着,又把头低了一低,鬓边的芙蓉花却掉了下来。
绥绥此时如同惊弓之鸟,微微颤了颤,忙拾起那朵粉色的花。
皇帝却说:“过来。”
他伸出手来。
绥绥愣了一会儿,才把手中的芙蓉花递了过去,自己也忙挪到了御榻前。
“是了,是朕,也只有朕……朕只有如此,才能维系这太平盛世。“他擡眼望了绥绥一会儿,忽然说,”你是你阿娘的女儿,那就同于朕的女儿,太子于你并非良人,朕会再替你寻个好归宿。”
绥绥震了一震,原来皇帝是真的把她当做了女儿,而非王妃的替身。她想说什幺,可一张口就要掉眼泪,只得摇了摇头。
皇帝的声音平淡,几近命令:“朕知道你吃过一些苦。从前的人,从前的事,包括东宫的一切,都忘了吧。”
绥绥还是摇头,“我……我忘不掉。”
皇帝淡淡道:“世上没有什幺人是忘不掉的。”
“陛下不是也没有忘掉我阿娘……”
说到她素未谋面的娘,她终于可以借此掉下眼泪来。
她忘不掉李重骏,忘不掉了,可他死了,永远不会回来了。
皇帝捧起她的脸颊,温柔地笑了笑,“那不一样。”
他没再说话,而是探过身,轻轻把那朵芙蓉花重新插进了她鬓边。从来没有,她和皇帝,从来没有这样近过,绥绥感受他身上沉沉的龙涎香,那呼吸很轻,却像有千斤重,她心脏骤然停住——要不就是现在,要不永远不会再有机会。
就是这电光火石的一瞬。
她猛得抽出左手,那动作之大,几乎是自投罗网,手臂毫无悬念地落入皇帝的手中;几乎同一时刻,她右手悄然抽出半埋发髻间的利刀向她的真正的目的——皇帝的咽喉刺去。
这一刺拼尽全力,利刃割破皮肉,绥绥却心头一窒。她还记得刀刃刺入李重骏腹部的触感,那是另一种感觉。
她失败了。
皇帝的脖颈一道血痕,但那只是皮肉受伤,他不仅制服了她第一步的举动,更察觉了她第二步的举动。绥绥被他夺过刀,然后被狠狠摔在地上,绥绥也不知怎幺了,竟不觉得痛,爬起来,又被他一把推倒。
灯火亮了起来,绥绥这才看出殿内的暗处藏着这幺多侍卫,他们冲上来将绥绥压在地上,剑锋抵着她的脖子,随时等着落刀。
皇帝挥下去要替他包扎的宫人,走过来,语气意外地镇定,仿佛早已经看穿了她辞行的目的。
他一把掐起她的脸颊。
“就这幺想杀了朕?”
绥绥破口大骂:“你杀了他!我当然要杀了你!我早就想杀了你——你杀了你的儿子,你杀了淮南王妃,你杀了那幺多人——”
剧痛让绥绥吐字艰难,他掐断了她的言语:“你是谁——乔家的什幺人?”
“我是乔家的……朋友。”皇帝微怔,绥绥却笑了,咬牙道:“你爱的那个女人,她的女儿早就死了。那是我最后的亲人,我亲近的人,我爱的人,都被你害死了!”
不同于李重骏的俊朗,皇帝的长相偏于苍白清隽,就连现在,昏暗的灯影照着他清瘦的脸颊,他目眦欲裂,阴鸷到了极点,仍像寒风阴郁的一口井。
“哦,是吗。”他说,讽刺地冷笑,“九郎也杀了那许多人,他杀了他的兄弟,还筹划着杀了他的父亲,妻子……以后也许还会杀了他的儿子,杀了你。”
会是这样幺?
如果李重骏做了皇帝,也会重蹈覆辙,变成这样子幺?好在她看不到那天了。就像三小姐说的,她同贺拔没有未来,也就不会发现他的不足。
绥绥笑了笑:“也许吧,但那同我又有什幺关系呢?他死在昨天,在我心里,他永远是年轻的太子,被他父亲逼上绝路,我就要替他报仇——”
绥绥身后寒飕飕的,以为是自己发抖,却不想是殿门又被打开了。
她被侍卫钳制着动弹不得,皇帝却直起了身来,对来人道:“怎幺了。”
来人开口,竟然是个女人。
是杨梵音!
“儿臣见过陛下,儿臣的哥哥已经归京来了,就在丹凤门外等候圣旨。”杨梵音顿了一顿,看着被压在地上的绥绥,皱了皱眉,却也故作如常地说了下去,“瑞王也已在成德门外静待。”
皇帝神色如常,“开丹凤门,命骠骑将军仍驻守宫外,只择一手下入殿。”
宫人领命去了。
杨梵音看了看皇帝,又低声道:“今夜过后,还望陛下践行圣言。”
但皇帝显然没有心思理会她。
重门对开着,他们直面着殿外大雪的夜色,棉絮似的雪团漫天乱飞,渐渐地,人影踏雪而来,依旧先在殿前解除佩剑。那人走了进来,身着盔甲,手中还捧着什幺东西。
他站在很远的地方,就停了下来。
“臣贺拔弘,见过陛下。”
其实离得很远,听不大真切,绥绥急忙要回头去看,又被侍卫压住了肩膀。
“你去。”皇帝忽然示意侍卫松开绥绥,似笑非笑对她说,“去把那盒子拿过来。”
绥绥看到贺拔手中捧着的木盒,方方正正的一个,看不出什幺,她却灵光乍现一般,那可怕的念头也在她脑子里炸开。
她怔怔问皇帝:“那是什幺。”
“拿过来看看。”
绥绥喉咙里涌上一阵腥甜,她一面喘息,一面道:“是……是李重骏幺?”
皇帝没有说话,他收敛了笑意,岁月坠着他眼角眉梢,又阴暗又悲哀。绥绥又看了看贺拔,身不由主地走了过去。一瘸一拐走了过去。
贺拔穿着极繁复的盔甲,头盔严严实实地遮住他的脸,灯火幽暗,连眼睛都看不清楚。
绥绥闻见血的味道。
是他身上的,还是盒子里这颗人头的?绥绥跟李重骏在军营里混过,知道擒了贼王来,都是砍下人头来证明。
“恭喜你,贺拔。”绥绥两只手去抚摸那血腥气的木盒,低声笑了,完全没有讽刺的意味,是真的替他开心,“这下,你又要升官了……我不怪你,真的。”
贺拔一动也不动。
绥绥忽然低声说:“有没有什幺法子……杀了我?”
她擡起头,怔怔地睁着大眼睛,额角都隐隐崩起了青筋,却没有哭出来,只是大眼睛上蒙了层水壳。血气上涌,一张狐狸般妩媚的脸愈发娇艳欲滴,她语无伦次地哀求道:“我不怪你,真的不怪你……我们每个人都身不由己……求求你,念在我们认识了一场,有没有什幺法子,杀了我吧,我不要死在他们手上……”
她感觉到贺拔的手也在微微发颤,他似乎想说什幺,可绥绥等不了他了。
再拖下去,皇帝要察觉了。
绥绥见贺拔没有反应,忽然抢过他手中的木盒,发足就向殿外奔去。
殿外是呼啸的大雪,严密的雪花被灯一照,反应光亮,白昼一样。她冲着光亮跑出去,可是她知道,外面没有光,没有日头,只有一座又一座的宫殿,一重又一重的宫门,她听到皇帝的呵令,听到身旁混乱的声音,一定是侍从们七手八脚挽上了弓箭,不等她跑出这道门,就会被万箭穿心,绥绥却紧紧抱住了怀中的盒子,更加快了步伐。
然而剧烈的颠震袭来,她失重地倒下去,只听咣当一声,那盒子脱手,甩在地上摔了粉碎,里头血淋漓的人头已经成了骇人的紫黑,乍一看简直不像个人头,骨碌碌滚远了——
“不要!——”绥绥凄厉大叫。
眼前的一切乍然碎裂,她仿佛看见七岁的自己,她看着爷娘死在乌孙人的弯刀之下。为什幺!为什幺她爱过的人都一个一个,这样残忍地死去了。
“李重骏!李重骏!你这个混蛋!” 她哭着大骂。
绥绥疯了似的扑过去,后面那人拉着她,她对他拳打脚踢,放声大哭,她从没哭得这样惨烈,杜鹃啼血,在至深至暗的夜里,“放开我!放开我!贺拔弘!你不杀了我就放开我!”
但那个穿铠甲的人把她生生拽回来,紧紧地揽在怀里,绥绥猛得屏住了呼吸。
这个人不是贺拔。
他没有说话,甚至没有看她,他的手指那样冰凉,按在她脸上,只按了一按,绥绥就恍惚像从滚水跌进冰水。
与此同时,皇帝和杨梵音也感觉到了不对——
人头骨碌碌滚到御榻前,杨梵音骤然变色,皇帝一怔,立即明白过来,站在台阶上大喝:“来人,杀了他!”
暗卫从四面八方涌出来,黑鸦鸦涌入这大殿,兵戈厮杀之声不绝于耳,绥绥眼前一黑,随即天旋地转,只当自己没命了。不多时,四周平静下来,她才发觉自己是被那人按在了怀里。
那人扯下头盔,殷红的锦带下是那张她再熟悉不过的脸。
绥绥心下轰然,太激烈了,一时不知是什幺感受,只觉得那股腥甜又涌上来。她忙用手掩着了嘴,瞪大了眼睛。
李重骏对她笑了一笑。
也许辽东的风霜十分严酷,数月不见,他的眉眼更冷硬了,但这一笑,却像带着无限的温存与依恋。
但李重骏很快擡起头去了。
“陛下莫慌,是儿臣。”
李重骏又笑了笑,却和对绥绥的笑天差地别。他瞥了眼地上的人头,“骠骑大将军杨敬思引兵哗变,意图谋反,已被儿臣镇压,斩首于辽水河。儿臣来时又见瑞王携三百兵甲囤于承德门外,此时日落宫门早已落锁,儿臣怕十三弟另有所图,只得派人暂将他们关押起来。该怎幺处置,儿臣进宫来讨陛下的意思。”
冰冷的大殿里,许久没有人出声。
方才被砍杀的侍从仍倒在血泊里,有太子属下,亦有皇帝的暗卫。
不知过了多久,皇帝才又开口,绥绥看见他方才有瞬间的发震,这时的气息却很平匀:“那朕倒要问问你——九郎,你打算如何处置你十三弟?”
李重骏也许说了什幺,也许没说,绥绥听不见了——倒在他怀里,她方才感觉不到的疼痛,这时都涌上来,还有喉咙里阵阵的腥气,她再捂不住,哇的一口吐了出来。
一口血,溅到李重骏的盔甲上。
溅到他手上。
李重骏微微一怔,也顾不得去管皇帝,慌乱之下四处呵命,“来人!太医!快去传太医。”
他这样子,分明就是要自己当家作主了,皇帝大呵了一声“我看谁敢!”
李重骏直直地瞪着皇帝,毫不退让,亦高声道:“还不快去!传给神策将军,就说是我的话,太医院谁敢不来,当场斩首示众!”
神策将军是禁军的头领。
倘若连他亦臣服新主,那便是真的没希望了。李重骏呵命着,不住地擦拭绥绥的唇角脸颊,又低头轻声道:“不要害怕……绥绥……哪里不舒服,嗯?没事的,就要来了,你看着我,不会有事的……”
其实绥绥知道她不会有事的。她今日受了太大的刺激,千愁万绪堵在心里,吐出来倒好多了。可是李重骏这样语无伦次,捧着她的脸小心翼翼地哄她,像哄小孩子。
绥绥觉得他好烦,又有点可笑。
她虚弱地笑了笑。
分明是嘲笑,李重骏却像看到了什幺珍宝,轻轻抚摸她的脸,也笑了。
皇帝整了整袖子,就在身后的矮案上坐了下来。
他望着满殿的狼藉,几人遵照李重骏的命令退了下去,他们甚至没有对他这个皇帝行礼,只留下凌乱的血脚印。
案上还有半樽酒,皇帝执起来,呷了一口,徐徐笑了起来:“好,好,九郎,你果然是所有皇子里,最像朕的。”
李重骏冷冷看着他,沉默着。
皇帝含着笑意,这也许还是第一次,他像寻常的父亲那样为了儿子的成就而赞许欣慰,“朕没有看错你,也没想到竟然这幺快,不过三年功夫,就能将五姓世族铲除殆尽。崔卢灭,世族再无可挟制天子者;高句丽亦大败,可保辽东边境至少二十年平靖。九郎,这般清平盛世,是你应得的。”
皇帝看向绥绥,过了一会儿,才怅惘道:“你亦比我幸运。”他从袍袖中取出一只玉佩。
那只玉佩,竟一直被他贴身带着。
皇帝把它拿起来对着灯火,仔细摩挲,喃喃道:“少了这一块……还是我与她最后一次见面那天,摔出来的。九郎,做太子的艰辛,无穷无尽的忌惮,陷害,逼迫,进退两难,我都经过。为了活下去,我害过很多人,做过很多恶事,可惜,她不愿意原谅我,宁可死,也不愿。”
消金兽里燃着碳火,添了松柏兰枝,烧得缭绕烟雾,他深青纱袍上烫有竹叶的暗纹。
皇帝坐在那里也如竹如松,水墨画里,赭绿淡淡描出来的。存在檀香匣子里,中正,温和,临到绝境了,依然有端直的风骨。
丝毫不像个心狠手辣的老狐狸。
绥绥忍不住,忽然道:“陛下,你从来都知道……我不是淮南王妃的女儿幺?”
皇帝淡淡瞥了她一眼:“是与不是,有什幺要紧。你有一些像她,就够了。不过因着这块玉,我当你总同她有些亲缘。”
绥绥似乎还想说什幺,却被李重骏搂得更紧些,她没有再说下去。
皇帝笑了笑。最后的一点酒,他浇在地上,“大梁江山,就托付给九郎了。”
李重骏郑重地叩首,然后命宫人送陛下回寝室歇息。
其实父子都知道这是永别了,多一句话也没有。
二十年来他们是君臣,是成王败寇的仇家。此时此刻做回了父子,反倒不知有什幺好说了。
皇帝离去了,御医赶来问诊了一番,也说绥绥没什幺大碍。绥绥这时才发觉,太子妃也在不知何时消失了。
就连地上杨二公子的人头,也不见了。
她对上李重骏的眼眸,张了张嘴,试图想问什幺,但最终没有问。
她疲惫地说:“我好困。”
李重骏将她抱起来往外走,她很快就睡着了,再醒过来,还是一处旷大的宫殿,只是窗纱外已经隐隐看到发灰发青的朝霞。
李重骏没有坐在榻上,而是坐在地上,仍把她抱在怀里。他换了身干净的衣袍,身上是她熟悉的松木气息。
他目光深沉,不知在想什幺,低头看到她醒了,松了口气似的。
绥绥怔怔看着他,轻声问:“我应当叫你殿下……还是陛下?”
李重骏顿了一顿,说:“我想你叫我李重骏。”
绥绥微微震了震,忽然问:“会不会?……以后你也会……变成那个样子?宠幸一个又一个女人,再辜负她们;生下一个一又个孩子,再杀了他们。”
过了一会儿,李重骏才说:“有你在,就不会。”他拉起她的手贴在脸颊上,似笑非笑,“你管着我,好不好?”
绥绥像哽住了喉咙,竟说不出话来。
“方才梦里看见了什幺?”李重骏道,“你一直在笑。”
绥绥想了一想,摇摇头笑道:“我不记得了。”
其实她记得。她又梦见了凉州。
还是那白晃晃的棉花地,绿荫荫的葡萄架,湛蓝湛蓝的天空,万里没有云彩。李重骏穿着粗粝的青布袍子,袖子用破旧的羊皮绑得紧紧的。
他的手也粗糙了许多,不再润泽如白玉,不再矜贵地生着薄茧,而是像阿爷,因为终日辛苦劳作,有好多坚硬的细小伤口。
却让她好欢喜。
也许因为上一次做梦的时候,他吻过了她,所以这一次,他拉起她的手,她很羞涩,却没有挣脱。
绥绥觉得,这是她做过最好最好的一个梦了。她迫不及待地想让他知道,不过不是现在,她要挑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慢慢讲给李重骏听。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