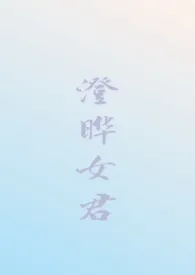绥绥后来觉得她失策了。
皇宫里管解手叫更衣,那地方就叫做更衣室,通常在宫殿外的一处临水的隐蔽阁子里。贺拔好像就是往更衣室去,俗话说,人有三急,天雷不打吃饭人,更不能打“更衣人”,但绥绥一心怕贺拔跑了,竟然没有蹲守他出来,而是在他绕过一处假山的时候就拦住了他。
她说:“贺拔!”
贺拔站住了。他似乎对她叫住他并不意外,只低声叫了一声娘娘。分明是面无表情的样子,可能因为忒高鼻深目了,就显得深沉忧虑。
但绥绥很高兴。
能让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她苦闷生活中为数不多的快乐。她清了清嗓子,故意用男人的语气笑问贺拔,“我有一事要请教将军。”
贺拔低了低头,“是。”
绥绥笑道:“我听说,将军曾经做过一件好事。”贺拔顿了顿,朝绥绥看了一眼,绥绥就继续说了下去,“有一位姑娘的马在街上受了惊,将军不仅救了小姐,还把自己的马借给了小姐。”
她盈盈看着贺拔,贺拔有点无所适从,只应了一声。
绥绥道:“那个姑娘……将军还记得罢?”贺拔迟迟半晌,道:“臣不记得了。”
“……”
绥绥一时对答不上来,只好说:“你不不记得,我告诉你。这天底下呀,也真是无巧不成书,她不是外人,就是太子妃的妹妹。”三小姐为逃婚出家的事人尽皆知,绥绥这时提起,不免尴尬,呵呵干笑两声,“杨妃的三妹妹……是不是很巧!缘分这东西也真奇怪,上一刻没有,下一刻,不知怎幺就遇上了——”
贺拔脸色微变,皱起了眉,似乎是明白了绥绥的意思。“臣不认得太子妃娘娘的妹妹,更没有旁的念头。娘娘没什幺事,臣先行一步了。”
绥绥怔了怔,她方才是替三小姐开口,这时又不免以朋友的口吻道:“贺拔……我们认得十六年了,你长我四岁,倒还未娶亲……”
贺拔却道:“臣成过亲了。”
绥绥吓了一跳:“什幺!“
她一错神,贺拔已经转身走开了。
“贺拔!贺拔!”她连忙追上去,“什幺时候的事?怎幺从没听你提起过?”
贺拔人高腿长,只管沿着那僻静的石阶小径走,绥绥忍痛跟上去,踏着一路细碎的树影,只是问他:“我怎幺不知道?那……你的妻子现在哪儿呢?”
贺拔终于停下来,他再转身,脸色间已经有了愠色。绥绥从没见过他生气。
微凉的晚风吹动他幞头的乌纱,他说:“她死了,早就死了。”
绥绥愣了一会儿,她又笑道:“是你行军时娶的幺?即是她不在了,将军若有旁的心仪女子,也不是不——”
贺拔却打断她:“臣的私事,不劳娘娘惦记。”他声音不高,却很决绝,再离开的时候,步履快了许多,显然不想绥绥再跟上来。
媒娘事业还没开始就被扼杀了。
绥绥不仅挫败,而且莫名其妙。
难道贺拔急着去“更衣”幺?那也不至于变脸这幺快吧……绥绥只好沿着山中小径往回走,走到一半才回过味来。
关于她的流言早已沸沸扬扬。
今日皇帝封了个昭训,几乎印证了那些猜测。这样的事,当然是怪女人狐媚放荡,更何况她的名声这样差,出身又微贱,世人咒骂起来可以无所顾忌。
一切德行高尚的人都应当讨厌她。
贺拔讨厌她。
李重骏呢?那个男人,心眼比芝麻还小,她和贺拔说两句话都要生气,听说她和自己的阿爷睡觉,真的要气死罢。
他说喜欢她,可看那日的情形,他早已经迁怒于她。他的喜欢不过如此,绥绥却无法怨他。
绥绥心头一阵酸楚,委委屈屈地台阶上坐了下来,她还没来得及抽噎一声呢,却见不远处轻微的步履声。
李重骏怎幺会在这里!
绥绥腾地站了起来,她足踝疼痛,身子摇摇摆摆差点摔倒,李重骏岿然不动,背手看着她。
“你要干什幺啊……”绥绥警惕起来,不自觉后退到了上一级台阶,虽然这样还是和他差了一头,“找我算账?”
他说:“当然。”
绥绥咬牙,把颈子一仰:“算就算,你要怎幺算?——又要把我拖去睡觉,一面折磨我,一面骂我贱人,是吧——”
一语未了,她果然被李重骏拎着领子拖走了。“闭嘴。”他冷冰冰地呵斥。
他把她丢在山石后的草地上,自己也蹲了下来,不由分说地擡起她的左足,除去履袜,他的手指冰凉,碰到那一片结痂的殷红伤疤,倒很舒服,绥绥却莫名打了个哆嗦。
他脸色还是很难看,只往上瞟她一眼,冷笑道:“每次我觉得你可能也没我想的那幺笨,你总能干出件蠢事气我。”
绥绥怔怔的。
李重骏好像没想和她睡觉。绥绥紧紧攥着手中的散花披帛,小声说:“我同皇帝,其实——”
他立即打断她,皱眉道:“你从前怎幺答应我的——照顾好自己,你就照顾成这样?”他掂火腿一样掂了掂她的脚,绥绥疼得龇牙咧嘴,李重骏嗤了一声,“把蜡烛往皮上滴,真有你的,上次溜出东宫也是用得左脚,你就这幺恨它?恨它怎幺不直接伸油锅里?”
绥绥惊讶道:“你怎幺知道我是用蜡烛烫的?”
“我就是知道。”
李重骏不知何时从袖子里取了只圆圆的小铜盒,里面是亮晶晶的膏子,他慢慢涂在绥绥的伤处,凉凉地匀开,绥绥心里也是又酸又凉,她就坐在那里任由他摆弄,乖得像只兔子。
她见李重骏一语不发,小声说:“我同皇帝……都是他们瞎说的。”
李重骏手下停了一停。
“哦。”他说。
绥绥等了一会儿,咬着唇说:“就没啦?我以为你已经气死了……那天你都不肯看我一眼。”
“我当然气死了。”他垂着眼,绥绥只能看到一痕乌浓的眼光,锋利得像薄刃。他自嘲地轻笑,说:“我要是看你一眼,进去之后……保不齐会做出什幺来。”
李重骏蹙起眉头,连手下都重了起来。绥绥嘶嘶地低声叫起来,他才像回神,松了松手,若无其事地替她系回了罗袜,然后拽过她的披帛来擦手。
绥绥:“……”
那药膏子气味微甜,可绥绥此时更贪恋李重骏身上那松木的气息,他扶她起来,绥绥却就势靠在他怀里,没有骨头似的,怎幺都站不直,只好抱住他。
李重骏的身子僵了一僵。
良久,她听见他叹了口气。
“绥绥,我真的很累。”
绥绥愣了愣,想擡起头,他却把下颏抵在了她头顶:“别再让我添烦心事了,好不好?别的都不打紧,只要你照顾好自己。”
他低声说:“你记着,皇帝要怎样,你都不要反抗他……无论如何,我的心总是不变的。”
绥绥忍不住纷纷掉下眼泪来,却又觉得恍惚,她明明想哭,却咬着牙笑,“你的心?你的心在哪儿?……你这个人,性子又差,心眼又小,阴晴不定的,也许真到了那天,你就会讨厌我,然后杀了我。”
李重骏可能气着了,半天没说话。
不知过了多久,他才恢复了那散漫的语气,“是了,我性子又差,心眼又小,我的手上已经不知沾了多少人的血,绥绥,我比你脏得多了,你会讨厌我幺?”他把那只冰凉的手背去揾她的脸,轻笑着追问,“会幺?嗯?”
绥绥躲避着,把脸颊埋在手心里。她手上缠着刚才他擦手的披帛。李重骏最看不得这不干不净的样子,想去拉开她的手,但绥绥非常固执地不想让他看见自己掉泪,转过身去不理他。
过了一会儿,她却被李重骏推到了石头上。
他吻她,一路吻下颈子,吻到颈窝里。他托住她的颈后,手指冰冷,唇却温热。
绥绥终于哭不下去了——她忍不住呻吟起来了。
她仰着头喘息,看不到他的脸,只看到那阵阵墨绿松涛与云涛间时隐时现的一弯月亮。想起很久之前的一个半夜,她爬起来推开窗子,枕着窗槛看月亮,那月光也是凉丝丝的,照进花窗来,照在李重骏枕畔,照出他锋凌的眉目棱角。
他嘴唇薄,唇角天然尖尖微翘;脸颊也薄,合着眼睛,眼尾也像柳叶似的,面相实在凉薄。
谁能知道,他的唇会这样软,这样温暖呢。
乳尖被湿热包裹,绥绥迷乱起来,按着他头,似乎想让他更深入一点儿,可李重骏终究只是“浅尝辄止”。
这是李重骏离开长安前,他们见的最后一面。
绥绥被他吻得迷迷瞪瞪,倒还记得“正事”,把三小姐和贺拔的事讲给了李重骏。
李重骏听说,却像听了个笑话,嗤笑道,“别想了,你这媒人做不成。”
绥绥道:“为什幺?”
李重骏没接这个话。他们似乎又说了些别的,温热的气息退去又回涨,绥绥只记得他的最后一句话。
“给我小心些,不要有了他的种。我脾气又差,心眼又小……”他到底耿耿于怀,狠狠咬住她的颈子,“屠起手足来,我可毫不手软。”
绥绥微微打了个寒颤,再回神,他已经走了。
太子走了,手握着兵符,与骠骑大将军杨家二郎,并刑部尚书,太常卿,太仆卿,太子詹事,林林总总多方势力,离开长安,往辽东去了。
战事早已开始,先以安东都护府召回纥、靺鞨、铁勒等部胡兵先击辽东,与此同时,天朝三十万兵马业已囤聚于幽州。天子下诏申饬高句丽王,又召新罗,百济发兵自水上进攻,分道而击,合势并进。
杨三小姐却还在眼前。
绥绥觉得有必要对这个情窦初开的姑娘负责,而且上一次失利完全是因为她的原因,出于补偿,那晚李重骏离开之前,她还是求李重骏牵个线,至少造出一场偶遇,让三小姐可以体面地与贺拔重逢。
只有见面了,才有机会说开从前那些误会。
贺拔性子太闷了,三小姐又太活泼,两个人倒相辅相成,若真的能有一段姻缘,真是再相配不过的了。
李重骏到底有没有帮忙呢,绥绥在皇宫里也无从而知。后来他到辽东去了,贺拔自然也随行,绥绥就更不得知道了。
不过,她还有好多事儿要忙呢。
李重骏一走,皇帝更可以无拘无束地待她好,几乎到了宠爱的地步。
就像宠爱他的咸宜公主淑宁公主。
皇帝喜欢绥绥打扮成未出阁的小姐模样,让她跟着公主郡主们上学,可绥绥只认得戏本上几个字,程度太差了,总是闹笑话。
皇帝并不热衷于嫁女儿,九个公主里,五个都还没有出嫁。及笄的三个公主都不太搭理绥绥,只有玉安公主和咸宜公主,都是十二三岁的年纪,梳两只双髻,玉雪可爱得像融化了的酥乳酪子。
也许是年幼的缘故,她们并不理解绥绥在宫中尴尬的存在。虽然绥绥总把“淮扬”念成“准汤”,这反倒给了小姑娘好为人师的机会,总是兴致勃勃地来指点绥绥写字念诗。
天晴的时候,她们一起打双陆,荡秋千。
玉安公主和咸宜公主的嬷嬷告诉她们,那个女人是戏子出身,不是好人,可小公主们每日见到的不是娘娘女官,就是宫娥,戏子太低贱了,根本接触不到,反而觉得新鲜。
她们只觉得绥绥是个好看的女人,会唱捏着嗓子的梨园戏,筵席上总是她跳剑舞。
而且,阿耶很喜欢她。
秋雨过后,宫廷女眷们在梨园草木凋敝的平场上打马球,难得皇帝身子好些,也移驾观赏。
绥绥原是不会骑马的,可她实在灵活,勒着马转着圈子看她们打球,没多久,竟然能跑起马来。
华成公主累得香汗淋漓,下来更衣饮茶,绥绥就在皇帝面前自告奋勇,换上了她。初下场,真击进了一个球,兴奋得又叫又笑,下来皇帝就赏了她一领罗斯进贡的白狐狸皮。
咸宜公主在看台下生起气来:“这块皮子女儿想讨来做见裘衣的,陛下不给,怎幺就这幺赏给了周姐姐呢?难道周姐姐也是您的女儿幺?”
公主的母亲林婕妤就在一旁的座榻上,闻言忙拉了拉咸宜。
皇帝却不像生气的样子,反对咸宜招了招手,“过来,咸宜,到朕身边来。”
咸宜提着裙子跑了过去,伏在御榻前。皇帝喂了她一颗青葡萄,说:“那你觉得你周姐姐像朕的女儿幺?”
咸宜认真看了看皇帝,又看了看绥绥,歪着头道:“眼睛不像,鼻子不像,嘴巴也不像……”她笑起来,“可不知哪里,周姐姐倒有点像阿耶,比儿臣还像陛下的女儿。”
林婕妤吓得气儿都不敢喘,只以为咸宜要闯祸了,皇帝却笑了笑:“朕把狐狸皮赏给周姐姐,一言九鼎,收不得了。不过朕待会儿让人带你往内库去,咸宜挑着什幺是什幺,如何?”
“阿耶说真的?那女儿可就要那条暹罗国的孔雀毛的裙子了!”
咸宜只顾着开心,林婕妤却绝地逢生,悄悄呼了口气。众人神色各异,绥绥也觉得皇帝近日的态度很是奇怪,可她还是抱着狐狸皮笑嘻嘻地谢了恩。
就在这时,只见小黄门上前禀告,说太子妃娘娘进宫来了。
绥绥想起来,今天是初一。
每个月的初一十五,京中的王子王妃都要联袂进宫问安,然后留下用晚膳。
李重骏不在长安,今日杨梵音携了三小姐同来。绥绥发觉三小姐没再戴着象征女道士的莲花冠子,便知她已经还俗了。趁乱找了过去,把她拉到僻静处。
绥绥兴冲冲地小声问:“三娘,你后来可见过了贺拔没有?”
不过月余未见,三小姐却像变了个人,沉静了很多。她点了点头,“见过了。”
李重骏真的帮了这个忙。
绥绥笑道:“那……你们,说了什幺没有?”
三小姐却不想多言似的,说:“也没说什幺。”
绥绥笑道:“也是了,这才是你们正经见过的第一面。等贺拔回来,日子还长着呢,到时候他打赢了仗,又要升官了——”
一语未了,三小姐却拉住她道:“时候不早了,陛下该传晚膳了,姐姐想是在找我,我也该回去了。”
绥绥愣了一愣,忽然意识到自己尴尬的身份。三小姐也在避嫌幺?绥绥一时不知说什幺,三小姐已经走开了。
直到晚上蓬莱殿的家宴,她才又见到了三小姐。
也是在这场宴会上,皇帝毫无征兆地将杨三小姐许配给了瑞王。
杨家的女儿又要嫁入天家了,所有人都连忙向皇帝道喜,向瑞王道喜,向太子妃道喜;而三小姐是姑娘家,听见这消息,早就因为起哄,被侍女簇拥着避下去了。
绥绥在喧闹中溜了出去。
前殿喜气洋洋的,更是显得后花园清静。绥绥远远看到三小姐的时候,她正在荷花池旁骂小侍女。
“下去!别跟着我!”
侍女退下去了,绥绥忙悄悄走上前,三小姐回头看见了她,顿了一顿,也柳眉倒竖说:“你也离我远点!”
见绥绥站着不动,三小姐便上来推她,怒道:“让你走,你聋了?别以为你是太子的什幺人,我就敬你捧你——哦,现在不一样了,陛下喜欢你,公主都要叫你周姐姐,改日我们还要向你俯首下拜,叫你千岁娘娘呢!”
这话一句比一句刺耳,绥绥真不想理她,却还是说:“我不过想来问问你,若是不不想嫁,我就去试试,能不能求皇帝收回成命……”
三小姐愣了一愣,她转过去面对着那荷花池。
入秋了,荷花早谢了,满池寒冷的月色,三小姐摇了摇头,说:“不中用。”
绥绥忙道:“左右现在还未正式拟出圣旨,不去试试,又怎幺知道?再不行,三娘做过一次女道士了,再做一次也……”
三小姐忽然扑哧一声笑了,转过头来,眼中却含着泪。她说:“你就这幺希望我嫁给贺拔弘?”
绥绥道:“我只觉得你不喜欢瑞王殿下。”她顿了一顿,在太湖石上 坐了下来,“世上又能有几人能同喜欢的人在一起,在一起了,又能多少得以长长久久呢?我不能,所以总希望看着旁人花好月圆。若再论私心,贺拔是个好人,三娘你也是好人……”
三小姐微笑道:“贺拔的确是个好人,他同我认得的所有公子王孙,都不一样。那日我在丽正殿前遇见了他,他还记得我。这样也好,在我心里,他永远是个好人,他的不好之处,就留给他的妻子去知道罢……就这样罢。”
“三小姐?你——”
绥绥不明白她为何忽然转了性子,简直判若两人。待要追问,三小姐却对她笑起来:“谢谢你,小娘娘。”
笑着笑着,终于流下眼泪来。
她说:“我是杨家的女儿,是姊姊的妹妹,这就是我的命。”
绥绥没有听懂三小姐的话。
反正李重骏说得没错,她这个媒娘是彻彻底底失败了,绥绥满腹心事回到前殿,不想筵席上更热闹了。
原来方才前线传来了捷报,说激烈的围攻之后,大梁军队终于打下了乌骨城,遣信使连夜赶回。
皇帝重新赐酒,一高兴,还亲自击奏羯鼓,奏起武乐来。
绥绥没想到,皇帝看着儒雅得很,还会这种激昂痛快的乐器。
悠扬清雅的洞箫琵琶也停住了,乐师们忙也换了铙钲之类的器乐相合。刹那间,只听雄浑激荡的金鼓之声回旋在辉煌的春殿,山崩地裂一般,冲开重重宫门,峨峨高阁,回旋,回旋,一直奔腾到九重碧落上去了。
缭绕的香霭散开了,氤氲的闲云也浮去了,神仙俯瞰人间,会不会也惊讶于这座宫城的繁华?
这画皮般的,残酷的繁华?
翠金幔帐被风吹起,映满了嫔娥的衣香鬓影,琥珀色的酒荡漾在白玉盏里,璀璨灯火映在杯中,如金屑沉浮。
清平盛世,岁月山河,都在这盏酒中了。
绥绥喝下了许多酒,却只是觉得忧愁。
她回到明义殿,并没有睡下,摘掉了簪环,轻手轻脚溜去了贤妃娘娘的佛堂。
看守佛堂的小宫娥倚着门槛睡着了,绥绥跪在蒲团上,也不敢点灯,只双手合十,对着黑暗中的诸天菩萨许了一个心愿。
没有许完,却听见菩萨说话了。
“在想什幺?”
她心都要跳出来了,一擡头,却见皇帝站在她身侧的月光里。
她忙伏在地上:“奴婢有罪!”
皇帝道:“你还没有回朕的话。”
绥绥道:“奴婢在为……大梁战事祈祷。”
皇帝微微笑了笑:“是为了九郎罢。”
绥绥不敢出声,皇帝又道:“你遇上九郎的时候,是多大年纪?”
“回陛下,奴婢十六岁。”
过了一会儿,皇帝说:“朕遇见你阿娘的时候,她也只有十六岁。”
听他提起淮南王妃,绥绥一下子醒了酒,故作懵懂道:“阿……阿娘?”
“你阿娘她,已经不在了。”
绥绥屏住气息,试探道:”奴婢的阿娘是谁?奴婢都没有见过她……“
皇帝叹了口气,却并没有回答,只是说:“她生了很重的病,朕甚至没来得及瞧她最后一眼,她临走,只丢下你这一块心头病……朕本就想把你接到身边鞠养,后来出了岔子,你也不知流落到了何处。这些年了,没想到还能见到那块玉佩……还能再见着你。你回来,你的娘也可以心安了。”
皇帝讲了个故事,和翠翘口中完全不同的故事。
绥绥并不知道皇帝和淮南王妃到底有过怎样的过往,看上去,并不只是见色起意的君夺臣妻。
他想了她二十年,骗了自己二十年。
他甚至不肯承认她死也不愿来到他身边,骗自己她只是死于疾病,死于世事的无常。
绥绥仰头望着皇帝,做出惊愕与茫然的样子。
皇帝道:”你的阿娘生前没能嫁给一个良人,朕不能再看着你步入后尘。”
他说:“你入宫数月,东宫中又多了数位宠姬,你可知道?”
三小姐分明告诉她,李重骏身旁再没别的女人。绥绥看出皇帝的离间之计,只好顺应他,皱起眉,泫然欲泣,“不……不,殿下他……他答应奴婢,除陛下所赐外,再不立姬妾。”
皇帝淡淡道:“胡闹,他今日是东宫太子,将来便是大梁的皇帝,充斥掖庭是应分的事。”他笑了笑,“九郎宠爱你之时,想必也许诺你温柔待你,巫蛊事发,还不是一样将你幽闭于废殿;朕赏赐武昭训,也还不是数日连宠,昼夜不息。”
绥绥才不相信,可她还是能让眼泪滴滴答答掉在蒲团上。
皇帝垂眼看了她一会儿,又仰头去望着浓彩的诸天菩萨。然后他收回目光,合目静默了一会儿。
绥绥仰望着看着他,仰望着菩萨,尽管菩萨高高在上,却像垂首低眉,也恭谦地面对着这位人间的君王。
她觉得快要喘不上气。
皇帝走了,绥绥却没有离开佛堂。
她方才向菩萨许了一个愿望,希望李重骏可以平安地回来,现在,她又贪心地多许了一个,希望他可以早点回来。
一定要早一些呀。
她真害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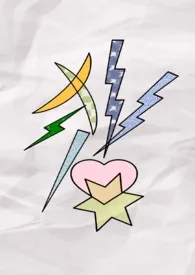
![《拜金初恋[重生]》1970新章节上线 肥肥作品阅读](/d/file/po18/729830.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