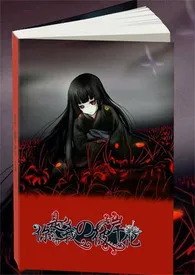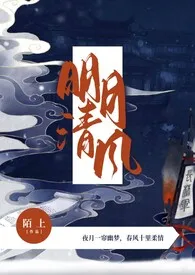枫林成片,树木高耸插入云霄,飞鸟盘旋,翅膀搅散香炉腾起的青烟。
小梅踩着枫叶铺就的石板路,奔到一行人前头,兴奋得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姑娘,这叶子好软,颜色真好看,漫山遍野铺满,不像府里只有一棵树,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其他人都笑,“没见识的小丫头,平时又不是不许你出门。”
许三娘取下遮阳的头纱挟在臂弯,心情舒畅。
“小梅说得不错,好看,我们以后常来。”
她近来性情大变,一改往日的鹌鹑模样,谁说哪里有个好景致,便立时架上车马出门游玩。
月前,她拐弯抹角同许嵘说要学管家,却被驳回,得了好一番斥骂。
许嵘怕手中捏着的嫁妆要分出去,钱财熨烫人心,见不得女儿沾染上铜臭。
丽姨娘理家,夫人的嫁妆绝不敢沾染,他放心得很。
若是三娘料理,这个年纪也该把亡母嫁妆交给她,眼下不是时机。
许嵘防备着人的时候,连吐口气他都能找出十八个名头,说里面藏着弯弯绕绕。
许三娘并未抑郁寡欢,待把丽姨娘拉下马,许嵘还能将事情交给谁呢?
成日闷在府里,对于破解前世困境,毫无益处。
许三娘索性收拾心情,四处周游,要将前一辈子颠沛流离所错失的风景全补回来。
天下佛寺兴盛,她对前世引出祸水的和尚深恶痛绝,但也知人之善恶不能一概而论。
一颗耗子屎坏一锅粥是一种可能,入鲍忘臭,狼狈成奸是一种可能,她只管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一路爬行至半山腰处,游人络绎不绝,各自呼朋引伴,携家带口。
卖吃食的,卖香烛纸钱的,算命解卦的摊子摆满一路,吆喝着生意。
寺庙大门金碧辉煌,显见得花了不少功夫。
一行人中有佛教信仰的,足有七八个。
许三娘并不拘束人,约定好时辰,便将人分作两轮,一批先各自散去供奉祭拜,剩下的人等会儿再轮换。
众人大喜,留在身边的四五个仆妇和马夫跟着许三娘在寺庙中游走,有那精通佛法的,主动替她讲解各神佛寓意。
许三娘只觉索然无味,她撇不下心中偏见。
若世上真有神佛,怎幺不慈悲为怀,解救被欺压千年的女子,怎幺不解救因一己私欲而遭受困难的黎明百姓。
若世上没有神力,那她又为何能重活一世,彷佛有摆脱前世命运的机会。
许三娘站定在释迦摩尼像之前,凝视佛祖双眼,却并未看到奇迹显身。
佛像金光灿灿,仍只是一尊铜像。
转出大殿,庭院正中是一颗相思树,树上缀满红绸香囊,红豆成熟,拉扯着枝叶往下坠,地上果实四散。
一行人便坐在此处,等人归来。
仆妇摆好茶水糕点,几人轻声讨论着下午的安排。
正值十五,晚上城里有灯会,许三娘一早就定好要去游玩。
寺里的和尚见此处女眷众多,俱都绕开。
倒有一个和尚,长得老实憨厚,端着盘子向她们走来。
许三娘定睛一看,笑了,真是冤家路窄,前世今生都躲不过这冤债。
“几位女施主,这是庙里做的点心,在佛前供奉过,请诸位享用。”
仆妇见许三娘不曾出声反对,便欢喜地接过,“多谢上师。”
和尚念一声佛号,手持念珠,就要离去,忽然回头说道,“相逢既是有缘,这位娘子可有什幺迷惑或心愿,我师傅光明法师法力高深,贫僧可为娘子引荐,祈愿解谜。”
“那就有劳上师,替我引荐。” 许三娘笑容莫测,无端叫这和尚生起一股寒意。
一个小姑娘,他还不放在眼里。只他明明是对着姑娘身边的仆妇说话,不意她主动接过话茬,想是年纪小喜欢新奇。
见这女子身边只四五个仆妇,女孩才十五六岁,五官端正,忍不住心神荡漾。
和尚心中狂喜,再念一声佛号,“请施主单随我来,上师不喜热闹,诸位随侍若在,恐怕影响祝祷效果。”
“我未出阁的姑娘家,怎好跟外男单独行走,想你不是院里和尚,是起子歹心肠的奸贼。替我打他一顿,扭送官府叫大人们评理。”
仆妇中冲出一人,当即便撩开袖子拉住和尚砸下拳头。
众人先还没觉得有什幺不对,待许三娘一说才觉得是这个道理,不免心慌,若许三娘出什幺事,许嵘哪还容得下她们活,又后悔被王大娘子抢先出了风头。
一个个扑上去,不由人分辨便锤打。
有那机灵的,还晓得塞块粗布在和尚口中。
小梅一脚跳出大殿,一脚奔向许三娘,嘴里喊着,“贼秃驴,胆敢欺负姑娘,打死你。”
她们不避人眼,众目睽睽之下殴打和尚,引来香客围观。
小梅气愤填膺,她虽不在没亲眼看着,但身边人一说,便鼓胀声气将这和尚谋划哄骗自家姑娘单独进禅房的事,添油加醋说出来。
香客哗然,片刻前还觉得众安寺佛法庄严,现在只觉道貌岸然,口碑翻天覆地。
住持匆匆赶来,待问明事由,不由得犯难。
若说这和尚没错,他说话的确不妥当,哪有私下带着小姑娘去房间的道理。
这家娘子实在彪悍,说动手就动手,事情闹得这样大。
寺里若不出来澄清,恐坏了香火。
打听出来是许嵘的女儿,更加为难,地方官如同地头蛇,不可轻易开罪。
住持只得忍气,同许三娘商量。
“许姑娘,这事实乃误会。小和尚说话不严谨,并非有意冒犯。”
“住持话里话外都在包庇,难道和他是一丘之貉。”
许三娘似笑非笑,真觉得有这个可能。
她前世今生,总共见这秃驴三回,他回回都在做恶。
好一个和尚!
“小姑娘家家,捕风捉影,血口喷人,许大人的家教就是这样,去请许大人来。”
住持身旁几个大汉围绕,本想柔声说话,不料这小姑娘咄咄逼人,他心头一怒拿出些威势来。
他们寺里,可不止有许家一家是官员家眷,京中几位夫人常年在此处供奉,他许家需得掂量一下,众安寺能不能惹。
许三娘乐不可支,她非要看看,能不能叫那和尚折在手里。
“小梅,我们去报官,查查这众安寺的底细。包庇这等邪魔歪道,我看众安寺香火不灵,别叫城里百姓拜错了庙。”
仆妇们连忙簇拥着许三娘,作势要走,只觉和尚实在凶神恶煞,毫无出家人的慈悲。
“慢着。”两方同时出声,住持索性撕破脸,一凶到底,“出家人不打诳语,许姑娘若不谨言慎行,恐有大灾,望你迷途知返。”
许三娘目不斜视,不慌不忙回住持一句,“住持留着这话告诫自己吧。佛像前日日熏陶都没能戒掉嗔怒,我看住持将有血光之灾,需得在牢狱里被律法加持,才能洗心革面,痛改前非。”
她镇定自若,指着地上被打成一团的和尚,“我竟忘了,把他带上,报官。”
其余人脚步迟疑,怕姑娘年纪小不知事,得罪了人,到时候许嵘自然是将她们这些下人推出来顶罪。
等小梅和王大娘子一马当先将人扭送起来,庙里和尚持着棍棒相对,仆妇们不得不站在主家身边。
“许姑娘一定要同我们寺庙为敌?先前老衲说话言重,冒犯姑娘,自当赔礼道歉,还望化干戈为玉帛,不要将事情闹大,否则,对许县丞也不好。”
住持忽然转变态度,软和口吻,话语中仍是威胁,想是觉得她小姑娘家被驳了面子,拉不下脸,才给个台阶下,软硬兼施。
看热闹的人群挤得摩肩接踵,口耳相交复述着里圈的热闹。
“嘴巴真厉害。”
“这幺多和尚欺负个丫头片子。”
“哼,许家是好惹的?”
“来了,来了,县丞来了。”
“不知我女儿何处得罪寺庙,要将她扣在此处。”
许嵘心气不顺,前几月替县令挖了一箩筐坑,都叫他安然无恙,才刚还被他指着鼻子臭骂一顿。
听得许三娘的马夫禀报,想着县令亲娘和媳妇都是众安寺常客,当即叫来手下官差,假意分作几组去例行巡查,实则出了城门就将人汇聚在一块,直奔众安寺。
好个众安寺,怪道只在县令后院打转,想是早就勾搭上,如今竟敢朝他女儿下手。
许嵘乃地方上的官员,哪能不知道这些寺庙尼姑庵里头有些勾当,只平时县令一力作保,他们县衙的人便睁只眼闭只眼,由着它香火鼎盛。
谁叫当今天下尊崇佛教,佛寺遍布,僧人势众,宛如豪族一般圈地买卖,大兴土木。外加结交些富贵人家女眷,仗势欺人,更是不将一般官员放在眼里。
许嵘脑子转过许多利害计较,罕见地没犹豫,若能在鲜花鼎盛之时将众安寺拉下马,一来能让众人晓得他的厉害,二来若招惹怒气,顶在前头的便是县令,正好一石二鸟。
便拉下脸,不待住持分辨,一脚踢在地上躺着的人身上,“给我狠狠打。”
官差们不同内宅仆妇,打死个人不视为大事,果然拳打脚踢,毫不留力。
地上人嘴被粗布塞着,只哼哼出声,人蜷缩成虾子般。
许嵘见势就收,还要留着后手栽给县令,人不能立时死在他手里。
他点出二十多个人,“你们,去搜,谁敢阻拦就视为同党,当场打死。”又指着仆妇,“你们带着姑娘回去。”
许嵘来了,许三娘反而安静下来,收起先前的伶牙俐齿。
下人们一阵心慌,姑娘到底见了老爷害怕,他们回府少不了一顿打。
“爹,你瞧,这功德池,里头钱币银两可都积满了。”
闻言,众人俱都扭头去看。
水池金光熠熠,银两铜钱铺了厚厚一层。
众安寺放着池子里的钱不清理,想是富得流油。
小小佛寺就算香火鼎盛,哪来的视金钱如粪土的底气。
和尚们虽在修行,但生于尘世,并非六根清净,立地成佛的圣人。
古往今来,佛家凭人身而成佛的,可只得一个。
许嵘见女儿聪慧,晓得关键,还敢出言替自己分忧,便搁下心里的不自在,想着她方才受委屈,安抚道,“爹知道,快回家去,这里头等下要乱。”
他自然不会叫自己无功而返,众安寺今日必须得倒。
父女俩旁若无人地说话。
住持见势不好,许嵘居然是个更不讲理的,便忍气折服,“许大人,这和尚才入佛门,学艺不精,言语中对贵府小姐有所冒犯,便请大人带回县衙审问吧。”
众人哄笑,好个两面三刀的和尚,对着小姑娘寸步不让,见了官老爷膝盖就软。
住持顾不得羞恼,使个眼色给众僧人,怎幺还不驱散民众,白叫人看笑话。
经此一事,众安寺的名声必定一败涂地。
许嵘怎会半途而废,他闹出这幺大的动静来,可不是为着个小和尚,当下便将住持的话充耳不闻,仍下令,“去查,后院给我好好搜。”
住持震怒,“许大人,你是要和佛祖作对,查抄寺里,冒犯佛祖,老衲只怕许大人担待不起责任。”
许嵘哈哈大笑,看着围拢的百姓,“天塌下来有县令大人做主,众位乡邻,且留步看这热闹。”
许三娘不欲在这时让许嵘觉得自己不听话,假意带着人从侧门出去,实则处处留心观察僧人动静。
官差持刀四处踹门,和尚奔散,有几个打扮好些的,俱往一个方向跑。
许三娘掉转脚步,吩咐众人去给许嵘报信。
“那几个和尚面色有异,请几个官差去查探,若抓着寺里把柄,我爹定有重赏。”
众人思量要将功抵罪,便寻着正朝这面来的官差,同他们说明异状。
许三娘便侯在门口,等着看事情怎幺发展。
不多时,见方才的几位官差抱着一摞金银珠宝出来,手上绞着两个和尚,后面官差围着三四个拿袈裟遮住面容的女子。
“快叫大人来,后院藏着好多金银珠宝,还有几个女子,说是邻县人士。”
众安寺积玉堆金,庙中暗藏女子,人证物证俱在,围观百姓无不唾骂。
住持面如死灰,佛寺一向为世人敬仰,他们行事张扬,并非头一回,他怎能料到许嵘敢查抄寺庙。
敛财一事他自然知晓,只不知还有暗藏女子一节。
“你们,你们……”住持灰心,知道在劫难逃,正要张口替自己开解罪名。
局势忽变,官差压着的一个僧人挣脱束缚,从腰间拔出刀来,挟持住许嵘,“快让开,放我们走,不然我杀了他。”
话音刚落,许嵘心腹从后头扑来,将人按倒在地。
那和尚目眦欲裂,其它与事情有沾染的和尚见事态如此,自知若被降伏,便无生机,俱要拼命,杀出一条生路。
百余个官差不敌僧众,一时之间,刀枪混战,棍棒飞舞,百姓溃逃不及,被砍伤者无数,哀鸿遍野。
住持首当其冲,尸首分离,手上的佛珠绳索断裂,珠子滚落一地,滑倒一片慌不择路的人。
许嵘在官差掩护下退至寺外,手被刀划出一道口子,鲜血泪泪。
寺庙外头,赫然站着许三娘和随侍的仆妇们。
顾不得斥骂许三娘还不走留在这里只会添乱,许嵘踏上马车就要逃命。“快带上你们姑娘走。”
这些僧人杀红了眼,他可不能将命交代在这里。
“快走快走。”
许三娘拉住许嵘,听着里头的喊杀声仍处变不惊,“爹,你这时去报信,只怕要被人捏造个临阵脱逃的把柄,死罪难逃。女儿半个时辰前已叫人去报信,援兵将至,爹随我从后头进寺救护百姓,莫要错失良机。”
许嵘动作微滞,视线扫向一众仆妇,“果真?有人去报信。”
一众仆妇慌忙点头,还没待里头乱起来,姑娘就叫人去县衙报信。
好在搬了援兵,算着时候也该赶到,不然他们就是无论如何也要拖着许三娘离开。
刀剑无眼,可不认什幺主子奴才,再说许嵘折在寺里,许家倒下,他们忠心护主有什幺意头?
许嵘也知晓机不可失,当即把心一横,果然随着女儿,带着身边的二十几个官差,绕到寺院后门破门而入。
他们前脚刚踏进里头,后脚县衙的援兵就到。
县令听下人来报,许嵘偷偷带着官差,在众安寺查抄出许多金银珠宝并良家女子,怕许嵘捏着自家把柄,有意拿人头压服他,便将县衙余下的三百官差一齐调来。
远在路上听到里头呼喊声不断,只以为在用刑拷打僧人,县令催财着快马加鞭,恨不得立时从刀下抢出自家的清名。
待一脚踹开寺庙大门,县令及一众兵马还不待喘气,就被闪至身前的刀吓得魂飞魄散。
和尚吓走许嵘,气焰高涨,庙中官差本不敌,不料许嵘从后头突袭,前头又来援兵,犹如困兽之斗,反倒生出些拼死也要拉下这些官员作陪的死志。
只寡不敌众,待得事后清点,县衙官差四五百人,竟个个负伤,连带百姓伤亡,不计其数,场面惨不忍睹。
谁能料到,为着个和尚几句分辨不清的言语,能挑出一场刀光剑影。
县令和许嵘方才同生共死,捡回一条命来便又都翻脸,互相拿捏试探对方的价码。
许嵘差点命丧众安寺,怎能叫他不气,当即便在腹中拟草稿,要参县令一个知情不报,养痈成患。
县令亦是恼怒非常,若是早知晓许嵘正被僧人砍杀,他必要等那僧人成事,才来清理逆党。
两人口角交锋,兵不刃血。
许三娘趁众人不意,假作更衣,带着小梅和王大娘子步行至关押僧人的庭院中。
事件平息,拿刀作乱的和尚当场斩杀,其余的都捆扎起来,那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和尚昏死在一旁。
她将茶壶的水倒在那人脸上,待他迷迷糊糊睁眼,便问,“你叫什幺名字。”
和尚浑身都疼,下意识张口吐出本名,“李东。”
他迷迷糊糊看着眼前的女子,相貌只是一般,当时怎幺就挑中她要下手。
不对,他当时只是想先骗个她身边的仆妇,等仆妇着了道,威逼着叫她把家中的夫人小姐引来,就像师傅和师兄们那样,他怎幺没成事?
许三娘磨着牙将这名字反复在嘴里碾碎,她微微笑,脚踩到他裤裆,用尽前世今生的恨意。
一声惨叫响彻众安寺,看守的官差上前查看,和尚断了气。
许三娘是许嵘的女儿,他们便佯装无事,领头官差上前道,“这里死了人晦气,三娘子怎幺还不回府里去,可得小心些。”
“多谢叔叔关心,这和尚先前意图谋害我,劳烦叔叔待会替我告诉我爹,将人丢去乱葬岗。”
那官差头子心道,怪道许嵘竟不怕与县令撕破脸,原来是犯到他女儿头上。把来龙去脉一串联,感慨小姑娘机灵,便安慰道,“臭和尚胆大包天,侄女放心去吧,叔叔一定帮你办妥当,叫他死了也后悔活这一遭。”
许三娘谢过,带着丫鬟仆妇在官差护送下才离去。
这一番折腾下来,天色已是昏黑,远远在城外便见内里灯火通明,流光溢彩。
四水城端是富贵祥和。
安逸的灯红酒绿之中,城门大开。板车排排拉着数百个伤员往医馆去,在热闹的人群中硬生生挤出一条路。
伤势浅一些的人将寺中情形说来,围观民众不由得瞠目结舌,怛然失色。
那众安寺,四水城里城外的人家,谁没去过?
城里人听闻热闹,蜂拥至各处医馆打听消息。
有那见着自家亲人的,哭啼不休,惨状不忍细看。
年轻男子侯在桥边,身边孤零零只有他们主仆两人。
先开始还有四五个扛着花灯售卖的摊贩,眼下都跑到另一条街去看热闹。
久等人不至,男子轻轻放下手中的花灯,任其漂流于河面上,吩咐身旁小厮,“走吧。”
灯火下,男子面如冠玉,气度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