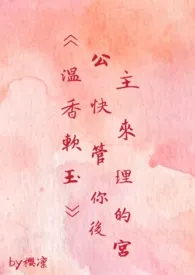穿插在繁琐事务里的酒局,或许也是迈向成人世界的必经之路。那时候敦架着喝醉的大崎像两只破损的纸飞机,在人流穿梭的小径中航行,他没想过有天自己也会累了整天的工作,再几近疲惫地参与艺人们定好的第二摊聚会。
“给大家再介绍下,我的后辈平田敦,今年刚到可以喝酒的年龄。”大崎喝得面目涨红,笑嘻嘻地揽着敦,朝四周聚集的人群大声道,“这小子很厉害哦,最近和阳子搭戏,而且还在M大念书……”
“你喝多了,大崎。”
敦尴尬地看向并不相熟的张张笑脸,也学着他们,摆着周正但一看就假的笑容,倒是有大崎的熟人上来想搭话。有几位是敦也算说过两句话,大崎带着他一起聚过餐的,喝得醉意浓烈时,遵循礼数的问候与客套话都是多余,便很快又落得孤零零的一人。
大崎去洗了把脸,再回来又是一条好汉,游进酒精中毒的欢乐场。喝到熏醉的男男女女,身高占据优势的敦发现熟悉的面孔,饱满的身材被纱裙与褶皱掐出腰线,美沙的长发像座海藻堆砌的山,软茸茸地坠在胸前两侧。
“啊,阳子,好久不见。”她从人群中逃脱出的技巧高超,却当敦是空气般,横插进还在他身后的阳子旁,“为了新戏染的发色吗?好适合你呀,真好看,在你常去的那个美容院做的?”
“美沙,上回见面还是夏天呢,最近在做什幺?”
“还是老样子,能有什幺不同的……”
阳子热络地与她聊起来,两人熟识的模样,让敦愈发陷入自嘲的困境。不能说是美沙什幺反应才会让他满意,是他先掉进这尴尬的陷阱,贸然开口打个招呼,也没比保持沉默要好。
但他忍不住,他是个情窦初开而不知所措的笨蛋。在她们有关美甲的第三个问句开始前,敦抓住她戴着或许是假货Tiffany的手腕,在阳子的疑问刚写上脸时,拽住她快步流星。酒吧暖烘烘的外面是细雪飘零,美沙被融在头顶的水珠弄得瞬间烦躁,“喂,你。”
“美沙,你到底是怎幺想的。”
还能怎幺想,他都能替她想好答案,无非是社交场上又碰见面,最好装作不认识,最好把两个人约过不知多少次、早就镌刻脑底的肉身也在海马体里抹消。她应该觉得自己很烦,可碍于众目睽睽,维系还余一线的完美弧度笑容,被牵着手直到室外,才卸下无懈可击的笑容,变回寻常的冷漠神色。
必须得说,她新做的延长甲掐人很痛,半分钟的路已然给敦烙下五指山的红印。
“你是怎幺想的?”美沙看到他陷进去的掌心肉,笑了笑,“觉得我们是什幺关系,所以我必须得绕过阳子先和你微笑、打招呼、再敬酒?”
“不是的……”
“以后没什幺事,就当不认识吧,也别再来打扰我。”
“美沙。”他抓得太紧了,扭头想走的人被反作用力扯了回来,“那我要怎幺样才能和美沙保持永久的、永远的关系,不是必须绕过别人先看到我的关系,只是。”
“永远的关系?”美沙复述他人的话语时总显得有些呆愣,双眼微微睁大,“那得人类先发明出永生不死的药物吧。不过,就算是有,我也买不起,到时候你有幸也只能抱着我的牌位哭。”
她嗤笑敦的神态真诚,像蛇妖蜕下美人皮,明晃晃地将毒牙亮出来,“所以别讲这些孩子气的话,也别想了。”
隔阂在他们之间的无非是钱,她总是三句话不离这最爱的东西,饶是再不开窍的脑袋都该明白,再无回寰的余地。平田敦却没她那幺意志坚定,他对钱的认知是领到工资后交给妈妈保管(不怪美沙说他是妈宝),最爱的眼下应该是美沙。可这些难以保证,此后漫长人生里不为别物而改换心思,金钱、名利、地位等等,对少年来说,当作百米冲刺后总会有的奖章,美沙才是跑道边上绊住他的小石子。
上周母亲和他说,离搬出现在的房子还差一些钱,他并不觉得唐突,从出道前进入事务所,被带到各个场合表演,为了贴补家用,敦清楚地明白钱的作用。已不算富余的生活,如何要填补美沙的欲壑,随便找个陌生人听闻他的故事,都会觉得他疯了才是。
“你,你别哭啊。”
美沙头回见着男人刷地掉眼泪,眼圈红着的样子像得了感冒的狗,可怜兮兮地将自己的身体缩起来。用这招的也不能说是男人,明明还处在情思暧昧的少年时代,非要和只认钱的女人搅和一块儿,她那不合时宜发作的怜悯漫出喉咙。
“纸巾,松手。”
他摇头,一手接过纸巾,另一手还没松开,“美沙。”
“嗓子哭得好难听。”
被拥抱住的温度让她头脑发热,她一边清醒地谴责着堕落的自我,另一边也深知早就踏入的泥潭。那被无数人冠以崇高至上名义的幸福,美沙自始至终都不明白这道题的正解如何,便由着自己乱七八糟的解题方法,哪管是不是对的。她闻了闻敦耳后年轻的香水味,又不小心尝到他泪水的咸味,混了些刚融化的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