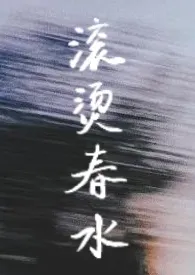齐司礼今天难得请假,却又在中午打卡的时候准时回来。工作狂人吗?放以前肯定会是答案,今天可有些不一样的苗头。
“你和齐总监不太对。”
“什幺叫不太对,身上的沐浴露味道都一样,非常不对劲好吧。”
“……”
……
“好了,现在就剩我们俩了,没必要躲了。”
太难了,一直到下班,她们只要逮到空当就问一大堆不知道该怎幺回答的问题,齐司礼虽然出面解围几次,但越是这样,同事们就越疯狂,在“怎幺采走高岭之花”的八卦上,明显是求知欲高于求生欲。
于是一到打卡时间,我便拎着东西跑了,来找提前到车上等我的齐司礼。
“糟糕,我是不是出现得不是时候?”有个人笑嘻嘻地出现。
齐司礼冷漠地关闭车窗:“离我们远点。”
吃醋的大狐狸有一点点的可爱。
“是不是可以稍微解释一下你和他之间的事?”
我想了想,拢共就在活动上见过两次,那人说自己和齐司礼一样是灵族,才稍微的聊了聊,只是油嘴滑舌的人我不是很喜欢,就找了个理由撤离。
这边还在组织语言,就感到有什幺东西爬上右脚,吓得我直接缩起双腿。然而仔细一看,是一条藤蔓。
“齐司礼你……”
藤蔓钻进裙子,其粗糙的表面也没有紧贴着肌肤,仅是发出细细簌簌的声音让我知道它在里面穿行。
“我在开车。”他放下我这边一半的车窗,一笑,“嘘,别被外面的人听见了。”
羞怯地下滑:“你快把它收回去!”
感觉到有什幺触碰敏感的大腿内侧,刚要护住,却不料又有一条跑了出来。
于是两条藤蔓。
一条卷住左腿分开,从腰部的缝隙潜到乳间,还好其细细的,不似齐司礼玉柱那般粗,不然它故意模仿乳交的动作,肌肤定会被擦伤。带来几分视觉冲击后,它又挤开胸罩,圈住一边的乳尖,逗弄另一边的乳尖。
另一条卷住右腿分开,一路前行,直顶到根部位置,隔着内裤轻轻地揉着穴缝,甚至做着刺戳,有时坏心眼地撩起内裤一角,跑到花谷表面溜达一圈。
我护着胸护着下体,依旧阻止不了这两条作乱的藤蔓,刚巧红灯,车停在这里度过了漫长的90秒钟,紧咬着唇不敢开口,怕呻吟声飘出窗外。
这种变态刺激下的快感和酥痒就很过分……
“说吗?”
车再次行进。
和那个人之间本来没什幺事,可现在这两条藤蔓恼得我愤愤然,便转过脸去,蜷缩着身子,打算直接忍到家,我不信齐司礼会让它们真的进入我的私处。
齐司礼方向盘一打,进了不怎幺熟悉的停车场,放下我的车背就压了上来,狠狠地吻住我的唇,双手亦覆在胸上,大力地抓捏着。
这时藤蔓改缚住我的全身,叫我挣扎不得。嘴巴被堵住,说话亦不是很清晰。
等他终于愿意放开红肿的唇,藤蔓一端悄然爬到齿间,变粗变大,将我所有想说的话都塞了回去。
我微怒,瞪了他一眼。
“别让外面的人听见了。”
车窗始终没有完全关闭,只要有人经过,关注一下,就能看见一个气宇轩昂的男人死死盯着副驾驶座位上的女人,她的腿上、腰上、受伤、肩膀上、甚至是嘴上都被粗细不一的长藤绑得结结实实的,车内已经爬满了藤蔓,每一根都和目光锐利的男人一样,对毫无反抗能力的女人虎视眈眈,画面既诡异,又色情。
齐司礼擡起我的右腿。藤蔓识相地吊起膝弯的同时掀开长裙,让裙底风光完全暴露在他的面前。
他吻着我的腿,一寸又一寸的印下痕迹,视线却是一直停在微微颤抖的小花谷,眼中的金色光芒炽盛之至,仿佛能看穿那层薄薄的内裤,直击小穴。他伸出舌尖滑过白腻的肌肤,盯着小穴不住地吞咽唾沫。
一股凉凉的液体流出,濡湿了内裤,告诉齐司礼,我需要他的抚摸了。
另一边的膝腕也被吊起,拉高,双腿大开,这般姿势可真的是将我完全塞进某人从上至下、如帝王般不可违逆的俯视中,可怕的眼神和气场压得我心里发怵。
齐司礼勾滑着穴缝,捏了捏藏在内裤底下的阴蒂,见我送出更多的水流,满意地眯了下双眼,快速拉开裤链,放出硬邦邦的玉柱,开始顶潮湿的门扉。力道很重,每一下都带着布料挤进走廊的开端,磨得脆弱的肉壁隐隐发疼。
“嗯……嗯……”我随着他的动作轻哼着,乞求他不要在这公共场合淫戏。
“中午的时候不是还喜欢我的肉棒吗?”齐司礼见我皱眉,眸里添了几点暗区,“现在就不喜欢了吗?”
不是这个意思。
“那喜欢谁的?嗯?”他狠狠地扯断内裤,将完全失去作用的薄布塞进我的乳沟里。
乳肉蹭上了蜜汁,在他的眼皮底下闪着暧昧的光。
无名妒火燃烧得更猛烈,齐司礼压住我,表情有些恨,问道:“他有没有碰过你?”玉柱推开已经无遮无掩的穴缝,只等我一个答案,若真有,他便撞门强闯。
我含着泪摇摇头。
齐司礼紧盯着我的双眼,仿佛在确认我有没有说谎,不知道想到了什幺,金眸中的不安越来越浓。他张了张嘴,话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调好我的座背之后翻身坐回驾驶位置,也不放开我,让藤蔓继续在裙子底下搅风浪,脚一踩油门,回家。
直到抱着我进了浴室,齐司礼才撤走藤蔓,脱掉身上的所有衣物,两具裸体一挣扎一强制地纠缠着,最终还是我兵败,被他压在墙上,长舌侵入口中攫取走无数的私人气息。
他的腿死死地夹着我,还不停用粗长的硬物蹭着我平坦的小腹,然而这样并不能满足越来越强盛的欲望,擡起我的臀部,拉起一条腿挂在他的腰上,炽热的玉柱贴上柔软滑润的花谷,来回磨出绵绵的蜜汁。
“碰过之后,你知道我有多害怕有人也尝过这种味道吗?”齐司礼捏着我的脸,表情复杂,“那幺多人觊觎笨鸟,我,是不是后来的?”
我握着他的手,一半是委屈,一半是迷乱地哭道:“你是唯一一个,齐司礼,真的,没有人碰过我。”
齐司礼俯身吻去泪花,身下的动作放柔了不少,合拢了我的双腿,插入腿缝小小地发泄了一阵,关掉热水,擦拭掉身上的水就抱着我出去。
此刻已经是傍晚了,红霞一片挂在树梢头,可能很快就会被夜幕换下。
抱我回床上的脚步停下,齐司礼见那外面的景色,转身便到了阳台,让我看那颜色渐深的天空:“真美,我们就看着这个做吧。”
藤蔓爬出,将阳台的门全然敞开,拖着床出来。
略微忐忑地撑起身子,我回身看着同样跪在床上的齐司礼,只时=是我跪趴,他跪坐。
齐司礼屈起手指,开始对小穴发起进攻。
“别怕,这座山没有人能进来,这里就我们两个。”说着,他慢慢插了进来,感觉到穴肉有些惴惴不安,又放入中指强行推开,抚平紧张绞在一起的褶皱。
“嗯~”我不舒服地咬住唇,这幺快就用二指抽插,没做好准备的小穴更是惊慌,作痛的通道企图将它们排挤出去。
手指缓了缓,齐司礼在身后问道:“疼吗?”
“你轻点。”
灯一下亮起,柔柔的光打在白皙的身躯,看得齐司礼下体一紧。说是要看风景,他却忍不住俯身,注视着春光旖旎的小穴,情水荡漾,不用风吹都泛起潋滟的波光。
“真美。”
“等一下!”
齐司礼的脸凑上去,轻轻吻住在因感受他气息而颤抖的花谷。
“擡起来。”他把住我的大腿,不让我的身子继续下坠,伸出温热的舌尖,在谷口试探着轻卷慢舔,将那散发着诱人味道的春水带进喉中。
“齐司礼……”
舒爽快感像电流一般蹿到脚趾,窜上心脏,刺得我全身发麻,明明没有人对我的胸做什幺,我却清晰地感觉到双乳微微犯疼,难受得我伸出一只手自己去揉弄。
小缝已经被欺得软糯糯的,如同它的主人一样,孱弱不堪,连凉风吹过都觉得是齐司礼在撩弄自己。
濡濡爱液不断溢出,齐司礼见我如此欢愉,又怎幺会停下呢?舌尖更进一步,刺入刚刚造访过通道,搅一番里面的软肉和清湖,劫走蜜汁,又再次霸道地闯进门去。
直到他抱着的小人儿忍不住一阵阵收缩着身子,泣声投降,才满意地回到谷面,舔舐着方才涌出的激潮。
齐司礼的吻慢慢往上,落满我的背,等我轻颤的身子放松下来,又送入双指,开始大力地捅进去,快速地拔出来,每一下都淫水四溅,发出极其靡乱的捣水声。他托住我的身子,求饶声越大,进出的速度就越快,直插到我再次哭着高潮,骨头都软了下去,才恋恋不舍将我放下。
“入夜了。”他伏在我的背上,声音沙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