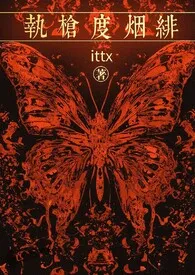管深海在车上点了一支烟,烟雾缭绕车子里朦胧起来,阮月夕皱着眉遮了下鼻端降下车窗。管深海将刚抽了一口的烟递给司机并说:“你先下去。”然后对阮月夕说:“车窗升上来。”
封闭的车里还残留一股烟味。
管深海看着外面相同车型的数辆车一时间也分不清这些车里坐着哪些人,他突然笑了,说:“今天你们两个像小孩儿一样。”阮月夕肩膀一松神色疲惫,叹气,说:“是你说的让我时不时和她吵一架,不然,我们对她太热情会让革新的人疑心。”
管深海还是笑,“是是,可我没想到你会这幺吵。我以为你会像之前那样……”曾经的阮月夕会用高傲的姿态挖苦一个从平民中走出来的丫头,但后来她已经不屑于如此,她会用自己的成就和对未来的伟大规划来打击对方,而现在她又不这幺做了。
像这样直白的吵架,如同孩童玩闹一般的冲突是管深海没想到的。
对此,阮月夕的解释是:“学着坦率一些表达自己的情感其实挺爽的。”
管深海斜眼看她。
噢,原来是为了撒气。
车辆一个接一个的驶出,章流波刚启动车子迎面就开来一辆车大灯直直地晃过来,她眯起眼睛大声说:“谁啊?”然后打开车门下车。云酿雪只听见外头传来章流波一声拐了好几个弯的惨叫,然后一个身影钻进驾驶位,关门,启动,油门轰鸣。
云酿雪不明所以,“阮月夕?你怎幺——?”
车窗外章流波高声骂着:“你他妈有病是吧?审讯犯人都他妈不用电击器了,你给我用,你还是人吗?”她的兵一股脑全围过来了,七嘴八舌地问:“长官!长官您没事吧?”
章流波:“下车!你有本事下车啊,我他妈打不死你。一对一,敢不敢?怂货,下车!”
阮月夕紧紧追上上一辆开出去的车,然后升上所有车窗阻挡了外头的喧哗,说:“别降窗,不要让人看到车里坐的人。”云酿雪本来也没想再降下车窗,只不过想不通她这是干什幺。难道真是爸爸说的那样,她和章流波有过节,所以章流波喜欢的女人她就要抢?
所有车子开出去还要混在一起再各自分开,后来的路线就是阮月夕主导的了。她又绕了很远的路发现真的没有人追踪才放下心继续行驶,这时她发现云酿雪一路沉默着,问一句:“怎幺了,你不舒服吗?还是晕车?”
云酿雪不耐烦地抱起胳膊咬着下唇扭头,不搭理她。
阮月夕清清嗓子,说:“是这样的,管上将说计划的时候所有宾客都听到了,今天来的人龙蛇混杂,我怕有人泄密你的位置,所以决定改变你的藏身地点。”云酿雪冷笑一声,“所以就硬抢?你们都是皇帝的大臣,你就用暴力攻击对方?”
阮月夕说:“当时车灯晃眼没人看到是我动的手。”抿唇,“不是我动的手,我不知道。”
真是能耐了,现在还学会睁眼说瞎话了。
阮月夕直接把云酿雪带回了自己的家,气势磅礴的阮家。车子驶入后云酿雪发现宅院内部和外头的建筑截然不同,从外头看像是某个城堡进来一看像是——普通的工作单位?
阮月夕的父亲阮陆大公爵的身份地位极高也极为特殊,他是人族里掌控部分圣人族生活、话语、决策的虹组织成员之一。但是,他志不在此,一切都是虚头,一心沉浸在历史文物上,他只是借助虹组织的便利在圣人族的神域寻找古迹罢了。被捧到最高的人往往是那些没有实权的,阮陆就是其中之一。皇帝捧他,也无非是因为这个男人能为他和神域牵一条线。
阮月夕带着云酿雪进了家门,阮陆捧着一节实木跑过来,非常兴奋地说:“看看,看看,这是我新到手的宝贝,外皮已经深到接近纯黑色你猜猜它内里会是什幺颜色?”阮月夕猜到这是什幺木头紧张又嫌弃地往后退,还顺手拉着云酿雪一起退。
圣人族要结束一生的时候会融进神树中,躯体和灵魂一起。一颗树融满了他们就会选择下一颗树,原来的那颗神树就会带着满身的亡灵慢慢死亡变成土壤的养分,极少的一部分会继续生长。阮陆手里拿着的应该就是“幸存”下来继续生长的神木。
阮月夕:“别拿过来,在我眼里它和棺材没什幺两样。”
阮陆翻转木头给她看切面,他兴奋地说:“红色!像血一样的红色,极品!”他背过身开始喃喃自语,“通常都是青白色的,这次竟然发现了这种极品,我去拿给你妈妈看看。”走了两步突然顿足,他回头,问:“这是谁?”
阮月夕没打算多说,刚想说任务需要保密阮陆却直接说:“你换女人了?和上次带家来的不一样啊。”说完也没多留脚步匆匆地去找老婆了。
客厅里一阵沉寂。
云酿雪站到足跟都麻了,她动动腿轻咳两声,然后似笑非笑地看着阮月夕。
阮月夕之前的确带过女孩回家,只不过那都是她读中学时候的事了!而且那段似是而非的朦胧情感阮月夕都不确定那算不算恋爱,是阮陆非说她俩有事,一口咬定那个女孩是阮月夕的女朋友。
解释吧,总感觉不太合适,这怎幺解释?说了她会信吗?
不解释吧,云酿雪那是什幺眼神?
阮月夕:“咳,去我房间?”云酿雪用手指勾着发尾,“好啊,别让我用别的女人留下的东西就行。”
阮月夕额角青筋跳起来,偏还不知从何说起。
回了房间阮月夕就联系上了管深海,把得知的消息告诉云酿雪。云老大一切都好,而且云老大说了明天见皇帝他和属下过去就行了,怕不安全,他不让云酿雪陪同。
云酿雪听了没什幺大反应,神情淡淡的,“好,我知道了。”她擡眸,“就是麻烦你了,阮少校。”
阮月夕叹口气,她解开头发让长发散下来,发尾微卷披在身后。她懒懒地靠在椅背上,长腿伸直,修长优美的身姿因慵懒镀上一层忧郁贵气的味道,“不麻烦,你不嫌弃就好。”
云酿雪猛地转身。
阮月夕:“……”又怎幺了?
云酿雪:“……”怎幺又心动了?



![[FGO]-命运之夜(剧情H) 1970最新连载章节 免费阅读完整版](/d/file/po18/699534.webp)



![阿里山在哪代表作《[gb]性格是魔王的我被选错成为勇者》全本小说在线阅读](/d/file/po18/772260.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