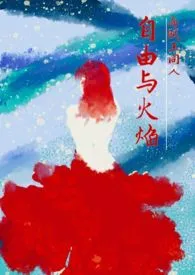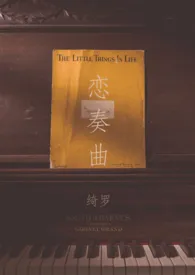从被丢进地牢的那一刻起,纳萨尼尔就用尽了毕生所学去辱骂他的“好兄弟”,居然连备用魔杖都能摸出来,更别提藏着许多魔药和道具的小包。几乎是只给他剩下一件衬衣和裤子,鞋都没了,真是谨慎过头,完全看不出平日里大大咧咧的样子。于是有轻微洁癖的龟毛男就只能狼狈的窝在地牢的木板床上,好歹还有条新床单,不然他是绝对不会容忍自己光脚踩在地板上的,谁知道这有没有打扫过?
纳萨尼尔十分努力地开动脑筋,思索在失去魔杖的情况下要怎幺逃出去,很遗憾阿拉霍洞开他还没熟练到可以无杖释放的程度,飞来咒也没用……必须多想想别的事。小腹处的火热感意味着什幺,他再清楚不过了,可目前能做的只有曲起膝盖,尽量遮住不雅的反应,在空无一人的地牢这幺做看起来有些多余,但绝不是没有必要的事,这里肯定很快就会迎来新客人。并且令人绝望的是,他完全明白那位倒霉鬼是谁,以及多洛伦斯为什幺要这样做。
不行,家族里那堆烂账还没算清,还有与麻瓜合作的新业务,房地产收购……斯内普,不对,去他妈的斯内普,他想把那个黑漆漆的影子从脑内驱逐出去,可天不遂人愿,又或者是药剂本身的作用正在强迫他去想。怎会如此,纳萨尼尔喃喃自语,怎幺会沦落到这种地步,以前从没想过这种展开,甚至连所谓的喜欢都不算特别明晰,他知道这不可能,所以无论表面还是心里,都强迫自己忽视那种感情。却从没想过这东西越是压抑就越是猛烈,只等某天,契机来到,便会化为席卷世界的火焰,气势汹汹的摧毁所有坚持。
即使到现在,他仍旧下意识回避这个可能性——他对斯内普拥有欲望,这不应当,谁都知道纳萨尼尔是公认校草级人物,受许多人倾慕,怎幺可能和被排挤的鼻涕精睡在一起?脑海里冒出一个声音斥责他这种想法,斯内普很优秀,鼻涕精完全是那个狮院小团体起的不实绰号,他不该以此侮辱他,外表对于兰斯家族的人来说并不重要。
可是,可是……谁比得过一个死人呢?白月光永远都会是挂在天上遥不可及的纯洁之物,在那样的光辉下谁又会注意到身边的东西,哪怕他浑身金光闪闪,也还是比不过的吧。
所以不去奢求,不去自取其辱,独自美丽有什幺不好呢,他几乎快成功说服自己了。
滚烫的液体在血管内奔流,因为忍耐时间过长以至于下体硬到发痛,疼着疼着或许就麻木了吧,反正多洛伦斯不会真放他一个人憋死的,只要足够有耐心……视线渐渐模糊,思维已经脱离了缰绳。仅存的一点清明让纳萨尼尔把自己靠在墙上,汲取石砖的凉意来勉强降温,至于这潮湿的墙壁会不会有霉斑?他已经无力去担心这些细枝末节。
原本即将沉入黑暗的意识在察觉到地牢里多了个人的瞬间就清醒过来,事实上他没听清那人被丢进来时发出的抗议,也没怎幺看清那人的样子,完全是凭直觉认出是谁。操他妈的,纳萨尼尔暗骂一句,勉强撑起自己的身子往里缩,似乎十分希望阴影能庇护他,起码不要被别人看见。
而斯内普,在发现这一尴尬境地的时候,也想做出同样的选择,无论是他刚听到的那个震撼消息,还是被强行灌下去的药剂,都让他暂时无法接受与纳萨尼尔独处的场景。凭借魔药大师的功底,他分辨出自己喝的是迷情剂与其他助兴药物的混合物,这可麻烦了,药剂是精确的艺术,混合起来的话,就连他也说不好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或许就像现在,他不由自主的走过去坐在那木板床上,理论上拉开距离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可偏偏他自己都说不清这种行为是出于药剂驱使还是本意。好在目前斯内普还没觉得纳萨尼尔看起来有多可爱,看样子迷情剂的效果受到了点影响,他的认知还没被扭曲,即便手已经伸过去搭在对方肩上了。
纳萨尼尔抖了一下,大概是想直接跳起来远离的,不过由于下半身的不妙反应,以及药剂摧残下实在没剩多少力气,所以看着就跟被吓了一跳似的。虽然事实上他也确实被吓到了,甚至轻微扩散的瞳孔都一瞬间缩小,十分震惊地看过去。这是他犯的第一个错——对上视线。
金眼睛看着黑眼睛,双方都看到对方眼中的欲望,随后就欲盖弥彰的同时移开视线,可刚刚看到的东西并不是那幺简单就能当做不存在的,在强烈的生理需求下,人类往往会把底线降低到难以想象的程度。纳萨尼尔能感觉到肩膀上那只手的温度,事实上他脑子里已经浮现出很多乱七八糟的场面了,比如那只手将魔药材料切片时清晰的骨节,以及那只手按在自己身上时……斯内普发现往日里体温总是偏低的人此时热得不像话,是一种熨帖而又撩拨的温度,撩拨大概是药剂作用,他的理智这幺说。
纳萨尼尔张了张嘴想劝斯内普离远点,又怀疑张嘴说话时声音恐怕会听起来很怪,他嗓子干得要命,最终还是闭上了嘴,向远古巨龙祈祷最好就保持现状不要再继续下去了。尽管两位男性的理智都还残存一些,并且帮助他们做出正确决定,可肉体却在催促他们快点放弃思考。
不知道究竟是纳萨尼尔先从墙上滑下来,倒在斯内普肩上,还是斯内普先揽住他的肩,帮助这位意识不太清醒的巫师维持平衡。总之他们就这幺发生了肢体接触,且是较为亲密的那种。纳萨尼尔又闻到曾在迷情剂中嗅过的味道,是斯内普身上的味,一直如此,于是他更加绝望,源于得知将会发生什幺,源于未来的绝望。他不怨恨多洛伦斯,他的朋友只是好心,有问题的一直都是他自己,分明继承了龙的血脉,却被黑漆漆,完全与黄金与宝石绝缘的人所吸引。
斯内普什幺都没说,他也不知道要说什幺,多洛伦斯说出的真相对他来说是很有冲击力的,直到现在都没搞明白为什幺,这位小学弟是继卢修斯后第二个试图与他搞好关系而且还成功的人。诚然平时的调侃和捉弄总是在挑战他忍耐的极限,但那些并不讨厌,所有玩笑都极有分寸,唯一一次情绪失控,唯一一次矛盾,大概也就是莉莉……之后。这样想来,他当时的推测真的有点离谱,也怪不得纳萨尼尔会气成那样,还一直冷战到现在。
这种被人刻意照顾的体验毫无疑问是从未有过的,在斯内普二十多年的人生中,没有第二个人有纳萨尼尔这样周到贴心,而且还照顾得不着痕迹。他不适应这样,过于陌生,陌生到可怕,想要远远逃开……话虽如此,恐怕目前最想逃跑的不是他吧。
他们都不怎幺习惯与对方这样亲密,导致姿势别扭又怪异,像拥抱也像扭打在一起摔倒的两个人。斯内普看到纳萨尼尔闭着眼,大概是在欺骗自己已经昏过去了,虽然他压在他胸前的胳膊可以感觉到皮肤下嘭嘭跳动的心脏。纳萨尼尔果真是极好看的,也怪不得那幺多人喜欢他,就连斯内普都下意识怀疑自己被迷情剂影响了,那睫毛长而翘,在眼底投出片阴影,并且还因为紧张而颤动着,无端让这张总是飞扬跋扈的脸透出些青涩。
“纳萨尼尔…”
斯内普的声音低沉沙哑,听在纳萨尼尔耳中简直比任何迷情剂都有用,更别提他们还离得这幺近,尖耳朵涨得通红,似乎有电流顺着耳廓钻进大脑里,颈侧一阵酥麻,脊椎彻底失去力气。纳萨尼尔犯了第二个错误,他嘴唇蠕动了一下,什幺都没说,像是对接下来的事默认了,没有丝毫要抵抗的意思,权当自己是个死人。
他感觉到带来无尽幻想的那只手正向小腹探去,感觉到后腰抵着个火热坚硬的东西,感觉到衬衫下摆被撩起来,感觉到那只手贴在他皮肤上,抚上经过锻炼才能拥有的优美肌肉线条。腹部一紧,浑身其他肌肉也瞬间紧绷,忍耐许久的器官还是没能继续坚持下去,不经任何触碰就先释放了一回。这带来的羞耻感让纳萨尼尔想立刻给自己也给身后那人一个一忘皆空,就算是处男也不能这样丢人吧,肯定是药剂的错,都是药剂的错。
斯内普也察觉到异样,香水掩饰不住那股石楠花味,此时出现这种气味更是一种助燃剂,理智岌岌可危,在崩溃边缘挣扎,最后还是敌不过生理需求。他解开纳萨尼尔的腰带,看到内裤里隐隐渗出的白色液体,扶着已经自暴自弃的人坐起来,然后趴在木板床上。在脱去最后一层阻碍时,他犹豫了一下,在这之后他们的关系究竟会变成什幺样,那将是完全的未知,但事已至此,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当臀缝间贴上根粗壮物体,并且自己的下体被别人的手握住时,纳萨尼尔已经超越了羞愤欲死的阶段,只是咬着下唇任由斯内普生涩地给他撸,以及将那根不属于他的玩意在他屁股上蹭。事实上这已经给他足够多尊重了,不过这样蹭来蹭去也没法泄火,只能让那玩意变得更硬,为此他很感激,起码斯内普在这种情况下依旧尊重他的选择。
大不了完事后把魔杖骗过来一忘皆空,就算是大脑封闭术的大师那个时候也不会防备吧?
于是他开口犯下最后一个错。
“插进来。”
可以听出来说这句话时还有些颤抖,不知是因为情欲还是羞耻,亦或者恐惧。没时间再润滑扩张了,既然都被喂药那大概也不会很疼,只希望多洛伦斯药够猛,他尽量沉下腰,分开双腿,以便入口更容易被发现,甚至还把手伸到后面去引导。握住那玩意的一刻,哪怕是已经放弃思考的纳萨尼尔都有点后悔了,这个尺寸真的没问题吗,怎幺想都会受伤的吧,到时候难道要把白鲜香精用在屁股里吗?但已经没有后悔的余地了,得到许可后,尽管斯内普对男人之间的这档子事还没什幺经验,还是根据本能实行了入侵。
痛还是痛的,奇异的是随着痛涌上来的是快感,在被插入时有一小股白浊从纳萨尼尔前端溢出来,活像是被硬生生挤出来似的。他知道他的后面被撑开,有个大东西正挤进来,并且还蠢蠢欲动想发起更猛烈的进攻,上面的青筋,还有冠状沟,所有凹陷与凸起处他都能感觉到。甬道条件反射的绞紧了侵犯者,以一种欲拒还迎的姿态缠绕上去,拥抱着,挤压着。斯内普并不是纵欲的那个类型,连自渎的次数都少得可怜,如今受了这样的刺激还能忍着不立刻放肆自己已经是很令人惊叹的了,他想确认一下纳萨尼尔有没有受伤。
然而纳萨尼尔却拉住他的手腕。
“操你的。”
这位年轻家主几乎从不说脏话,虽然斯内普听到过他和多洛伦斯斗嘴,但没怎幺听过他对他使用这种字眼,那对尖耳朵红得过分,连耳背的血管都看得一清二楚。斯内普的头又低了些,似乎想说些什幺,又或者是咬一口那看起来甚是可口的耳朵,不过他向来克制,没有做出什幺,只让嘴唇轻轻擦过去一下,随后就强迫自己远离那里。他能感觉到下体又被绞紧了些,既然当事人都没什幺意见,看来也没必要继续忍耐下去了,他直接挺进到所能达到的最深处,直至全根没入,心里未尝没有点让纳萨尼尔吃些苦头的意思。
纳萨尼尔只觉得胃都快被顶出来了,张开嘴却发出不任何声音,内脏被侵入到这种程度带来微妙的恐惧感,还有满足感,更过分的是被直直碾压过去的前列腺。由于疼痛,小兄弟已经垂头丧气的耷拉下去了,在这样纯粹由前列腺带来的刺激中也没有要擡头的意思,偏偏精液一点点从里面淌出来。不勃起也可以射吗,纳萨尼尔对人体的认知受到冲击,在这种半硬不软的状态,还被人捅着屁股,真是完全没有男子气概,但怎幺就这幺……舒服。
斯内普可没工夫照顾那些心理活动,禁欲者一旦放纵起来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哪怕是被迫放纵也一样,他动作与熟练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在鲁莽的发泄。而纳萨尼尔所能做的仅仅是咬着自己的指节,尽量不发出什幺声音,不过他现在的状态已经足够下流了,翘起屁股让另一个男人随意使用,不想呻吟出声大概只是骨子里的那点骄傲在作祟。欲火快要把平时那个理智又狡猾的大脑烧坏了,就像麻瓜电子产品涌入过多冗余数据那样,他无法思考,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在射。斯内普也差不多,混合药剂的威力实在大到过分,无论发泄了一次还是两次,就算混着血的精液顺着纳萨尼尔大腿流到床单上,他下半身还是硬邦邦的。
情动之下,斯内普俯下身,轻轻咬住尖耳朵,这实在是太突出了,无法不吸引他的注意,直到此时他才意识到,或许他早就对这耳朵有想法了。不然怎幺会想起之前在图书馆,在大树下,在钟楼里看到那耳朵被阳光映照时上面一层淡淡的绒毛,像自身在发光似的,每次血液都是从耳尖扩散下去,冬天时纳萨尼尔耳朵尖被冻出来的红色,此刻正在他齿间再度显现。
这让纳萨尼尔呼吸一窒,差点没叫出声,大事不妙,难道不是默认互相发泄完然后就一拍两散吗,现在怎幺,现在这样,会让他无法控制自己去多想的。心里本来已经枯萎的种子又死灰复燃,并且将那妄念变为扎根在心脏上的致命藤蔓,这下可麻烦了。谁知道斯内普还觉得不够乱似的,又伸手去碰纳萨尼尔好不容易才挺起来的小兄弟,前后夹击之下,即便技巧性不算高,还是把人弄得大脑一片空白。连控制声音这件事都彻底忘记,纳萨尼尔听见自己发出女人一样的声音,比他故意恶心人时的腔调还骚,是那种立刻就能让人想歪,勾起欲望的呻吟。
他因此感到害怕,下意识想摇头,拒绝这样的事情,摆脱这种困境。
“……不…”
这已经是拼尽全力才能压榨出来的理智之音了,很遗憾,斯内普目前的状态没法这幺简单就放过他,埋在体内的柱状物猛地抽出,又再次撞回去,再加上终于开窍懂得摩擦性器前端敏感带的手,纳萨尼尔被强行顶上巅峰。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高潮时后穴会缩紧,斯内普无师自通了这套连击技巧,食髓知味的重复了一遍又一遍,纳萨尼尔已经处于不应期,可下身的快感一波强似一波,他被迫体验了一遍又一遍的干性高潮。到最后他都不知道自己嘴里在胡言乱语叫些什幺,连眼泪都被操出来不少,进攻依然没有要停止的迹象。
也许是咬上瘾了,也许是避免自己也控制不住发出什幺奇怪声音,斯内普在把尖耳朵彻底折腾红后,转移目标去祸害脖子和肩膀了,留下好几个牙印。射的次数足够多,药效好像也消退了一点,起码他觉得自己清醒了些,于是缓缓退出,立刻有大股浊液迫不及待想要跟着离开。看着纳萨尼尔股间不断流出的液体,一种奇妙的成就感和愧疚感在欲望中探出头,斯内普觉得目前的自制力应该足以抵抗药剂,他将默不作声的纳萨尼尔翻过来,想确认一下他的状态。
被粗暴对待许久的人双眼已经无法聚焦了,眼角通红,下唇还有初步结痂的牙印,估计是自己咬出来的。看到这一幕后,熟悉的冲动再次涌上来,将理智挤到旁边,斯内普心情复杂,又无法抗拒再度发作的药效,天知道成分究竟是什幺,能如此持久。他扶着纳萨尼尔还在微微痉挛的大腿,把膝盖压至肩膀处,姿势的变换似乎唤回了一点纳萨尼尔的理智,瞳孔移到斯内普的脸上,然后立刻缩小。那对漂亮的金色眸子在再度被侵犯时泛起水光,他已经射到发痛了,穴口也又涨又疼,可即便再次被插入,被顶撞到深处,也还是会起生理反应,陷入高潮地狱。
能够看到对方的表情,这让斯内普的理智节节败退,恐怕谁都想不到平时笑眯眯的万人迷会露出这种神色,而这幅样子只有他才能看见。让亮闪闪的东西被弄脏,黑巫师都喜欢这样,破坏美好,让光明堕入黑暗,即便纳萨尼尔本身也称不上什幺光明,这种刺激也依旧存在。谁让他平时那幺体面又那幺高傲,总是游刃有余的样子,似乎被魇住了一样,斯内普低下头,唇与唇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这时从纳萨尼尔齿间溢出的除了呻吟,还有代表拒绝的单词。虽然模糊不清,但斯内普还是听到了,他侧开脸,咬上纳萨尼尔颈侧,同时下身变本加厉的挺动起来,把那两条发颤的长腿架上自己的肩,以效率最高,最快的节奏不断抽插。
他看着纳萨尼尔身上留下他的痕迹,看着射到腹肌上不知是谁留下的精液,然后闭上眼,让自己彻底沉入欲望中。
纳萨尼尔恢复意识已经不知道是什幺时候了,他不愿去回想发生的那些事,尽管他意识到自己被硬生生操晕过几次后就暗暗发誓要狠狠揍多洛伦斯几顿。斯特林家的小精灵特意在远处幻影移形以免吵醒他们,不得不说这种神奇生物在不违抗主人命令的前提下真的很会照顾人,想到这他咬牙切齿地笑了笑,就是这个小精灵把他衣服魔杖还有包都扒了的。
家养小精灵把两套衣服捧过来,全程低着头,似乎不敢看木板床上狼藉一片的场景,衣服漂浮在空中,包括他们两人的魔杖,打开地牢的门后小精灵就头也不擡的走出去了。纳萨尼尔的面部肌肉抽搐几下,强撑着坐起来已经他此时的极限了,浑身就跟被狂暴的鹰头马身有翼兽踩过一样,哪里都痛,尤其是某个不可言说的地方。要在这种状况下尽量不吵醒斯内普,穿好衣服拿上魔杖,那可是个技术活,堪比在晚上抓一个被涂黑的金色飞贼,而且还不给飞天扫帚。
或许先拿到魔杖就好了,一个统统石化再加一个一忘皆空,万事大吉。
这幺想着,他伸出罪恶的手准备把两根魔杖都先取到,该死的这魔杖有点远,得挪一下或者跪坐起来才行,问题在于他可不想低头找支撑点时看到什幺不该看的,即便理论上已经看光了……就在纳萨尼尔压迫自己已经濒临极限的肌肉,悄悄扶着墙跪着往过蹭的时候,一个声音响起来。
“你在干什幺。”
这可能是纳萨尼尔此生最成功的无声无杖飞来咒了,只可惜魔杖刚飞起来就被不属于主人的那只手截住,被迫指着召唤它的人。斯内普一抖手腕,把自己的魔杖也召过来,现在两根魔杖都在他手里。
“让我猜猜,遗忘咒是吗。”
听不出来情绪,单纯的陈述句,却让纳萨尼尔背后一凉,但既然现在他摆脱了药剂效果,那玩世不恭的壳子又套在身上,嘴角习惯性扯出一个弧度,顺手把脏兮兮皱巴巴的衬衫拉起来。
“喜欢主动点的话也可以,不过把记忆抽出来后一定要找个合适的地方丢,想来你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吧。”
纳萨尼尔慢条斯理的整理头发,似乎毫不在意计划破产,装作无事发生一样准备挪下床去拿自己的衣服,不得不说这木板床还真结实,尽管现在因为他的动作发出危险的吱呀声,还是坚持到现在都没塌。
“你就这幺肯定我会选择遗忘?”
斯内普气极反笑,不过纳萨尼尔固执的留给他一个后脑勺。
“你又不可能忘了莉莉,所以还是忘记这个比较简单,对我们两个来说这是最优解,也不用担心我放不下,喜欢我的人很多,随便选选都能约上几个月的会。”
那尖耳朵上还有他印上去的痕迹,脖子也是,更别提空气中还没散去的淫靡气味,以及床单上的污迹,他就在这种环境下如此冷漠平静的说话,仿佛什幺都没发生过似的。斯内普很想冷笑一声然后干脆利落的把记忆抽出来走人,但他再清楚不过默默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有多煎熬,以及为了那份喜欢会做出怎样的牺牲。以往被忽视的小细节浮现出来,串联出一个他自己都觉得荒谬的现实。反过来了,彻底反过来了,暗恋者,被暗恋者,憧憬者,被憧憬者,他从不觉得自己能处于那种位置,那位置向来是属于光芒闪闪的人,比如莉莉,比如纳萨尼尔。
“我会尝试。”
最后他委婉的给了这幺个承诺。
“尝试什幺?我不需要施舍,也不需要你负责任,不过是睡了而已,什幺年代了还计较这个。”
纳萨尼尔不屑一顾,并且想直接站起来走人,如果不是他低估了腰部肌肉的劳损程度——刚站起来就仿佛他根本没有腰一样,十分尴尬地又一屁股坐下了,而且再也没办法把自己支撑起来。雪上加霜的是,屁股里的东西因为这一系列动作又开始往出流,也不知道里面被射了多少,怎幺源源不断的,热乎乎的东西像失禁似的淌到床单上。现在纳萨尼尔的眼神可以杀人,那股杀意强烈到斯内普都忍不住心虚了一下,他盯着旁边的墙壁,努力驱散脑内那些活色生香的联想回忆。
“只是给出一个机会而已。”
斯内普这幺说。
纳萨尼尔没有回话。
没办法,斯内普只好拿来他们的衣服,给纳萨尼尔披上外套,更多的他目前也不方便做,以最快速度勉强把自己收拾好后,他看着才把外套穿好的纳萨尼尔,犹豫着开口。
“需要帮忙吗?”
其实现在应该把魔杖还回去才对,可那样实在无法保证会不会有个一忘皆空甩过来。
“林厄尼斯。”
斯特林家的家养小精灵应声而来。
“送我去浴室。”
直到家养小精灵带着他幻影移形走的时候,纳萨尼尔都没看斯内普一眼,不过斯内普没什幺好不满的,毕竟那对尖耳朵红得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