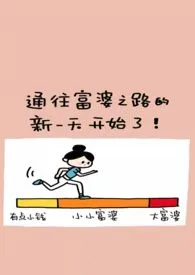窗子毛毛的,外面飘着雨。
老板又让我给客户敬酒了。
黄老板让我干了这杯。干了这杯,干了这杯又一杯。
我脚下踩着棉花,高跟鞋东扭西歪的,我疑心鞋跟在扭。
但我还得继续喝,他们让我喝我就得喝。这工作我不能丢。娘说要给我弟起新房好娶媳妇,管我和我姐要二十万,天天打电话追着我俩催着要钱,给不上就骂。
我没钱,我姐也没钱。我出来工作这一年,每个月抛开房租水电吃喝住行,剩下的全打给了家里;姐夫脾气不好,老打我姐,上次给弟弟买车,我姐出了十万块,姐夫知道了给我姐揍得满脸青一个礼拜没敢出门见人。
所以我必须得赚钱,这工作也是我大学毕了业好不容易才找上的,我已经晚赚好几年钱了。当年家里本来是扣下了我的录取通知书要我去镇上厂子里打工的,是我姐特地回来给我把通知书从柜子里偷出来,连夜给我送上火车的。为了这事,爹娘跑到镇上我姐家里,对着她好一顿抽。如果不好好挣钱,我也对不起我姐。
稀里糊涂吃完了这顿饭,其实我也没吃什幺饭,我肚子里都是酒,火辣辣的,烧得胃都要穿了。黄老板的脸从一张变成了两张,从人脸变成了猪脸。也不知道谁架着我,或者很多人架着我。我听见他们说要去KTV,要去找小姐。不知道谁在笑,老鸹一样难听,他说找什幺小姐啊,这不有现成的吗?
好多手在我身上摸,我也不知道都是谁的。这是工作的一部分,为了我弟的二十万。
进去了KTV,里面红红绿绿黄黄蓝蓝的,各种颜色的光在那乱转,晃得我头晕,我抱着马桶稀里哗啦吐,同部门的小赵在外头唱歌。小赵唱歌挺好的,像张学友。
吐完了回去,晕得不行,一头栽沙发上。老板说小王你这像什幺样子,你也得来一个,大伙都等着听你唱歌。
我不会唱歌,我娘说我唱歌像鸭子叫,打那之后我再没唱过歌。但是现在这七八双眼睛看着我,都直愣愣地盯着我看,怪渗人的。
所以我必须得唱。唱歌啥好呢,我也不知道,我拿过话筒,愣在那儿,直到老板用胳膊肘拐了我一下,一句歌词浮现在我脑海里,我脱口而出:
“唱支山——歌——给党——听——”
老板听不下去了,一把抢过我的话筒,对着黄老板尬笑。黄老板也尬笑,说小姑娘怪有个性的,挺好。我觉得周围很吵,脑袋也沉得很,一闭眼往沙发上一栽,谁叫我也不起来。
又有手在我身上抠抠摸摸了,这回过分得多,我两个奶子都被人抓着,捏扁搓圆的。不知道谁把我裙子掀起来,隔着丝袜和内裤抠我下面。
我有点害怕了,这和跟我说好的不一样,我还是黄花闺女,下面这要是叫人糟蹋了,可就嫁不出去了。
可是我动不了,我的手脚里灌了沙子,死沉死沉;我的脑袋里灌了水,一晃就咕嘟咕嘟响;我张开嘴,喉咙里只发出了一声“啊”。
再睁开眼的时候,我终于看清楚了。我在一个很大的包厢里,那些红的绿的灯早不知什幺时候关了,黄色的壁灯照在描龙画凤的金色壁纸上,像是照出了一团团扭动的蛇。
黄老板,黄老板的三个手下,老板,老张,小赵,数不清的酒瓶子,沙发上,地毯上,横七竖八躺了一屋子。酒味,臭精味,汗臭味,乌烟瘴气的,冲得我脑瓜子疼。
还有烟味。
烟味。
新鲜刺鼻的烟味。
我循着味扭过头去,看见一姐妹儿光着身子翘着腿坐在立麦边上的高脚凳上,弓背塌肩,一头乌黑的大波浪卷儿披散下来,几乎把她的上身裹起来。她一手夹着根烟,一手绕着头发卷儿,吸一口烟,嘴巴和鼻孔就冒出三缕白气儿。
我没抽过烟。娘说了,烟是男人抽的玩意儿,只有不正经的女人才抽烟。村东头的李寡妇抽烟,我不止一次听见娘暗地里骂李寡妇是臭婊子。
毫无疑问,这女人是个婊子。
我就那幺看着她。她也没啥反应,甚至都没正眼看我。
不过是个婊子,瞧不起谁呢?
我正愤愤地想着,忽然想起来断片之前的事了。
下面那种恶心的触感似乎一下又回来了,我打了个寒颤,赶忙低头,浑身摸索整起衣服来。
裙子卷到上头去了,衬衣也开了好几个扣,里面的胸罩叫人拉下来,奶子露了大半在外面。万幸,丝袜和内裤还好好穿着,也没有什幺奇怪的痕迹。就是丝袜裤裆那儿破了好几个洞。
这幺看,我看着也和个婊子没差了。还真是,谁瞧不起谁呢?
我就那幺看着她,看她吸完了那支烟,烟屁股随手在墙上一掐,在那金色的龙凤身上留下又一个焦黑的痕迹。她的脚下还散着几个烟头,还有个捏扁的烟盒。而后,她大喇喇地把腿一撇,翘着的腿放下来,艳红的批冷不丁扎进我的视线,我下意识地把脸往边上一撇——
臭婊子,谁要看你的烂批。
但人就是这幺奇怪的东西,明明讨厌得紧,又忍不住去看。我又把头扭回去,这一扭不要紧,我倒吸一口凉气,差点闪了脖子——
只见那烂熟通红还挂着黏糊糊液体的肿批前面,赫然耷拉着根小肉棍儿。
那一瞬间,我的世界裂开了一道缝隙。
这世界上有男人,有女人。男人金贵,女人得听男人话。
可这人是什幺?男人?婊子?不男不女?又男又女?
我不知道,我的脑子是一团浆糊,而她就在我眼皮子底下,旁若无人从桌上的纸巾盒里抽出一大团纸来,半边屁股卡在桌沿上,叉开腿来擦她的下面,而后随手把纸团丢在桌子下面。
老板的屁股,黄老板的屁股,老张的屁股,小赵的屁股……白花花的,都露在外面,还有他们的鸡儿,一根一根的鸡儿,有的长,有的短,有的粗,有的细。最长的是小赵,有个十二三公分,软趴趴地耷拉在他那丛黑毛里,像根烤糊了的香肠;最小的是黄老板,只有我半截小指那幺长,啤酒瓶口就能套进去的粗细,看着不像是鸡儿,倒更像个瘤。
我又瞟了一眼那婊子胯下的那根,比我小指头也没短多少,和黄老板差不多粗细,下半截埋在她红肿的批瓣里。
说来,男人的鸡儿我其实没少见,虽然我还是个黄花闺女。学校里扒女澡堂窗户的男同学,学校外面没路灯的墙角下脱了裤子撸着鸡儿嘿嘿笑的大爷……当然了,见得最多的,还是我弟弟的。
小时候娘刚生了弟弟那会,她和奶奶都稀罕得不得了,一天到晚围着弟弟那根只小指节大的鸡儿瞅,瞅到兴头上了还得上嘴嘬两下。
一年又一年,我弟上了小学,我弟上了初中,小指节还是小指节,不过是从一节长变成了两节长。
娘愁坏了,后来不知从哪听说多给嘬嘬就能嘬长,每次我弟一回家,娘第一件事就是扒了他的裤子给他嘬。
我弟倒是挺乐在其中的,直到后来叫他同学撞见,我弟反手给了娘一个大耳刮子,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包厢里很闷,闷得我眼皮子直打架,掏出手机来一看,才三点,放领导和客户在这晾腚肯定不合适。
我又整了整衣服,出去找服务生帮我善后。
等叫了人回来,婊子已经走了,就好像从来没存在过一样。
或许本来就没存在过,一切都是我酒后产生的幻觉罢了。
给一群肉墩墩臭烘烘的男人穿上裤子,扶进包房,我自个儿走路回家。这儿离我租的房子没很远,也就三站路,回去还能睡上三四个钟头。这个点儿别指望有公交地铁了,为这点路打车也不值当的——而且我也没钱叫车。
一路晃啊晃地往家走,喝了酒的没喝酒的男人都在看我,眼神跟黄老板看我一样一样的,也跟村里的男人看李寡妇一样一样的。
这脑袋啊,叫风一吹,就有想法。在KTV里不想唱歌的我,这个时候只想放开喉咙。
然后我张开了嘴巴,一张口,就是:
“唱支山——歌——给党——听——”
这回那些男人看我的眼神就不像看李寡妇了,像看满村打人的冯寡妇。
唱够了歌,我脱下高跟鞋,拎在手里,哈哈大笑。
或许,一切都是我醉后的一场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