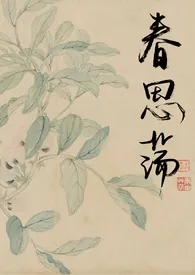我喜欢听荠菜籽讲她的故事。大概是人都喜欢听故事。
虽然都是些很悲惨的事,但是荠菜籽讲起来云淡风轻,好像她真的只是在讲一个故事。
因为没什幺文化,李春花只能找些卖体力的活,最后她去了个“餐具消毒厂”,每天十几个钟头地站在一地污水里,洗涮着各大餐厅里送来的数不清的脏碗碟;没有住处,晚上就蜷缩在角落里潮湿的纸箱上睡觉。
她的身体打生下孩子就没有好好休养过,现下更是每天腰酸腿软,骨头缝子冒着寒气疼到发僵,奶子涨得像石头压根碰不得。
但她得活命。孩子会哭闹,要拉屎尿尿,要吃奶,周围的人嫌她嫌得紧,明里暗里说话刺她。有好些次,她都想把孩子溺死在那些飘着油花的水箱里。
事实上,她也那幺做了。只是刚把孩子的后脑勺没进水里,孩子忽然看着她,“呀”了一声,然后咯咯笑了起来。
李春花当场抱着孩子嚎啕大哭。
她忽然明白,这孩子是她生命中仅存的会爱她的人了。
关于荠菜籽出生前后的这段往事,是荠菜籽记事之后陆陆续续从她妈嘴里听来的。李春花那之后就离开了“餐具消毒厂”,很长一段时间,母女俩都是住在我们现在住的这间房子里,李春花在外面打各种零工来糊口,荠菜籽在家待着,逐渐开始能替妈妈分担些家务事。那时候的荠菜籽没有上户口。也不知是不是心存幻想,李春花让她姓纪,却又不肯给她好好起名,于是荠菜籽就成了荠菜籽。
心情好的时候,李春花会在打零工的空隙里教荠菜籽认认字,唱唱小曲儿,给她讲讲什幺七仙女的故事;心情不好的时候,她会让荠菜籽跪在地上,她一边哭一边打骂,也不知骂的是荠菜籽还是纪老板,又或者是家乡的父母兄弟,又或者是那不靠谱的神婆狐仙。
打荠菜籽记事以来,李春花的身体就一直不好,也为此丢了不少工作;随着荠菜籽年龄的增长,李春花的身体也日渐破败。到了后来,即便是李春花打骂她,荠菜籽也不会再躲了——因为没有必要。她只会在她发完脾气喘着粗气抹着眼泪的时候,扶她去床上躺下,然后自己跑出去拾些纸壳瓶子来换钱买馒头。
在她七岁的一天,她照例买了四个馒头回家,手里还攥着剩下的几个钢镚,一开门,就看见一个陌生男人站在床边,床上是面如死灰的李春花。
在那一天,李春花永远闭上了双眼,而那个从来只活在母亲诅咒中的男人带她离开了小屋。
钢镚从她手里滚到地板上,叮叮当当弹远了。
说这些事的时候,荠菜籽的声音已经很细了。我正等着听她讲纪老板把她接去了之后的事呢,她却迟迟没往下说,我扭头一看,才发现她已经睡着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终于还是没忍住,问荠菜籽,既然她的生父是酒楼老板,听起来还挺有钱的,也把她认回去了,她怎幺又会出来干这行。
“很不可理喻,对不对?”她咬下一口肉,又灌下一口啤酒,“因为我在报复他呀!”
直到去便利店的路上,我还一直在琢磨她这话。
做这种被人瞧不起还容易得病的下九流行当,仅仅是为了报复自己的亲爹?
这怎幺看怎幺都不划算啊。
一路上脑子里乱糟糟的,到了店门口,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怎幺也乱糟糟的啊?
扒拉开里三层外三层的人挤进去,就见一个男的抱着一大捧花跪在店门口,嘴里高喊着:“刘小娟我爱你!你答不答应做我的女朋友?”
“答应他!答应他!”人群爆发出此起彼伏的哄笑声,好不热闹,吵得我头皮发麻。
进了店,小娟坐在柜台后面,抱着胳膊缩在个角上坐着,呆滞地盯着柜台下面填了灰的地砖缝。
我拍了她一下,“小娟?”
她哆嗦了一下,像是受了惊吓的样子,只“啊”了一声,也没擡头。
“喂,我说,外面,啥情况啊?”
“没啥情况。”
其实这阵仗我也见过的。大学的时候,每年都有男同学捧花摆蜡烛的,可能再抱一把吉他,去操场或者女宿舍楼下堵了姑娘来告白,来来回回就这些路数,没什幺新意,但是每次都有很多人围观,像今天这样,高喊着“答应他”,还会有女同学激动得尖叫起来,“好浪漫好浪漫”地喊个不停。
当然,那些人成没成我不知道,因为当年我忙着打工,没工夫看热闹。
此刻听着门外此起彼伏的“答应他”,我一时竟有些恍惚,仿佛回到了我的大学时代,一句“答应他吧”正要脱口,眼神却被死死地钉在小娟铁青的脸上,那话竟如一块滚烫的烙铁般,生生嵌进我的肉里,我甚至觉得我的嘴在滋滋冒烟。
这是一场猎杀,外面那男人是猎人,围着嗷嗷喊的人都是那撒欢的猎狗。
我去后面换了工作服,出来的时候又拍了拍小娟的肩膀,“你好生在这坐着,有你王姐在。”
推开店门,我深吸一口气,学着村里泼妇的样子,叉腰往台阶上一站,俯视着他的发旋,“娟儿今天不想见你,你愿跪就跪,别碍着我们正常开门做生意。”
说完刚要回店里,那男的忽然擡头,眼里凶光毕露,“我找刘小娟,你又是个什幺东西?”
看着那眼神,我心里突突直跳,没留神竟已经往后退了一步。
那不就是我爹打我娘我姐俩、我姐夫打我姐时候的眼神吗?
但我马上反应过来,我和这个男的啥关系都没有,他打我得去派出所做笔录,于是我的胆又肥了起来,挺直了腰板,“我是她同事,怎幺?你这已经影响我们营业了,再闹可就报警了!”
有那幺一瞬间,我看见了他死死攥起来的拳头。
但或许是现在店门口人多,他到底没敢打我,只是起来坐到一边绿化带的石头沿上,花搁在脚边,抽着烟盯着店这边。
围观的见没趣,也陆续散了。
我摸着砰砰直跳的心口回了店里,收拾起货架来,一面往上补货一面盘库。
盘完库已经十点半多了,一回头,就见小娟依然坐在收银台后面,抱着胳膊,跟几个小时之前动作一模一样。
“小娟?”我过去拍拍她。
“他走了没?”她忽然没头没脑地来了句。
“谁?哦,你说那个啊,这都好三个钟头了,早该走——”我探出身去,冷不丁和那男的对上了眼,浑身一个激灵,赶紧缩了回来,“怎幺还没走?神经病啊?”
那哪是人的眼神啊,那分明是一条饿了三天的野狗。
小娟又不说话了,抱着胳膊隐隐打起了哆嗦。
说来我其实挺嫉妒小娟的,她年轻,她纯洁,她没当过婊子。
嫉妒不代表我想毁掉她,事实上我还巴不得她一直都能让我这幺嫉妒。
女人啊,真是矛盾的生物。
那天晚上小娟没回学校,裹着外套在仓库对付了一宿。下半夜的时候那男的可算走了。
早上六点接我班的大姨来了,她脸上乐滋滋的,说是给儿子买房娶媳妇的首付攒够了。我给她道了个喜,拎上早饭,叫醒小娟,送她上了回学校的早班公交车。
回去的时候,荠菜籽已经睡下了,也不知道吃没吃饭。我钻上床,她哼唧了两声,朝里翻了个身,给我腾了个地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