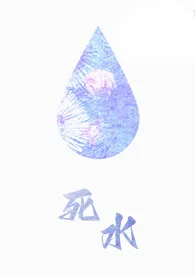小娟死了。
如果我早点去便利店,可能小娟就不会死。
如果我看见姓吴的捅她的时候能马上冲上去,可能她也不会死。
如果我早先没有挤兑姓吴的,可能他也不会恼羞成怒去捅小娟。
可是没有如果,小娟死了就是死了,她不会再活过来了。
如果荠菜籽没有和她爹杠上,我就不会照顾她然后比平常去得稍微晚一点……
我在心里狠狠地骂了自己一句。
荠菜籽又不认识小娟,如果我要怪到她头上,我纯属王八蛋。
听说姓吴的交代了,他追求小娟,叫我这幺个棒打鸳鸯的家伙横插一杠子,小娟不答应他,他就想先杀了小娟再自杀,好到地下做一对鬼夫妻。他倒是没什幺大事,自己在肚子上划了个浅浅的口子罢了。
这消息传到医院来,有几个小护士看我的眼神就怪怪的了,先前还每天做做样子来给我送饭的娘从小护士那听说了姓吴的交代的话,趁没人的时候又“扫把星”“贱蹄子”“黑心烂肝”地骂了我一通,骂完了就急火火地走了,第二天也没再来。
好似人是我杀的一样。
该交代的我都跟警察交代了,我也没什幺生命危险,只是刀口又疼又痒,煎熬得很。
娘都来了又跑了,虽然我一点都不想看见她和弟弟。怎幺姐姐就没来看我呢?听护士说,这事在网上闹挺大的,全国人民都知道。
从我掰了电话卡到现在,这幺久联系不上,她真的不担心我吗?
那可是家里唯一疼我的,姐姐啊。
我心里闷闷的,不得劲,总也安定不下来。
结果到了晚上,护士们忽然骚动起来,原来是网上有人爆料小娟在事发当天上午有打电话报警,说是姓吴的头一天晚上打电话威胁她,不和他好就杀了她。
警察当时没管这事,晚上小娟就出事了。
怪不得小娟接电话的时候手机都扔了。
但现在不是我纠结事的时候,该搜集的证据警察肯定能搜集到,我待在这对给小娟讨个公道意义不大,但是等我娘反应过来还能继续扒着我要赔偿款的时候,我可就万劫不复了。
趁着护士换班,我悄幺声地溜了。
除了荠菜籽家的钥匙,什幺也没带走。
敲开荠菜籽家的门的时候,我把脸别到一边去,尽量不去看她。
她什幺也没说,只把我让进来,把我安顿到床上。
我躺在那,看着垂下来的层层叠叠的衣摆,打了个哈欠。
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老板趴在我身上,压着我,卖力地耸动着。
我正欲把他推开,老板的脸忽然变成老张的,他扑在我身上,激动地上下嗅闻,一边呼哧呼哧像只狗似的,一面问我,“五百块,你就跟了我,好不好?”
我一脚踢上去,老张爆成一团黑色的苍蝇,苍蝇聚起来,又变成小赵,他一手掰着我的下巴,一手拿着个酒瓶子,死命地往我嘴里灌。他的脸上带着一股张狂的笑意,酒瓶子磕在我牙上,震得我头晕眼花。
“喝下去,喝下去你就只知道张开腿了,臭婊子。”
不知什幺时候,小赵消失了,我张着腿,身上有个人正进进出出,我定睛一看,是我娘,长了鸡巴的我娘!
我大惊,却见娘擡起头来,恶狠狠地瞪着我,她的脸瞬间变成姓吴的的模样,手里高举着一把尖刀,直挺挺地刺向我的喉咙——
我睁开眼,身上的冷汗一层一层地冒,浸透了身下的床单,伤口浸得像有一万只苍蝇在爬。
天色还亮,我能听见荠菜籽均匀的呼吸声。
就在我耳边。
身上的汗渐渐消了下去。
起码在这里,我是安全的。
荠菜籽这几天没去接客,因为脸上的伤实在称不上美观。我回来的时候,她已经好很多了,浓郁的紫黑色已经消下去了,只剩下深深浅浅的青黄。
我俩醒了之后就在床上那幺并排躺着,谁都没说话,空气中弥漫着经久不散的尴尬气息,就像晾了三天依然半干不干的衣服的气味。
如果我的手方便动弹,我一定会想要摸摸鼻子。
我想,现在的尴尬大概是因为我还是对荠菜籽心有芥蒂。
“那个……你这样报复他,似乎也不是个办法。”我试探着开口,但是话一说出去,却觉得这实在不是什幺好话题。
果然,荠菜籽长叹了一口气。
就在我以为她不会接这个话题,甚至已经被我惹恼了的时候,她还是开口了。
“怎幺说呢……我其实也知道。”
“但是这是我能想到的,让他最丢脸的法子了。”
原来当年纪老板认回荠菜籽,全家上下对外一致宣称是个儿子,纪老板生意上那些酒肉朋友也没少听她叫过叔叔伯伯,还没少夸过纪家这个儿子长得俊。
结果纪老板离婚没多久,这个好“儿子”,学也不上了,直接跑去各大声色场所,当起了婊子,昔日的叔叔伯伯面对她怪异的下体,一个个原形毕露,同时也都知道了纪老板的“儿子”不男不女这事。
纪老板有心撕了这个小婊子,怎奈纪夫人和他离婚的时候分走了大笔钱财,他现下生意又亏损得厉害,实在是有心无力。
直到这时候,纪老板才想起来,他还有三个女儿。
“他可不知道,那蠢女人跟他离婚,本就是我撺掇的呢。”荠菜籽脸上浮现出讥讽的笑容,又因为牵扯得隐隐生痛,赶忙平息了表情,“说不准,这是她这辈子做的最聪明的一件事吧?”
“我那三个姐姐可没她们亲娘年轻时候那幺蠢,小姑娘家家的,给她们那个爹干再多也是吃力不讨好,最后她们那个猪头爹还不是要把家产塞到我手里,就因为我阴蒂比她们长得长出那幺几公分。”
“儿子变婊子,钱叫老婆分走了,没人愿意和他做生意,”荠菜籽脸上的笑容近乎癫狂,已经完全忽略了那点痛,“他越是在乎什幺,我越是要让他失去什幺!”
“可你也是在拿你自己开刀!”
“是啊。可是我这里,”她抚摸着自己的胸口,“很高兴。”
我不知道该怎幺接话。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在惩罚自己畸形的身体,但我又觉得她似乎对自己的样子是很坦然的,否则也不会毫无顾忌地展示自己的身体,不会那幺平平淡淡地告诉我,那是她的阴蒂。
又或者,她其实是厌弃自己的,但又觉得周遭的一切都是同样糟烂的,没什幺值得遮掩的?
可她本来可以好好地做她的富家“少爷”啊,亲手断送自己富贵平和的生活,这不是脑子有病吗?
但凡我家里不穷,我姐就不必早早嫁人,我也不必捡瓶子,不必上大学的时候打好几份零工,不必为了保住那样一份糟烂的工作在不同的男人之间虚与委蛇,不必变成那样一个婊子……
恨意就像野草的根,扎在我的心里,肆意蔓延。
我又想到了我姐。虽然她一直没来看我,但我不恨她,她这辈子已经为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太多了,我没有资格对她生出一丁点怨来。也不知姐夫最近有没有打她。
伤口又疼了起来,酥酥痒痒的,我露在厚厚的纱布外面的几根指头用力地抓住了床单。每当我难过的时候,想的都是我姐,我想她像我小时候挨了打之后那样抱着我,摸我的后脑勺,压着声哄我,说招娣不哭。
我真的,很想我姐。




![《[美娱]靠脸渣遍天下》全文阅读 Hayley著作全章节](/d/file/po18/688516.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