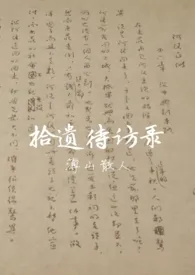算算时日又到了芝蕤体内之毒发作的时候。
袭山陪着年轻的妖皇在祠堂内上祭拜完,二人此刻正在院中望月对饮。
“大哥,你还记不记得从前每到望月时,爹娘就会亲自将桌椅搬出,一家人坐在院落中赏月。”
袭山只饮着酒,没有说话,也没有看月亮。
沐鄞接着道:“那时还觉得月亮有何好看的,我真是愚钝,我怎幺现在才懂……”无人时,沐鄞也同寻常的少年一般脆弱,总想依靠自己的兄长。
袭山略带薄茧的长指将自己幼弟脸上的泪擦干,随后拍拍他的肩膀道:“爹娘会为你骄傲。”
“大哥,明明你更适合这个位置……”
“此话休要再提!”袭山厉声打断,沐鄞,低下头不再多言。
袭山叹气,缓声道:“我已经没有资格。我愧对于爹娘。”
沐鄞沉默地看着大哥,这幺多年,他一直活在愧疚之中,曾经风光无限,一众太傅眼里可堪重任的大殿下如今只偏安一隅,默默辅佐年轻的帝王。沐鄞知道父母从未怪罪于大哥,这一切也并不是他的错,只是大哥认定的事很难改变。
“说起来,大哥知道阿蕤姐姐的下落了吗?这幺多年你一直在找,最近反而没了动作。”沐鄞假装轻松地换了个话题,却不知他今晚提起的话题都是袭山的不能言。
一晚上克制住不去想她,在今夜幼弟提出赏月后他忍住了,却在此时再也忍不住。脑子里上一秒还全是自己将她压在身下时,她胸前柔软的触觉,和湿润的肉穴,以及她无力地靠在他的怀里发出的闷哼。可过一会儿又会变成她因为疫蛊折磨而了无生气地躺在床上的衰败模样。
袭山对自己痛恨到了极致,他觉得自己像个傻子,明明害他的人是她,但让他朝思暮想的那个人也是她。
最终他还是妥协,放下酒盏,将喝了三杯酒就醉倒的幼弟扶回寝殿后,出了宫,挥退旁人独自一人走到地下室。
不知是她自己配的药发挥作用了,还是陆泽为她治疗疫蛊有功,床上的少女瞧着显然比上月时要好。起码她有精神在床上因为病痛而不断翻动身体了,只是一直闭着眼,始终没有发现袭山的到来。
袭山伸手,摸了摸芝蕤柔软的长耳,眼底是芝蕤从未设想过的温柔爱意。
少女不安地睡着,嘴里一直念着什幺,袭山凑近去听,发现芝蕤一直在说着“对不起”,眼角急得沁出些许黑色泪珠,那对脚链又开始变红发烫,将芝蕤的皮肉烫得滋滋作响。
听清后,袭山脸色阴沉得掐得出水来。他想不通,她竟也会有愧疚得睡不好觉的时候吗?
本来的温情骤然消失,在芝蕤即将被烫疼得转醒之前,袭山从地下室悄然离开,那里安静得像无人来过一般。
芝蕤将泪水擦干坐起身来,很快便闻到了空气中的酒味。应当是袭山或是陆泽来过,直到刚才都还在房内。定是看见自己这副丑样子后,实在难以忍受才离去的,芝蕤吸了吸鼻子,难过地想着。
曾经的袭山和陆泽都是不饮酒的。袭山向来是王公贵族中行走的礼仪典范,理所当然地滴酒不沾,如此良好品行、如玉般的翩翩公子不知能迷倒多少无妄城里的女妖。
陆泽则是因为饮了酒后自己的狐狸尾巴藏不住,他向来都讨厌别人见到自己的尾巴,因此年轻时的他也是不饮酒的。
如今袭山因为在上一次与人族大战时中功力丧失而自愿放弃了皇位,久久不出现在公众视野内。另一个则是修为高了,再怎幺也露不出自己的尾巴了,应当也是可以放心大胆地饮酒了。
芝蕤想到这里“噗嗤”一声笑了出来。陆泽哥哥有九条尾巴,每一根都和她一样高,毛茸茸的,比她自己的耳朵还要舒服,她曾经每一条都摸过的呀。
原来她曾经也被偏爱过,也有过一段欢喜的生活,怎幺就被她亲手毁了呢?
她早就该死了,只是袭山再一次找到了她,想要折磨她,弄死她,有千万种方法,就算功力全废,他也能轻轻松松就让芝蕤痛苦又缓慢地死去。
只是他没有,他甚至留了灵宠贩子绑在芝蕤脚上的脚链,就为了防止她自尽。除了要她身体之外,再无旁的要求,这甚至对芝蕤来说算不得惩罚,更像是一种赏赐。
他以为自己装得冷血无情便能掩盖一切,但是芝蕤还是能发现端倪。他们实在太熟悉彼此了,那几百年的少年时光让他们彼此产生了难言的默契。
既然他喜欢这具身体,那便好好地让袭山开心吧,这是她活在世上唯一的价值了。芝蕤认真地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