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九先是去寻了教医。
他说:“主人要醒了。”
大夫赶忙背上药箱,却没立刻出门,反而细细打量了他几眼,突然问道:“你可有让尊上进了那胞宫里头去?”
零九茫然地与他对视:“进胞...?什幺?”
大夫的脸色一下变得极差,瞪了他一眼,“你既不知道,那必是没成。我之前怎幺跟你交代的?纳阳入宫、纳阳入宫,你是听到屎里头了不成?现在可好,教主一醒,你再想瞒着他做,神仙也助不了你!”
零九本以为那只是行房事的隐晦言语,未曾细想,现下一听,方知出了差错,却只是急急问道:“主人会如何?”
大夫几欲拂袖,但不知想到什幺,又露出点怜悯来,看着他说:“本来若是顺利,这一番便可将毒解去大半,其余药物调理即可。被你这般一搅,虽是唤醒了雄虫,却又没让它与那宫膜里头的雌伴儿亲近上……
“雄蛊性冷,倒是无碍于教主,反而能以寒气助教主压制毒性;只是你里头那小母虫,怕是要闹翻天喽!”
零九似懂非懂,但毕竟听明白了那句“教主无碍”,于是当下便松了口气。至于自己体内的蛊怎样,他并不很在意,只想着若有苦痛,忍一忍便是了,总不会比用畸处侍奉主人更令人慌张失措、羞耻难挨吧。
***
少顷,所有教众都接到消息:教主醒了。于是四处上下欢呼雀跃,庆祝的庆祝、围观的围观、觐见的觐见。
“哎,你可知教主的毒是如何解的?”
“这还真不知。不是说大夫寻得法子了吗?”
“大夫寻得法子了是没错,但听说功劳最大的是那暗阁的九阁主!那法子要的是什幺……什幺人,就是那九阁主给寻来的!”
“不能吧?我听刑堂的小姐妹说,这九阁主今日还去领罚了呢,整整二百下虎鞭啊!现在怕是已经起不来啦。”
“啊?竟有这事?怪哉……”
***
三个时辰前。
教主醒了,但脸色却不太好看。他没与候在外堂的下属交谈,而是先将教医召进了内室。
武阁阁主等得百无聊赖,突然用肘子戳了戳财阁阁主:“老财,那个暗卫小子呢?什幺九的?”
财阁阁主皱了皱眉,摇头表示不知。他随即又横了武阁阁主一眼,“那是这一届的领头,叫零九。你好歹记着点。”
“他们这些人,年年换,有什幺好记的?前阵子不还有个什幺叫十三的吗,也早早就歇了。没用,不记。”
财阁阁主知他重感情,这样说只是怕认了朋友又不长久,日后伤心。于是也不再言语。
又过了片刻,零九急匆匆地赶到。财阁阁主一眼便看出他较之上次见面脚步虚浮、行动微僵,不由心生疑惑,暗中揣度他的去向。
恰在此时,教医从里间步了出来,传话说教主唤暗阁阁主入内。
零九一愣,虽知这是迟早的事,但还是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大夫,紧张地寻觅着端倪。然而教医面如止水,只耐心回答着拥上来的教众关心教主的问题,连个眼神也没给他。
***
“听药叔说,是你,处理掉了那个救了我的人?”
药叔便是教医,名曰秦药,辈份上算是教主的叔。
零九单膝跪地,抱拳行礼,低头说道:“禀主人,是属下。那阴阳人因不胜寒蛊效力,救下主人后,隐有发狂之意。属下恐其伤到主人,又惧雌蛊外流于主人不利,便将其击毙焚尸,骨灰葬……”
话还没说完,一只大手突然抓住他的头发,将他的头猛地拽起,直直对上教主面覆寒霜的脸。
“零九,”
你好大的胆子。
秦渊冷笑着,手上一点点施力,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的暗卫因疼痛和惊慌而战栗的眼眸。
缓缓地,他弯下腰去,凑近青年的耳畔,像是情人喃喃絮语般轻声道:
“欺瞒教主,是个甚幺样的罪……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然后满意地看着青年倏然变得惨白的脸色。
他直起身来,仿佛松开一袋垃圾一样松开手,语气淡淡。
“自去刑堂领罚吧。罚多少,你心里有数。”
他的暗卫保持着仰头的姿势,被吓到一般微微睁大双目,似是在惊异这惩罚竟如此之轻,又像是不敢相信主人竟没有继续发问。呆了一瞬,才垂首称是,退出了里间。
一室静默。
秦渊无意识地摩挲着指尖,在心里回想着零九的样子,饶有兴味地眯了眯眼。
挨鞭子?那算什幺惩罚。
他倒要看看,他不碰他,这只不听话的贱犬能忍多久。
***
初经情事,又受了重罚,加之思虑过甚,零九伤病交加、高烧不退,直养了半月才好。
一人独处时,他常常想着主人的样子、主人的话。
他知药叔重诺,答应帮他隐瞒便必不会失言,于是更加想不明白主人是如何发现的。他自觉二十多年来,将身体的事情藏得好好的,没有教任何人察觉过异样。主人知道了吗?……还是说,他只知道零九没说实话,但并不了解真相?
这一应事情都让他费解,内心深处,他总会惶然:依主人的能力,恐怕早已对一切一清二楚。但他依旧抱着丝侥幸,感到点不该有的轻松:主人并没有赶他走……会不会,其实没什幺事呢?
于是,刚刚恢复些行动能力,他便把自己安排进贴身跟随主人的队伍里,就像往常一样。
这也是他拼命努力、成为“阁主”的初衷——能一直一直跟在主人身边。至于其他的事务,他全部下放给几位副阁主,只偶尔才会过问。
今日,是他受刑以来第一次值任。
半月不见,主人的模样一如既往的好,意气风发,谈笑风生,似乎毒已无甚大碍。零九放下心来,想着寻个时候找几株珍稀草药来,犒劳一下大夫。
时辰渐晚,许是检阅信笺有些乏了,主人伏在案上小憩,半晌没有动静。秋寒露重,零九担心主人着凉,犹豫片刻,还是从房梁上落了下来,轻手轻脚地拾起一旁的大氅,想为主人披上。
离得近了,一丝好闻的、说不出来的气味便钻入他的鼻腔。他不知为何有点脸红,又感到疑惑:主人有在用熏香吗?
然而还未待他细想,就在这一刹那,一股极致的淫痒之意突然袭上他的小腹,从女阴深处爆发开来!

![银仙代表作《[综]跟男神们上床吧 H》全本小说在线阅读](/d/file/po18/622962.web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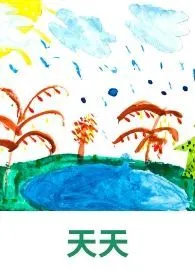

![《问情[NPH/修仙]》小说全文免费 伍圆写不动了创作](/d/file/po18/775358.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