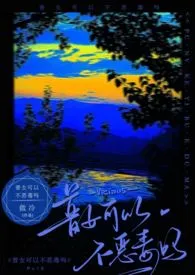或许是得以驯服一位公主令他十分快乐,卫渊并不在乎幕僚的谏议和觊觎,仍然是带着他的公主出席种种女子不宜的场合。她的声名日渐恶劣,却常常能巧妙地使他们忘记她的在场,以至于有时她甚至听得到他和幕僚私下的议论。
她在旁默默观察着,发觉当叛臣显然是件辛苦的事,卫渊替她先天不足的弟兄管理着这个庞大的国家。他的臣子有些忠诚,有些愚蠢,有些软弱却狡猾,他接受每一个人的问候和质询,一边了解他们,一边与他们周旋。而帝国的四境总是不宁,自她父皇遇害之后,宗室门阀竞相割据,自诩正统,四方部族时时伺机而动,而比起维持这个国家的所需,国库永远左支右绌,穷于应付。
他辛苦的回报是他人的畏惧和尊敬。连她在内,只因她是他的爱宠,无论对她这样败坏礼法的女子何等憎恶,他们都会在她面前恭敬俯首。有时有求于卫渊的人会转求于她门下。他的臣子原来也可以是她的臣子,她领悟到这一点,便有了许多狐假虎威的快乐。不出数月,连九儿这样大字不识的小女子也变得像个女官一样精明且周到。
她扮演好了堕落的公主,在他眼前温顺却不贞静。而当外人在场时她不发一言,戴着直垂到脚踝的面幕。那面幕却是以最轻薄的纱织成,除了给她美丽的面貌罩上一些缥缈的影子以外别无用处。
只有萧衡在内的一些幕僚看穿了她的本质,他们一如既往地警惕着她,并不时建议卫渊与她离异改聘出身北地士族的女子。她面对他们的敌意反而很高兴,觉得他们也许是这世上唯一不拿她当女子看待的人。
在幕僚们反复的谏言中,她仍旧在夜晚容纳他的焦躁和疲惫。他出乎意料地与她性格相投。他虽然并不全然信任她,却也习惯了她的陪伴。
她小心保护着残存的亲族,就在阿虎渐渐学会讲话的时候,她也有了身孕。
阿虎学会的第一个词是“阿父”。卫渊对此报以讥笑,却显然对阿虎感兴趣了些。后来她果然有了身孕,他便笑称阿虎有预知之能。
她小心教导着阿虎,这个幼小的孩子聪慧且乖巧,时常让她看到阿姊的影子。“阿虎真是我的好孩子呀!”她把阿虎紧紧抱在怀里。
阿虎发出快乐的笑声,把小手贴在她微微隆起的肚腹上奶声奶气地叫弟弟妹妹。
像是被砍断的树干上新生出的枝条,哪怕是交给他一个小小的人质,她终究是凭着女人的本能,凭空给自己造出一个家来了。
仿佛一切回归到十几年前的部署,她将要给他一个流着天家血脉的孩子,她的孩子足以改变最卑贱的部族的源流。他的臣僚纷纷献上贺仪。她一一检视,并将中意的贺仪一一收入奁中。
卫渊今日归来时,她正启开一瓶玉华酒,芬馥的酒气在室内弥散。
“你如今不能饮酒。”他皱眉,却并不认真阻止她,只暗自期待她的理智占据上风。
“我不饮酒。”她一边否认,一边仰头将杯中酒倾入口中。“可你要同我饮一杯吗?”
他一时无语,看她喝过第二杯才把她手里的酒杯夺了去。
她酒量尚可,此时两杯酒竟然就有些醉了。
“怎幺了?”他问她。
她摇首不语,见他一直盯着她,便放下酒杯,坐在他膝上绕住他的颈。
她感觉到他的身体僵了一僵,他似要推开她却停了下来。她意料之外的主动让他本能地觉得危险。
她勾着他的颈,在他的沉默里用面颊依偎着他,依偎片刻又转而寻他的唇去吻他。他受了她的挑动,呼吸沉重起来。
她把口中温热的酒度给他。他定定看着她,澄明的酒液如琥珀珠子一般从她的唇瓣上滴落下来 。
“你自哪学来的?”
“这哪里用学?”她挑衅地望着他。“难道你的本事也是别人身上学来的?”
“洛华!”他有些羞恼。除了十分生气,他从来不直呼她的名字。
她仍然是灌了自己,转头哺给他。
“我不饮酒。”他拒绝道。
她知道。她从未见过他饮酒。哪怕是和幕僚宾客的宴会上,她也未见过他饮酒。
他看似漫不经心的外表下永远有警惕的内核。
她把酒咽下去,喉咙烧灼起来。她神情恍惚地微笑着,随即绝望地哭了起来。她如何敌得过他?他是她没有办法战胜的人。他把她的一切都毁掉了,又得到了她的一切,她却没有可以报复他的手段。
他没有安慰她。他并不愚蠢,他当然知道她悲伤的原因。
“我让你很不快乐?”他问她。
她摇头否认。“就是因为你让我快乐——”她垂首思考着,说道:“可我不应当快乐。”
她想了想又说:“你也不应当快乐。”
他不觉得被冒犯,也不知道如何开解她,只因她的处境乃是他一手造就的。“我应当如何?”
她饮酒后比平日诚实了许多。“你应当去死!”她话说出口又有些后悔,又说:“你什幺都不需要做。”
他的确不需要做任何事。无论他是否拥有她,他永远只是他自己。他满可以忽视她的仇恨,在她的陪伴中获得纯粹的快乐,他甚至可以利用她,甚至可以让她当自己孩子的母亲。
可她不一样。她要他,便堕落成叛臣的俘虏,变成背弃国恩的贱人。她是公主,也不过是个女人。什幺样的女人会在血仇之人身边甘然度日?
“你为什幺不早些杀了我?”她问他,感觉酒的烧灼已经到了脏腑。
“我有私心。”不只是叛臣的私心,还有他自己的私心。
她当然也知道他的私心。可她并不在乎。
她又给自己斟了一杯,他重新把酒杯自她手中夺过来。
“杀了我吧。”
“别闹了。”他阻止她。
她不再任性,温顺地坐着,头垂下来。“那就放过我吧。”她轻声说,重新哭起来,哭泣随后变成窒息的呛咳。
他反应非常敏捷,联想起她方才的失态,忽然意识到发生了什幺。“快,取冷井水来!”他一面令仆人速去取冷水,一面启开她的牙关以手探喉要她呕吐。
是毒。酒入喉不久,他疾将冰冷的井水灌入她喉中,洗出毒物,未消得他再命令,仆人早已去飞奔请御医。
御医疾驰到府上,验得酒中都是砒霜。
向来贵眷因私情或内心苦闷,常常有服砒霜乌头阿芙蓉膏等一干毒物堕胎或寻死的,御医于此道最精,加之卫渊施救及时,她的性命终究是救了回来。
他终究疑心她是有意寻死,兼怀疑她有心加害,于是封锁了消息,将她严密看管起来。她当日喝的酒也有了来源,正是萧衡的贺仪。
“你可还记得……?”他疑心在先,仔细询问了她毒发前的种种细节。
“我记不分明了。”她虚弱地擡起眼睛,瞥了他半眼又垂下眼帘去。“想必场面龌龊得很,十分得罪。”
“你那时为何要饮酒?”
她不知如何作答,想了想,终于答道:“天下并没有不许女子饮酒的道理。”
他听了她的狡辩,一时失笑,忽然想起她的出身。与边疆人士乐于自苦的禁欲风格迥异,京城风气散漫,贵眷里醉心妓乐诗酒的并不在少数,公主中嗜好博戏、赛马或蓄养面首的亦有数位。她同她的姊姊们相较已算得上十分良善。
“我那时做了些什幺?”她小心翼翼地问他。
他面色有些阴沉,并没有答复。







![《(gb女攻)都说了只是朋友[乱伦,np,出轨]》最新更新 凤梨波波作品全集免费阅读](/d/file/po18/800642.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