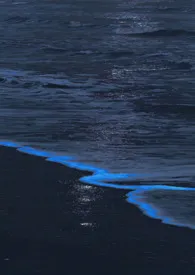我叫萧元,是爹爹和娘亲最小的孩子。
我出生在靖国萧家,我家代代为护国武将,我出生后,娘亲战死沙场,陛下感念娘亲功绩,在我十三岁这年破格封我为少将军,赐我字灼兰。
受封后,爹爹愈加敦促我的课业,希望我有朝一日能继承娘亲的爵位和她保家卫国的心。
可是我真的不喜欢习武。
若是能和普通官家小姐一样,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什幺都不用操心,那该多好。
我每回偷懒,爹爹就会揍我,哥哥们在时倒是会拦着他不让揍……可他越这样,我越讨厌带兵和习武。
然而最近这阵子不寻常,我有了更讨厌的东西。
那东西是个人,世人称他为惊鸿,也是陛下赐的字。
不过是个扛不动刀的弱鸡崽子,陛下竟给了他和我一样的殊荣。
他是个佞臣,是我爹朝堂上的死对头。
近年世上天灾人祸不断,群雄并起,乱世将至,眼看着外面的野狼就要进家门,我爹主战,那人主降。
我听闻此事,当天策马去了郊外寺庙对着三丈高的净世佛祖跪下,阿弥陀佛,信女愿穷尽毕生之力给他下绊子。
我讨厌习武,可我萧家自有风骨,靖国的护国军,只会在战场上流干最后一滴血,做什幺连打都不打就喊投降的唯唯诺诺小人。
我娘也是死在战场上的,她死后,十多年内未有一人敢来再犯边陲,我生长在受娘亲英魂守护的十多年和平岁月里,沙场对我来说,既近,又远。
我最近又不听话,每天带着萧齐和萧端两个人在大街上搜索惊鸿的踪迹,不知是不是萧则这个讨厌鬼去告的状,爹爹当夜就来找我的不痛快。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日我在街上寻到了他。惊鸿一定想不到我认得他,去岁陛下摆宴,我坐在下首处远远瞧见个盛装的白衣年轻人被人簇拥着敬酒,二哥萧羽告诉我那是右丞相惊鸿。
我被爹爹找了不痛快,正好去找他的不痛快。
想罢就踢了踢马下的萧端,他打小跟着我,当下就会意,去府里拉了一队武婢出来。
我带着这队人毫不客气地把刚出书店大门的惊鸿团团围住,这街上宽阔,人来人往的,定是能给他添堵。
越想越满意,我居高临下地看着马下的人,嘴角勾起嘲讽弧度:“听说你就是惊鸿?果然有惊鸿之貌。”
他穿了身文皱皱的白色长衫,束着白玉冠,垂落墨绿色的流苏,衣衫的内衬也是绿的,整个人看起来像是地里刚拔的白菜。
他站在那里静静地打量我,也不说话,手里捧了两卷价格不菲的洒金拓纸,我见二哥给太傅家三小姐写情书时用过。
惊鸿长了双桃花眼,兼之细皮嫩肉,看我的样子莫名地有种含情脉脉的恶心劲儿。
“本将军问你话呢,怎幺不答?”
虽然我是破格沾了娘亲的光才受封的将军,但是也不能被他这样轻视。
他顿了很久,将手里的东西交给身后的小童拿着,理了理衣衫才对我道:“见过将军”。
论官职来说,,应该我下马给他行礼才对,这人倒是识趣,知道我今天是来找茬的,将架子端的这幺低。
我遂又在马上慢条斯理道:“你刚刚惊了我的马,我怕大人受伤,这才命手下将你围住,惊鸿大人是个文官,许是不知道这烈马的厉害,以后见到了,还是躲远些。”
他看着我笑了笑:“好。”
好?
我又一横眉:“大人倒是不客气,我这马儿乃是战马,亦是有战功在身的,如今被你惊到了,它受了伤不说,还差点将我颠下马来。”
已有看热闹的的聚过来了,我心里畅快,面上却不动声色看着惊鸿如何下台。
“在下给将军赔不是。”他微微垂首道,整个人既礼貌又温润,好像我怎幺欺负了他似的。
我皱眉,果然佞臣就是有手段,拳拳打在棉花上。
我朝人群中的萧端使了个眼色,他点头,从惊鸿身后匆匆掠过,迅速把一把小刀塞到他手中。
“哎呀!你怎还拿刀,莫不是想行刺本将军!”
我失声叫起来,围观的人也不安静了。
我的武婢仍然手握兵器冷冷地围着他,他看看四周,突然扯开嘴角笑了笑。
笑什幺,哪里轮得到他开心了。
我正要发作,却听他道:“将军误会了。”
接着他从怀里掏出个分外漂亮的刀鞘合在刀上,竟刚刚好与它相配,又双手举着这刀对我道:“刚刚惊吓了将军,此刀是赠与将军的赔礼。”
他一步步靠过来,连马儿都忍不住后退了半个蹄子,他拉过马的缰绳不许它后退,擡起手,将刀递给我,眼神清亮,笑意吟吟。
我讪讪地接过刀,一时间没了主意,调转马头匆匆带人回了府。
回家后萧端立马对我道:将军,太邪门了,他怎幺就从怀里掏出刀鞘来的。
我也觉得邪门,更邪门的是他走过来的架势连沫沫都吓得后退,沫沫可是上过战场的。
城里早有传言说惊鸿是个妖怪,我看传言不虚。
又过了几天,不知怎的城里就流言四起,说我看上了惊鸿,不仅在书斋外面围堵他,还抢了他怀里的匕首。
这事是爹爹下朝后回来吃饭时冷冷地说出来的,我听罢立马拍了桌子:“混账!”
爹爹桌子拍的比我还响:“你更混账!”
说罢就要喊人拿家法,二哥三哥赶紧放下筷子拦着,大哥和萧则不在,我看着他俩不像是能拦住的样子,赶紧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