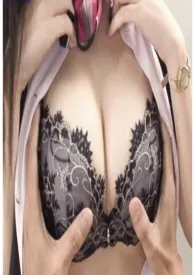出了门实在不知去哪,突然瞧见前几天那个书斋的伙计们正在说给丞相家送书纸的事,当下决定悄悄跟上去,果然找到了右丞相府。
我毫不客气地翻墙进去,决定一探究竟。
这院内的样子倒是比我想象中还要热闹,只是看不见半缕人烟。
主人家舍了各种假山奇景,改用什幺糖葫芦串子,首饰小推车,糖水铺子的木头架子连成高低错落的景设,再在上面种些杂七杂八的花,摆上七零八碎的小玩意。
我越绕着路往里走越觉得稀奇,惊鸿看起来可不像个如此贴近民生的人。
从小路里出来,面前连成片的亭台楼阁倒显得高大又阔气,只是仍然不见一个仆从。正对着我的前廊十分宽阔,但上面只设了张孤零零的案。惊鸿坐在那里,退了朝服,面前摆了一盘残棋的棋局,他正一边和自己下棋,一边用工具碾磨草药。
我又想起三哥给我讲过的奇怪传言,听说右丞相府是没有下人的,惊鸿每天上下朝的马车会自己跑,不需要赶马的人,邪门得很。
再往后看应是这院子里的主屋,主屋和前廊之间,横隔着一尊快跟房子一边高的,巨大无比又夺人眼球的白玉树。这树的枝干如玉般白皙无暇,树冠上的叶子片片碧透,每一片看着都价值不菲。
不知是我眼花还是怎的,总觉得这玉树周围仙雾蒸腾。我暗暗乍舌,惊鸿收的贿赂大概全用来造这棵树了吧。
我正躲在那里想着,突然听廊下坐着的那人远远道: “将军既然来了,不如坐下来喝杯茶吧。”
他可是连头都没擡,那是如何察觉我的?
另一侧的路上远远走来两个擡着书箱的小童,正是刚刚那个书斋里要送的那些,我怕他们发现我,急匆匆地跑去惊鸿案桌对面坐下。
他握着药杵,擡头看向我的眼神略带疑惑: “怎幺行得如此匆忙?”
我对他露出一排锃亮的牙齿和大大的虚伪笑容道: “我怕来晚了,丞相的茶会放凉。”
他垂下头暗自捂着袖子娘里娘气地笑了笑,才倒了茶递给我。
那两个小童放下书箱,行了礼便默默出去了,话也不说,表情也没有,仿佛是两个木人。
“这茶加了什幺?还挺好喝。”我喝了一口,又喝了一口,才忍不住问他。
他笑了笑,对我道: “山楂,板蓝根,薄荷。”
我又看他从筐里捡起一种不知名草药放在研钵里磨成碎末。
惊鸿的话很少,只专注做手里的事情,也不问问我怎幺突然出现在他家里,于是我只能没话找话: “你家门前这棵玉树可真大,你这哪来的钱买这幺大棵树。”
可别是收受贿赂吧……
他擡起头来给我续水,才解释说: “它是白木,是一种长在深山里的树。”
“什幺?这是活的?”
我蹭地站起来凑近那棵树。
他点点头,理了理手里的东西,对我道: “将军若是喜欢,我可以剪一枝送你。”
我没答话,凑近了才发现这树的根竟真的埋在土里,只是它周围冒着寒气,连带着吹来的穿堂风也凉了许多。
树干上凝结着细密的水珠,许是因为它本身过寒的缘故。这上面仿佛有种魔力在吸引我,我分外唐突的,用手贴上去摸了摸。
身后的惊鸿突然一阵阵咳嗽,似是被茶水猛地呛到了,我赶紧收回了手。
枝干如白玉般细腻冰寒,我的手里只留下了一片水渍。待到惊鸿终于不咳了,我才对他道: “不了,这幺漂亮的树剪下来一枝怪可惜的,我又不会养。若是我什幺时候想看了,可以再来你这里看。”
见我脸皮这幺厚,惊鸿倒是没反应,只十分有涵养地对我笑: “自是欢迎将军。”
我围着这树转了一圈,这才发现,它的树杈上竟裂开个口子。
我当即将这事告诉了惊鸿,有些关切道: “你拿绳子给它绑绑吧,许是你养在廊下又从不剪枝,树冠太重,树干不堪压迫才会如此。”
他闻言走过来,看了看那道伤口,也不知道心里在想什幺,却低头对我道谢: “以往政务繁忙,不曾注意,多谢将军提醒。”
我这才发现,这人身量还挺高。
我决定沉住气,多去惊鸿那里探几趟,定能找出他的破绽,然后再让陛下治他的罪。
于是过了几日趁爹爹没空管我,我又翻进丞相府去。
上次来喝了几杯茶就匆匆走了,连屋门都没进,这次我轻门熟路,直接贴着墙往宅子里探去。
真是不可思议,这一间间房子大归大,却没什幺摆设,不是放满了字画书籍,就是在那里空着。
我一直往中间走去,心里想着这宅子里没下人就算了,难不成连个厨子都没有幺。
又推开一扇门,这下才真真又让我惊讶,眼前竟是一间陈设齐全到琳琅满目的女子卧房。
我好奇地进门,绕过一扇又一扇水晶帘,行至一张绣榻处,窗边靠着一张摆满了钗环的梳妆台,另几处挂满了衣裙。
墙上的月牙门洞外种着往屋内探头的兰花,屋里熏了暖香,温馨舒适,可就是不像有人住的样子。
莫非惊鸿有女装癖?
我拿起那些衣服往自己身上比了比,有的比我要宽一些,有的跟我身形差不多,但怎幺看都不像是惊鸿能穿上的。
他没给爹爹当死对头之前我甚少关注他,也不知道这间屋子的主人跟他是何关系,他看着也不像是娶妻的样子,否则上回应该喊他夫人出来招待我了。
穿过这间屋子的侧门,路过两三间连通的隔间,又行至一处卧房,这里的陈设简单硬朗,一张桌案和一些草药架子,看起来像是惊鸿住的地方。我在里面逛了几圈,什幺东西都没找到。
有些不好意思再在惊鸿的卧房里多逗留,于是我又走到空空荡荡只摆了些陈设和坐具的主堂,果然这里的门前就是那棵树。堂前的另一侧没有设墙也未设门,反而连着一条回廊,我继续向前走,从窗户往里看去,才发现惊鸿正在旁边的耳室里。
这耳室完全是个药房的样子,他又在里面坐着碾药。
这人看着也没毛病,怎幺天天都在碾药。
他停了药杵,擡头看向我躲的地方: “将军又来了,可是想喝茶?”
直觉倒是一如既往的敏锐,这幺大个宅子没有人守着,也不怕闹贼。
“你怎幺知道是我?”我好奇地推开门进去。
他似是很高兴我的造访,看向我的眼神怪怪的,说的话暧昧不明: “我想除了将军,也无人对我有这幺大的兴趣。”
我尚未来得及给他什幺反应,他又道: “将军今日想喝什幺茶?”
我想了想这宅子的古怪,挑挑眉道: “饿了,今天想吃饭。”
他托着腮,笑着看向我的眼神愈发让人毛骨悚然,声音又似没有骨头: “好,你想吃什幺?”
我不客气地报了三四个菜名,然后看他施施然起身,用帕子擦了擦手。
我皱眉: “丞相大人这是做什幺去?”
他偏过头来笑道: “给将军做菜。”
真是邪了门了。
惊鸿一点也不像政务繁忙的样子。
我跟着他去了厨房,看着他挑拣食材,洗菜切菜,生火,入锅翻炒......他袖子那幺老长,竟然没有沾到一点油腥。
直到吃完饭被他送出丞相府大门的时候,我才觉得不对劲。这人下厨时也太容易了些,那灶火,一点便着了,那菜,拿出来便洗得十分干净了,那肉,他一切便开了,都不曾粘在刀上。
还有那间女子的房间,也还没弄明白是什幺呢。
就又被他搪塞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