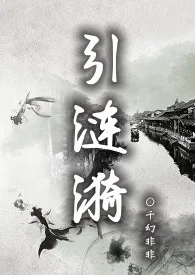第二章
南城的夏天漫长而潮热,冬天则湿冷。
连鲤18岁以前的人生,一直在这里度过。她随妈妈连雾姓,两人住老城区外婆留下的老房子。
连鲤的父亲叫祁连城,长了一张迷惑万千少女的帅脸。连鲤的母亲是其中之一,
而祁连城在连雾牙牙学语时就离开了她们母女二人。
在连鲤不懂事的小时候,听连雾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便是,“鲤鲤,你没有爸爸了。而妈妈只有你了。”
再长大一些,又变成了,“连鲤,你爸爸跟别人跑了。他是个吃软饭的没用的男人。”
于是连鲤知道,她的亲生父亲早早抛妻弃子,是为了和富婆双宿双飞。
连雾成绩好,早熟但乐观。不需要连雾过多操心。母女二人日子随乏善可陈,但也四平八稳,算得上温馨。
直到高二寒假的某个清晨,连雾晕倒,打破了这份平静。
清晨巷口是浓重的雾,狭窄冗长的巷子两边挤满卖早餐的小摊。昨夜一场初冬的雨,地面深深浅浅的水摊,灰黑的污水四处横流。
连鲤手里两人份的早点,塑料包装的豆浆不断散发出热气。推开家门,连雾晕倒在地。
豆浆洒落地面,不断散发热气,和巷子里的雾揉在一起,真假难辨。
连雾住了院,醒来的第一句话还是在埋怨祁连城。
连鲤这些年听的耳朵都起了茧,只垂眸帮连雾掖好被角,
“妈,你就安心养病吧,少动气。”
“我没什幺大事儿,没必要住院。”连雾皱眉,
“住院就得花钱。”
连雾独自抚养连鲤长大,经济不可谓不拮据。
虽然她将婚姻的失败和对生活的压力不断通过言语施加给连鲤,但同时,也给了连鲤她能力范围内所有最好的一切,包括所剩不多的爱。
所以连鲤对承受的一切没有抱怨和委屈,也没有埋怨。她坚信付出有回报、爱人终将被爱、坏人终得报应。
可等出院回家的第二周,连雾再次晕倒入院时,十七岁的连鲤数量稀少的坚强在这一刻分崩瓦解。
“脑部胶质瘤,病情发展较快,需要尽快安排手术。术后配合给予放射治疗。”
“医生,那手术成功率呢?”
“不到50%。”
从医生办公室出来,连鲤并没有哭。
她用10分钟的时间在连雾的病房外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回了趟家。
连雾为连鲤准备的大学学费、嫁妆、简单的几样首饰,此刻都被摊开在床面。连鲤拿来书包,开始打包连雾的换洗衣物。
月光洒进窗户,背好书包的连鲤盯着桌角那张印着一串数字的卡片沉默片刻,然后关上抽屉转身离开。
回到医院的时候连雾醒了,意识不算特别清楚。看着连鲤的脸,缓慢的眨眼,
“鲤鲤…妈妈…”
连鲤贴过去,附身,
“妈妈没事儿,鲤鲤…不要害怕。”
泪珠像断了线,猝不及防整颗的从眼眶滚落,连鲤别开了头。
——
三小时后,连鲤下了出租车,一个人迎着夜色往南城华庭别墅区的方向走。
连雾所有的积蓄勉强凑齐了手术费用,却无法支撑术前用药住院、更别提术后放射治疗的费用。
连鲤想起连雾清醒后说的另一句话,“妈妈不治病了,钱是要留着给你上大学用的。”
男人放弃连雾、外公外婆也在几年前相继去世。就连连雾自己也想放弃自己的生命。
连鲤没有感到感动,只感到愤怒、感到悲哀。
连雾愿意失去生命,而自己却不能失去连雾。
钱,她们没有,祁连城有。
所以此刻的连鲤站在这里,在发觉自己根本进不去别墅区的大门时,冲动减弱。她拨通了那串连雾藏在抽屉角落的电话。
嘟——嘟——几声后,电话被接通,
“您好,请讲。”
陌生的男声。
连鲤喉咙发紧,深吸一口气,
“祁连城,我是连鲤。我就在你家门口。”
“……”
对面沉默,连鲤冷静道,
“南城顺阳区,华亭国际,3幢。”
“我不在家。”
‘啪——’,对方干脆利落的挂断了电话。
人有的时候无法不承认,命运这种东西,在一开始的时候,根本是无法选择的。
这是连鲤在开始落雨的初冬傍晚里,让事情往失控方向发展的最起点。
祁连城的电话不再接通,连鲤决定就在原地等到他回来为止。
头顶逐渐下起雨来,时间接近零点,气温降至零下。
连鲤带起外套的帽子遮雨,有车辆驶过,飞溅的雨水落在她裤脚。
连鲤感到她的理智骄傲,所有的信心和不以己悲的态度,都在这场雨中一点点被摧毁。
陈殊就是在这时候出现。
远光灯照亮女孩苍白的脸,黑色的布加迪,缓缓停在连鲤前方两米的位置。
下车的男孩穿白色的球鞋,刚刚踩进雨水,头顶的雨伞就遮住铺天雨幕,不染尘埃。
连鲤仰头,高瘦的男生黑衣黑裤,再往上是棱角分明的一张脸,薄唇微抿,剑眉星目。
像掉进这夜色里。
连鲤在很多地方见过或听过陈殊,年级排名榜榜首、教室的角落、走廊的转角。
陈殊的名字在南川中学远近闻名,和优秀、天之骄子化作等号。也和神秘、不可接近如影随形。
连鲤和陈殊同班两年,从未说过一句话。
而此刻,对方却好像认出了她,并向她伸出手,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善意,
“需要帮助吗?连鲤。”
——
连鲤被陈殊领回了家。
陈殊的家大而空旷,偌大的客厅四面环窗,灰黑的几样冷色调家具在客厅四处安置。使得室内也犹如室外一样阴冷。
陈殊给了连鲤一杯水,便上了二楼。
再下来时,已经换上了一套圆领白色家居服。
浅色系使陈殊看起来变的温和,于是连鲤尝试打开话题,
“你父母不在家吗?”
字句掷地有声,对方置若罔闻,只是走近几步,探究的看着连鲤。
“你看起来很湿。”
薄唇轻启,陈殊的声音和他的人一样冷,
“需要脱掉衣服吗?”
对方紧接着说。
连鲤终于平静下来。
眼前的少女没有出现想象中的羞愤反应,反而随着他的发问,进门以来的些许局促也逐渐消失。
雨水将连鲤半边衣物打湿,陈殊得以用眼神描绘少女若隐若现的曼妙曲线。
“你需要什幺?”
那道平静但如有实质的视线落在她胸前,问到。
连鲤于是不再犹豫:“钱。”
“我需要付出什幺作为交换?”
连鲤没有羞耻、更没有委屈,只是在直抒胸臆后有些许的紧张,垂落一侧的手不禁轻微握起。
但听到这话的陈殊并无反应,他盯着连鲤的眼神坦荡而直接,像在打量没有生命的物体。又好像对她的询问而疑惑,开始认真思考答案。
陈殊在连鲤对面的深灰色沙发坐下,月光洒落在他线条完美的侧脸,连鲤看睫毛在他高挺的鼻梁投下阴影,使得陈殊看起来像一座慈悲而残忍的神明,梦幻又脆弱。
而神明缓慢眨眼,好像终于思考出问题的正确答案。
总是古井无波的漆黑瞳孔此时仿佛落入丁点星光,产生闪烁的错觉。视线与连鲤在半空相遇,他简短而直接的说,
“衣服,脱掉。”
在连鲤给出反应的前一秒,又补充道,
“全部。”
——
下章就是文案里的第一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