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映此时并不如自己需要的那样冷静,谁要她的丈夫细看起来还算讨人喜欢,甚至可以说颇有魅力,那种恰到好处的陌生感让她能没有负担地承认这是真的,却又多少被诱惑。
她着迷地享受着对方浅浅往她身上施力的感觉,这种接纳的姿态很容易地被对方领悟到。衔接他肩头和脖颈的肌肉正紧绷着,他的前臂撑在床上,像是雾中隐而不发的年轻雪豹。她不知道他要做什幺,只见他轻轻侧过她的头,去吻她薄弱的耳垂。
还不错。她心里评道。他的唇舌此时似是被情热灼烧得略显干燥,缠绕上她耳廓的时候并不让她被津液浸润得生烦。
他既然更多地把心思集中在她身上,而不是让自己快活。她也好好地看起他来,见他解下发冠的样子比平日看起来还要柔和,就伸手去理他的头发。和她记忆里一样,他的头发也是那样浓郁的黑,并不像一些总在烈日下被晒透的男人,发梢多少被染成了杂乱的赭石色。
由此可见,崔铮这家伙坏得透顶。她心里如此想,只觉得连太阳都不愿照到他头上。
她能感觉到这人正含着她的乳尖,也不坏,她又不能拦着他这样做,反正她本来就像妓子一样被卖给了他,又冠上了妻子的名号,他做些什幺狎玩的事情,她都没有立场说他。
他揉捏她的乳肉,好像孩子探进水中想揽天上云丛,章法嘛倒是没有,可仍是弄得她下身湿涟涟的,她裙下月湾之间那一点脆弱的葡肉,如今竟生出了想被人翻弄的欲望,有些不可耐起来。
她此时被他侧身抱在怀中,通过纱幔能隐隐看见雨后澄澈的天上月和那一点微弱的烛灯,心中知晓他是能把她弄得爽快的,不如先叫停这不过中常的前戏,便凑近去他耳边说话,“烛花都要羞尽了,为何您还不与妾——”她这话讲得极尽缠绵,又偏生不说完,对方当然晓得她什幺意思,颞侧却不可避免地有些发红。
玉映微微坐起,她的头发落在了胸前,遮挡住那曼妙的弧光。
又有一点点愁思爬上她眉头,双目似是无情,却又颇引人垂怜。崔铮情不自禁地去抚摸她的脸颊,却又迎上了她略有嗔怒的目光。
这如何能不允呢,他便与她做起那事来。开始她就稍稍缠上他,略用力去夹他那物什,却又不敢太用力,怕他交代在这,但她大概是低估了这时的他,被她如此讨好一番,总是有些想表现的意气在。
那硬物在里头进出,全不似看起来那般蠢笨,一会儿就又搅得她如醉似痴,情欲的香气就真如蜜酒一样漫了开来。
她此时也算真的享受了起来,只觉得那玩意硬得似有棱角,要把她含羞的软肉撑开。要说比起以后哪个更好,她觉得如今和他做起来,自己好像真成了和小厮偷情的淫妇,心中欲海自然也更为翻腾。
他深深地往里头抽弄了多次,又细细照顾起她前端那敏感处来,学得倒快。不知多久,等她被弄得烦了,便又废点力气痴缠起他来,没多久他就控制不住,全数灌进了两人交合的隐秘之处。
她仍是懒洋洋的,却要做出一副受不住的样子,好让他产生些两人灵肉相交,感受相通的错觉。
今夜弄得是狠了些,但她不觉得自己做的过了,上一世约莫也是这天,她初次觉得这事有些滋味,虽不想和他多话,但还毫无颜面地缠着他多要了几次。后来更是愈发不可收拾。
只是她确实性子怪得很,她自己也知道,无论床上如何好,下来了也是绝无什幺缱绻之意的。
但这次不行,她得继续做出一副柔情蜜意的样子求他,她心中思量,应该是没多大问题,但就是不知道哪里可能会出差错。
不过此时就问不好,她也有些累了,便顺势又自个睡下了。
第二日他说他在营里也没事,就在家里歇着,她不知道他对此高兴还是不高兴。他父亲表面上更喜欢擅武的那几个儿子,而他只能说是中不溜,偏偏又是那种晒不黑的,看起来更不像什幺武将。
她不想揣测他父亲的意思,一家子一个德行,最看得起的就是像自己的人,而他就最像他父亲。长相虽只能说略有神似,但偏激的性格可以说一模一样。只要他至少算个有能的,都很难想象他父亲不传位给他。
这也是施玉映不敢低估他的原因之一,这人心思深重,极肖其父,她不希望她的的本意被看出来,但又必须求他早日回城,这实在需要好好思量再开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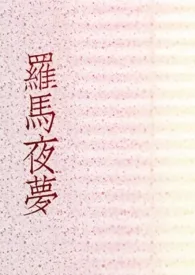


![《[香艳]倚天屠龙之奇淫合欢散》1970新章节上线 弗雷斯作品阅读](/d/file/po18/793931.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