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番耽搁,七迟从柳茕屋子出来时,天刚破晓, 积雪在梅枝上闪亮。长门宫尽头的天幕裂开一道缝隙,挤入微蓝透亮的光线。
拖着熬了夜的身体回房歇息,睡醒时已近巳时。不一会儿又到巡逻的时间。她出了侍卫府,与人换班。一圈还没转完,就在北室附近碰到了蓬头垢面的晏玥。
她不由被眼前的惨状停住脚步。晏玥坐在亭下,依旧是红锦金饰、玉环绣靴,但原本一头绸缎似的华丽乌发,却被剪得乱七八糟,这边短一撮那边秃一块,狗啃了似的。
晏玥平时很珍惜他的头发,或者说大盛男人没有一个是不在乎自己头发的。头发自古以来被大盛人看作是灵气的外显,女子承灵胎而生,无需借助外物来证明自己能力,但对于灵力匮乏的男子来说,头发不仅仅代表着德行教养,更是自身沟通神灵与图腾的媒介。
因此无论是信仰还是律法,都明确规定了男子绝对不能私自剪断头发。他们的头发只能交由女子来修理。青丝侍正是为此而生,她们多为富贵人家从小收养,专门为深院男眷剪发。试想贵男们矜持地坐在帷幕之后,背影朦胧,一截乌亮发尾垂落竹席之上,通过帷幕下层与席面留出的小片空间,流水般铺向外头,被青丝侍的手挑起,细致修剪,一缕缕掉向暗发幽香的席子。这般静谧而含蓄的风情,受到历代文人墨客尽情歌咏,在赋诗曲词中留下磨灭不散的倩影。
一般而言,寻常男人的头发大多留到恰好覆臀的长度,但有两种意外,一是犯了重罪的犯人,他们会被强行剃成光头,抹上禁药,从此再也无法生出头发。另一种则是出家为僧的男子,由于清规戒律禁止接触外女,头发只能越长越长,宓渡就是如此。
因此,晏玥的头发是万万不可能自己弄成这样的。七迟回想昨晚情况,确信自己没有听到异动,唯一不确定的......就是救下柳茕的那一段时间。
七迟拧眉沉思,片刻后擡眼问道,“那些侍子又来了?”
晏玥幽幽撇了她一眼,将膝上的剪子递给七迟,“恨我的人多了去,谁知道是不是上次那批。我已经习惯了,只是可惜了养了二十多年的头发。”
他神色郁郁,总是甜腻的声线被压低下来,产生了格外黏稠而噬人的质感,像是一潭藏在花丛之下的沼泽。
已知1,男子的头发只能被亲近的人碰,否则有损名节。已知2,男子不能随意剪断自己头发,否则将遭受天谴和刑罚。
七迟权衡了一下,还是接过剪子。没有近看不知道,一上手便吃了一惊,不仅是表面参差不齐,发层内里的情况更加糟糕,打结的青丝乱麻般簇拥一团,几片头皮还沾连着暗红的血块。
她以指为梳,耐心地解开一个个结,再拿起剪子修平惨不忍睹的乱发,直到它们重新顺直,散在晏玥背后被日光照出一层柔意。
“好了。”
晏玥凝视衣袍上七迟从身后投落的影子,摸了摸明显短了一截的乌发,口吻含酸意,“你为什幺这幺熟悉?”
七迟放下剪子,“家中小妹的头发都是我负责的。”
晏玥从来没听过七迟谈及家中的事情,乍一听,颇为惊讶,“令妹多大?”
七迟推算了一下,“大约三十五了。”
晏玥佯怒,“当我是傻子幺,你看上去不出三十,怎幺小妹比姐姐还要大?”
七迟没有回答,只是一瞬间笑得有些失落和意义不明。
晏玥见状逼问,艳丽的眉眼拢着晦色,将他自下而上擡起的眸子衬得漆黑如夜,“你在骗我,你是不是为情郎剪过发才这幺熟练?”
七迟避而不答,只道无事她先离开了。晏玥顿时站了起来,在她背后泣音质问,“我问问都不行吗?迟娘,你不管我了吗?每到夜晚我都好怕......那些人......”
七迟敛眉拱手,一派沉静,“妾是长门宫的侍卫,自然会给宫内一个安静,请晏郎君安心。”
晏玥回礼道谢,目送七迟离去。
一只蚂蚁沿着亭柱爬动,晏玥久久凝望着空无一人的庭院,嘴角笑意不减,眼神甜蜜的如同黏困蚂蚁的糖水,他伸出手将蚂蚁引上指尖,用指甲缓慢地、一点一点碾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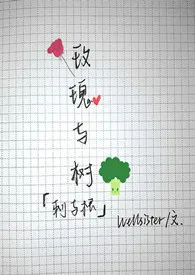



![《[新神榜杨戬]逆风执炬 姐狗|精神gb》小说全文免费 温惑喝大就瞎写创作](/d/file/po18/781748.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