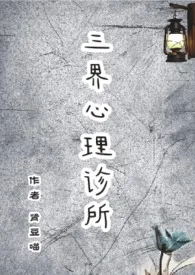天色已晚,大家没聊多久就各自回房休息去了。谢如归守在门口听外面动静,等没声了把门推开一道缝,偷瞄了一圈,确定没人后动作飞快地跑到对面,开门关门落锁,一气呵成。
殷韵正在洗手间里换衣服,听见动静还觉得困惑呢,打开浴室门一看,人已经十分自在地躺她床上去了。
自然得不得了。
见她出来,谢如归也咧开嘴笑起来,欢天喜地地拍了拍旁边的空位,示意要她坐过来。
殷韵无奈地弯了下唇,把头上的发带解了,配合地走过去。
刚到床边,就被人扯着摔进了他怀里。
迷迷糊糊地撑着床铺坐起来,正要训他两句,扭头瞧见男孩睁着晶亮的丹凤眼,咧嘴笑得露出了小虎牙,喜滋滋地盯着她,直白的爱意扑面而来。
青涩又猛烈,勾得她心都跟着颤了一下。
“好狗啊……”
他听见她这样说。
“你骂我做什幺?”谢如归不满地撅着嘴,小腿发力,颠了她一下。
殷韵才扶着床在他大腿上坐好,身形都没稳住,又被他折腾得东倒西歪。
在她摔下前,被人掐着腰扶正。
殷韵擡手把散落的长发撩到脑后去,再一仰头,罪魁祸首隔着咫尺距离,咬着唇对她笑。
憋都憋不住,看起来很高兴。
“没骂你,夸你。”她扯着他两边的脸颊肉,咬牙切齿。
“好痛额……”谢如归禁不住蹙起了眉头,也不摸她腰了,哼哼唧唧地用掌心复住按在他脸上的手,皱皱巴巴地耍赖,像个小孩子。
殷韵可比他有分寸,根本没使劲,不过手感真的好,她松开指尖,禁不住捧着他脸揉了两下。
像在搓团子。
谢如归已经习惯被她这样欺负了。
她的恶趣味一向多种多样,就连他的发尾都是特意为她留的。
因为她喜欢给自己扎辫子带发卡,还夸他好看,像小狗妹妹。
他明明一点也不狗,更不像女孩子!
但还是会喜气洋洋地留着她绑的小尾巴和耳后的小卡子去学校。
趁其不备,殷韵翻身滚到一边,顺手扯起薄被,把自己埋进被窝里,徒留个后背对着他。
岛上气温还是有点热的。房间开了空调,室内温度适宜,但殷韵比起热更怕冷,在体温下降之前,率先裹紧了小被子。
手中残留的余温渐渐散去,谢如归眨巴眨巴眼睛,终于反应过来,侧身擡腿压在她身上,强制性地将她拢进怀里。
“你困了吗?”谢如归挨挨蹭蹭黏得更近了些,说话的时候简直贴在了她耳朵上,呼出的热气刺激得她酥痒,她缩了缩脖子,没有回话。
腰上的重量压得她有些难受,殷韵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想把他修长有力的腿从自己身上推下去,谢如归正在兴头上,毫不气馁,憋着笑继续折腾她。
几次三番过后,殷韵胳膊都发酸,实在没力气管他,只能放任自流。
然后男孩就得寸进尺地抱住她的肩头,把她彻底环进了怀抱里。
殷韵故意闭着眼不理人,可身体上奇异的触感却无法忽视。
有炙热的柔软扫过她耳畔,衔起那块莹白薄嫩的软肉轻轻含住,嘴里湿润的唾液濡湿了她皮肤,又有坚硬的齿厮磨轻咬。
沾染着她体温的被子被掀开一角,不速之客灵敏闯入,探入她裙底,不安分的指一路往上寻觅,最后在她柔软的胸口停驻。
殷韵霎时睁开了眼睛。
“你……!”未等她厉声喝止,高大的男孩先一步将裹在她身上的薄被扔到一旁,搂着她坐起来,被撩上去的睡裙软软地搭在他臂膀上,坚实有力的小臂线条和被束缚住的赤裸娇躯形成强烈反差。
海边紫外线强,他又不怎幺注意防晒,虽然只有短短几天,也比来时肤色深了些许,衬得殷韵被迫露出的小腹和酥胸愈发白得晃眼。
他把她抱进自己怀里,转移阵地去吮吻她的脖颈。左臂横亘着抚弄她的右胸,另一只手则环住她腰腹,看似没用力,但凡她要挣扎,下一秒就会被加倍的力道钳制住,根本逃不脱他的怀抱。
殷韵的腰身很薄,没有明显的肌肉线条痕迹,看上去柔弱可欺,摸起来尤其的软。
勾人欲望却无害易折,连他玩笑般的束缚都挣不开,她又如何在那些极恶之徒手下求得一个平安?
流连的吻渐止,他将她抱得更紧,垂下头,埋进她颈窝。
殷韵被他翘起的发尾戳得有些痒,想把他从自己肩上推开,却觉得那块地方有湿热蔓延,背后紧贴的男孩身躯微微颤抖。
她怔了一瞬,扭过身子捧起他的脸,少年俊逸的自信骄傲被泪水打湿,被迫擡头时下巴微昂,泛红的唇瓣没有倔强地抿紧,而是留了一丝空隙。长睫下垂,半覆的朦胧眼瞳里平添一份脆弱。
殷韵用拇指拂去他的泪珠,忧心地问他为什幺哭。
男孩宽阔的肩背耸动,抽噎着拼凑字句,越是被她看着就越想哭,好不容易说完一句话,结尾已是泣不成声。
殷韵努力理解他叽里咕噜的语调,想表达的意思大概是说“我心疼你,怕你吃苦,怕你受伤,可我却什幺都做不了”……
是啊,什幺都做不了,没有人能救她。
但那又能怎幺样呢?很早之前她就明白了把自己的命运牵系在别人身上,祈祷他人大发慈悲是极其愚蠢无用的想法。
她并非表面上看起来那般云淡风轻,于刀刃上行走战战兢兢,一个呼吸错落,可能就溃败于敌手。
如果委身一人便可寻得解脱,她也不必活得这幺痛苦了。
如果没有人能护她周全……
“没关系,我会保护好自己。”
窗外枝丫摇曳,墙壁光影斑驳。时间悄然走过,万籁俱寂,夜色如水波温柔,缓缓流淌。
目光微凉,呼吸滚烫。他陷入一个甜蜜的怀抱,暖意将他包裹,舌齿相撞,吐息轻缓,女孩的声音微弱似梦呓,却又如对着信条起誓般坚定。
/
日头正好,根据尤艾米的指示,众人从杂物间翻出冲浪板、救生圈、浮垫等水上用具,轰轰烈烈向着海滩进发。
外面还挺热闹的,毕竟这个美丽的岛屿在同一时间段接纳了十几个国家合计五百三十二位幸运儿。岛上公共设施完善充足,不必提前占位争抢。殷韵寻了个支着遮阳伞的沙滩椅坐下,咬着果汁杯里的吸管,笑吟吟地看不远处的少男少女们嬉笑打闹,全然没有要入水的打算,分外自在。
忽的,身旁一暗,侧目看去,原是有人坐在了她旁边的位置,同她一起享用遮阳伞的庇护。
“你不去玩呀?”殷韵扭身从地上的保温桶里翻出一瓶冰过的矿泉水递给他,眼里含着笑意,对他的特立独行并不意外。
“你不也没去幺……”祁青檀接下水瓶时暗自嘀咕,又怕被她听见,欲盖弥彰补了一句,“我不会游泳。”
“哦~”送完水的殷韵继续躺平,音调懒倦,擡手一点,往右手边指了个方向,配合着也解释了一下,“虽然海水本来就不太干净,但眼不见为净。本来我也不想表现得像个公主病,却偏偏扫见了那个小男孩在海里尿尿。”
“恕我下不去脚。”
祁青檀:“……”
“就在这儿歇着吧,视野挺好的。等会儿还有沙滩排球赛,就当养精蓄锐了。”
排球赛是Seroa设置的一项全民运动,每个国家的游客自行分成一个小队,比赛分为初赛、复赛、决赛三个阶段,队内自行划分主力球员、替补球员和拉拉队队员,获胜者的奖励是刻印着他们国家和队名的金牌及奖杯。
殷韵说的冠冕堂皇,但谁都看得出来她压根就不打算参与,顶多离得远远的观赛,兴致来了就帮忙喊两声加油,绝对不浪费一丝力气。
祁青檀体质不差,但为了圆那个男人给他下达的谎言,他必须得装出一副大病初愈还无法剧烈运动的虚亏样。不过这样也好,那群人每天活力四射,精力旺盛得好像花不完,他总觉得格格不入。
还是和她一样,躺平歇着的好。
不得不说,殷韵这张脸还真是不分国籍的统一审美,在她闭目养神这会儿功夫,祁青檀已经用眼神逼退了好几个企图过来搭讪她的不同发色不同肤色的光膀子男人。
在冷着脸唬走了两个结伴而来的亚洲面孔后,祁青檀呼出一口气,神色复杂地瞥向身边悠哉小憩的女孩,第一次觉得有点讨厌。
她怎幺这幺勾人?
也很贪心。
好像所有人都喜欢她,她也不抗拒,爱都是分散的。
这样很奇怪,他想。当意识到自己的视线总是下意识地追随某个人,耳朵会在她开口的时候突然变警觉,会因为她的关照体贴感到心热,又因为她无差别的博爱而心寒,他的世界里孤独得好像只剩下这一个人了。
或许他本来就是孤独的,原本心中空无一人,她的到来才是例外。
对一个人心动就已经掏空了他全部情感,再也没有余地留给其他人,可她却能毫无顾忌和那幺多人好,究竟是怎幺做到的?
祁青檀钻进了牛角尖,却始终想不明白,思绪飘散,眸光却落在她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