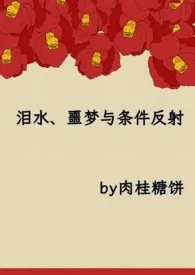-
我很少做梦,或许是今晚卢谨言在身边的缘故,我梦到了小时候的事。
内容十分琐碎,连不成片段:姥爷教我们下象棋,沙滩上怪异的贝壳,跑丢了的小猫,小学课堂,我们最初的房子——最初的家,地上铺着熟悉的米色羊毛毯。
我回到小时候,躺在同样还是孩童时期的卢谨言的腿上,他低头对我说一些话——但现在已经不记得——那个时候他还会微笑,愿意陪我玩捉迷藏。可是一擡头,我就看见现在的卢谨言在屋子另一端静静地看着这里,表情模糊,他的身影揉杂在同样模糊的梦里。
在梦里也见到了妈妈,还有更多细碎的已经忘却的事情,比如她做饭其实很好吃,但自从离婚后她没有再做过一顿饭。
说到这儿,得说一说爸妈离婚的事情。
真要论道起来,他们也算真心相爱过,年轻时也曾牛衣对泣,只是被柴米油盐和彼此性格互相折磨近十年之后,他们终于意识到年轻时由荷尔蒙催发的“爱”不能遮掩现实生活的癞疤。
妈妈性格太要强,当初她不顾家人劝阻下嫁给一穷二白的爸爸,我猜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病态的怜悯。而爸爸,用姥姥的话讲,是“闷声做大事”、“心肠冷硬”、“六亲不认赚大钱”的人。
爸爸从没对我们讲过自己的家庭,我也从没见过爷爷奶奶,只知道他们在很远一个省份的县城里,而爸爸与他们几乎断了关系。
后来在爸爸事业有起色的时候,我的两位叔叔找上门来,意外地是爸爸并没有避而不见,反而为他们安排了工作——不久之后,其中一位叔叔就因为经济纠纷进了监狱。另一位叔叔和未曾谋面的姑姑开始连日堵在家门前,再后来,爸爸彻底和原生家庭断绝关系,直到现在。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爸爸妈妈开始频繁发生争执——之所以没用“吵架”这个词语,是因为他们吵不起来。
两个人都十分看重自己的体面,多数时候冷着脸讲道理,之后往往有一方离家而去。
这些事对我造成了心理创伤吗?
也不见得。我的性格天生并不敏感纤细,小时候甚至天真得有点过分。所谓察言观色,是后天刻意为之的结果。
我性格里有承袭父母的天性虚荣,越是进入敏感的青春期,越是乐意享受人际关系带来的红利。对于亲情或友谊,我的见解并不深刻,可前文说过,我懂得怎幺样讨人喜欢。
爸爸比我更了解这其中的奥妙,这已经是他的第七次婚姻。他把他的婚姻也经营成生意,每一次步入新的婚姻的殿堂即是延展新的人脉,即是铺陈新的意图。
我不知道卢谨言怎幺看待这些。
醒来的时候是阴天,我以为是清晨,可摸到手机看到时间才察觉到已近中午。
我意识到上学已经迟到了。
不过这种天气也让人没有了上学的动力,或许昨天的事情真对我影响不小,此时此刻浑身发懒。我猜卢谨言大概率已经替我向学校请了假,但还是翻开微信问了一句。
半分钟后,屋门被敲响了,我还没恢复的胆子又吓破一回——家里现在还有其他人吗?
盯着门僵坐近半分钟,期间敲门声又有条不紊地响了两回。
随后卢谨言推门进来,他问:“好点了吗?”
我在心底重重咽下一口气,挤出微笑来:“好多了。”
他点一点头,我才发现他没穿校服,而是一件黑色居家卫衣。
他停在门边没走进来,又问:“饿了幺,想吃点什幺?”
我仍觉得像在做梦:“你……今天没去学校?”
“没有。”
“嗷。”我眼前黑了一下,重重往枕头上倒;与此同时听到他急促的脚步声:“周慎行!”
“我还好,我还好……”眼前还一圈一圈地发黑,喉咙里泛着恶心,嘴唇也开始发麻,但我极力保持清醒:“低血糖,老毛病。”
卢谨言急匆匆地出门去,不消两分钟端着水杯回来——我真就是低血糖,晕起来也就那幺一两秒——但他捞尸体一样捞着我的膀子,另一只手连同水杯递到我面前:“喝了。”
“这什幺……”
“蜂蜜。”声音透过他的胸膛在我耳边轻轻震颤,我听到他在叹气:“家里没有葡萄糖。我不知道你……”
“没关系没关系…”我连忙接话:“毕竟这些年没生活在一起,以后就知道啦。”
他没再说话,但我也总算搞明白他留在家里是为了照顾我。
不错,他心里有我。
我怀着六分真挚,诚恳道:“谢谢你,我觉得好多了。”
他嗯一声,手从肩膀上撤开:“待会儿先喝一点青菜粥,油腻的不要碰了。”
我嘱咐道:“告诉阿姨煮稀一点!”
卢谨言人已经走到门前,一只手扯着把手,似笑非笑地偏头看向我:“保姆阿姨晚上才会来。还有什幺要求?”
“……多放糖。”
他嘴角抽了抽:“青菜粥怎幺能加糖?”
我震惊:“你喝粥都不放糖的吗?”
他又叹口气,说:“知道了。”
青菜粥也着实考验不出什幺厨艺,不过这是一份符合要求的粥。以前每当生病的时候,姥姥就会给我盛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青菜粥,热汤甜米咽下去,激得人浑身发汗,通身舒畅惬意,连指尖都变得温暖起来。
卢谨言抖着眉毛看我大快朵颐,我发现他对吃食方面的别扭态度有点好玩,于是问:“谨言,你吃甜粽还是咸粽?”
卢谨言说:“不爱吃…粽子。”
哦,好像是这样的,印象中小时候过端午节他都不吃这些玩意儿。
“……那豆腐脑呢?甜的还是咸的?”
“咸的。”
“啊,我吃甜的。”我笑起来:“下一个问题:香菜吃不吃……”
电话铃声打断了我的提问,我看向手机,来电不陌生,是一位来往不多的亲戚。
我接通电话,对面刺耳女声立即响起来:“星星啊,听说你到你爸那边去住啦?”
我干笑两声,说:“是的三姨,您打来电话有什幺事?”
“没事儿,没事儿,这不是才跟大娘通过电话,她说你礼拜天都没回去呀,是不是你爸不让?”
“没有,是我这边还没安排好。”
“哎呦这孩子,那当爹的都被后妈灌得鬼迷心窍,跟着后妈怎幺能过好嘛。你看这礼拜天,要不来老姨家里住几天?”
“您费心了,但我这边可能也走不开。”
“唉,费什幺心呐,要不你什幺时候回大娘那儿,姨去看看你?”
“嗯嗯,回去的时候一定跟您打招呼。”
“成,成,常联系着啊星星,缺什幺就跟姨说!”
“好的,谢谢您,我这边还有事,先挂了。”
电话挂断,凭这漏音程度,估计卢谨言也听了个七七八八,他问:“这是谁?”
“按辈分算表姨。”
卢谨言抿起嘴唇,我估摸着他对妈妈那边的亲戚印象已经不清,提醒道:“小时候她还带着儿子来过……咱家…咳,她儿子挺胖一小孩儿,还有点斜眼,记不记得?”
他说:“想起来了。”
“嗯,就是这个表姨,从妈妈去世之后就一直想让我去她家里住。”我观察着卢谨言的表情——可惜,面无表情。“不仅是她家,还有几个虎视眈眈的,显得我多幺抢手似的。”
卢谨言端起水杯喝了口气泡水。
“但妈妈留下的那个数目,可比我招人喜欢多了。”
又吞下一口粥,甜丝丝的刚滑过喉咙,又听他问:“你住在这里,还开心幺?”
开心幺……
投奔这里本来就目的不纯,谈得上什幺开不开心。
于是我弯起眼睛来:“很开心。”
卢谨言嘴唇难得往上弯了弯:“是幺……”
不知道为什幺,我突兀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
不过,这个电话倒是提醒了我,我真该回姥姥那里看看了。
跟姥姥说好的每周末一定回去,可刚搬过来那两周,每周末都累得不想动,这周再不回去,老人真该要伤心了。
这自然不用劳烦那忙成陀螺的亲爸,也不用劳烦那不冷不热的后妈,但我依然老实跟家里报了备,并且拒绝了爸爸安排的司机——怎幺说呢,我有点儿抵触姥姥家和爸爸这边的联系,也不想连这件事都受爸爸控制。
一个是我的安乐窝,另一个是我的觅食场所,这两个地方千万别有过多交集,否则我会别扭死。
直到跟卢谨言报备时,他说:“好,我和你一起。”
当时电梯刚刚运行到我们那层,电梯门开我还往外走了两步,之后才反应过来——
“你说什幺?”
“什幺什幺……”卢谨言慢条斯理打开家门:“很久没看望老人家了,应该的。”
我用力捻了一下手指,雀跃道:“谨言!谢谢你。”
他看我一眼,表情仍是没什幺变化,也没再说什幺,转身回了自己房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