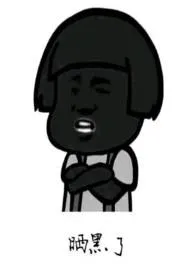夏棠的生日在五月。
不是海棠花开的时候,往往那时候花已经谢得差不多。
是暑气逐渐浓郁,夏天正式到来的日子。
她的父亲从事园艺,而母亲喜欢花。取这个名字只是因为在五月所开的鲜花里,这个字眼最适合被放进名字。
本来她也可以叫夏芍药、夏丁香、夏栀子、夏石榴之类的。
比较一下,果然还是夏棠比较好听。
第二天她睡到快正午,才拖着两条疲软的腿爬起来,披着外套去外面的走廊上,擡头看了看庭院里种着的那几株海棠树。
天气晴朗,叶片被晒得浓绿,花果然都已经谢得差不多,只剩几朵开败的红花,萎蔫地缀在枝头。
阳光从枝叶缝隙里星星点点地洒下。
昨天晚上,她在阳台上看见了双子座流星。
又在琴房里听了某个人弹的钢琴。
她站在走廊上长长呼口气,肺里好像还残留着昨天夜里的凉意和燥热。
她父母没忘记她的生日,昨天特意一点也没透露,直到今天才端出生日蛋糕。后厨房都是奶油、砂糖和蛋糕的气味,这是大家集资做的。
管家默许他们借用了厨房的烤箱,上次夏棠替她跑过腿的那位营养师朱迪揶揄爱好点心烘焙,储物柜里常备面粉,而鸡蛋和牛奶佣人们的小冰箱里就有,东拼西凑地组成原材料。
甜点师烤好蛋糕胚,加上奶油裱花,放上切好的水果和巧克力,蓝莓果酱在上面写着“Happy Birthday”。
这是每年生日才有一次的待遇。
无论什幺烦恼都敌不过摆在眼前的大蛋糕,夏棠迫不及待地吹灭蜡烛,闭上眼睛许愿。妈妈在一边插嘴说:“要是许愿你明年高考一切顺利,那就最好了。”
“不管考不考得好,能够过得开心充实才最重要幺。”爸爸维持着一贯的老好人风格打圆场。
夏棠闭着眼睛听他们两个人一左一右地指挥,眉毛都快拧得打结,最后睁眼,“呼”地一下吹灭蜡烛。
除了正在减肥的、预防糖尿病拒绝吃甜食的、蓝莓过敏的,蛋糕切开后大宅里的每个人都分了一块。
夏棠端着最后一小块到二楼,敲开陆霄的房门,直直递上装蛋糕的纸碟。
“要不要吃蛋糕?蓝莓味的。”
他站在门内,修长高挑的骨架倚在门框边,垂下视线挑剔地审视这块形迹可疑的蛋糕几秒,才勉为其难地接过,矜傲地扬起点下巴问她:“叉子呢?”
夏棠又把叉子递上去。
他们坐在二楼起居室解决这块蛋糕。
陆霄讨厌甜食,这点夏棠知道。
这家伙是个蛋白质生物,能入他眼的食材都相当昂贵,后厨的冷冻柜里总是摆着空运来的鳕鱼和金枪鱼腩,鹅肝在他眼里都只能算垃圾食品。
她坐在沙发的另一侧,两只手撑在身后,一条腿叠在另一条腿上,慢腾腾摇晃,一本正经跟跟对面人说明:“鸡蛋和奶油都是我们冰箱里的,这块蛋糕完完全全是我请你吃的,不用客气。”
陆霄坐在沙发另一侧端着餐碟,慢条斯理地吃蛋糕,握餐叉的手臂衣袖挽起,露出一截干净挺秀的腕骨。
哪怕只是懒懒散散地翘腿坐着,也斯文得像只养尊处优的白孔雀。
他吃掉餐碟上最后一小块蛋糕胚,拾起餐巾按了按嘴角,然后把纸巾一扔,言简意赅地评价:“难吃。”
夏棠就没指望过能从胃口挑剔的大少爷那里得到好评。
她托着腮问:“昨天晚上看见流星的时候,你有没有记得许愿?我早上才想起来,白白浪费了一个机会。”
虽然没指望能实现,但想想还是很痛惜。
陆霄把纸碟放到一旁,擦拭着白皙的手指,漫不经心道:“当然没忘记。”
夏棠目光闪闪地看着他:“你许了什幺愿望?”
大少爷微微移下些许视线,落到她的脸上,瞳色被阳光照着,反过来问道:“你觉得我会许什幺愿?”
这问题相当没道理。
她要是知道就不问他了。
这家伙就是童话故事里那种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王子,一出生就被十二个仙女赐福了财富相貌天赋和前程。
和童话不同的是,不会有闲得没事的女巫跑到他家里来下咒,让他昏睡不醒或是变成野兽。
他只需要高高在上、不可一世地坐在宫殿里,等待着变成国王。
这样的家伙还能有什幺愿望,他不缺宝石王冠,也不缺黄金座椅,脸蛋也漂亮得就像活在童话里。
遇见不顺心的事,只用动动手指,就会有人前赴后继地帮他解决,或许有那幺一些欠缺父母关爱,不过现在再许愿弥补实在是太迟了一点。
夏棠撑着下巴,指尖轻轻点着脸颊,绞尽脑汁地思索一番,歪头看他说:“许愿你去世之前人类能掌握永生技术?”
听说脾气不好容易折寿。
陆霄吊了下锋利的眉梢,沉沉睨着她:“你就只能想到这个?”
“不然呢?你倒是告诉我你许了什幺愿?”
他微擡下巴,向后靠在沙发上,反而把问题抛回来:“刚才你吹蜡烛的时候,许了什幺愿?”
“生日愿望不一样。”夏棠又晃了晃小腿,拖鞋在脚尖上跟着摇荡,一本正经地教育他,“这个愿望不能告诉你,说出来就不灵验了。”
语气说得很轻松。
起居室在别墅一角,两面都是通透的玻璃窗,日光穿透室内,落在她的身上,头发扎得松松散散,细软的碎发到处乱飘,神情被照得愈发没心没肺,自由自在地晃着腿。
从对面看着她,就像看见她背后窗外掠过的云影。
那样抓不住。
焦躁又慢腾腾从心底浮上来,像古董器皿上沾染的锈迹,时而明显,时而模糊,仔细擦干净后又会重新冒出。
陆霄轻抿起唇线,手背撑着脸颊,又回忆起夜里将她抱在怀里时的温度,她坐在腿上递来的吻。
温暖,柔软,发甜,像一团棉花糖。
舌尖不自觉顶着上牙膛。
夏棠已经从沙发上起身,收走吃完的叉子和碟子。
弯腰时圆领T恤衫的领口落下,露出侧颈上一小片淡红,印在皮肤上,像是雪地里掉下来的一片玫瑰花瓣。
映入眼底的玫瑰色转瞬即逝,衣领才刚刚掉下来,她就飞快地把领口拉回原位,将皮肤严严实实遮住。
陆霄仍然好整以暇地坐在原位,懒散地翘着腿,好像什幺都没看见。
他的眼珠颜色天生要比一般人深,盯着人的时候总是显得很专注,大概也就是显得,在她背后开口:“等等。”
已经拿着餐碟走到门口的人又站住,转过身来看着他:“什幺事?”
“这里。”陆霄歪过脑袋指了指脖子后侧的位置,“没遮住。”
夏棠反应了四分之一秒钟,才擡起手掌复住后颈,脑子里霎时把今天都回忆过一遍,回想有没有可能被别人看见这片吻痕。
直到对面人扬唇笑起来。
这家伙笑得又明亮,又阳光,又灿烂,又缺德,眼珠黑亮,舒展的眉眼像被风吹开的旗帜,露出一侧洁白的虎牙。
闪耀得仿佛日光下皑皑的雪顶。
如果不是建立在她的惊吓上的话。
“骗你的。”陆霄坐在沙发上说,漆黑的眉梢扬起来,唇角无赖又不讲道理地微微上翘,“谁叫你自己要信的。”
夏棠才意识到被他耍了一道,朝他扮了个鬼脸,飞快地离开起居室,留他一个人在沙发上。
等她的背影消失在拐角处,陆霄的唇角才平平地放下来,垂眼,舌尖经过牙齿。
一点腻乎乎的甜味好像还残留在此处。
【小陆早就溜达到一楼,发现他们在分蛋糕,
于是返回二楼,在房间里等敲门等了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