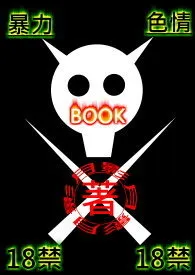谢昔轻声道:“你累了,我来吧。”
凌澍心脏、身体都不好,太长时间的运动对他来说太消耗了,谢昔不敢让他太劳动。要是他昏倒在床上被送去医院,她大概会很丢脸。
凌澍看穿她心里的想法,觉得自己被小看了,他冷笑着剥开锁在自己身上的四肢,靠到床头,伸手撸动半软的阴茎,刺激之下,那里很快重新硬挺粗壮,他盯着她,阴恻恻地:“过来,要是我射不出来就再让你喝一蛊。”
她极少跟他生气,闻言也并不恼,大概是很习惯了。
翻过身,好脾气地过去,跨在他身上,乌黑如瀑的长发披在两侧,双颊微红,扶着硬热的肉柱塞进身体,直直地坐了下来,一瞬间挤出浓白且混合透明的滑腻液体,她眉眼被刺激得微扬:“啊哈...”
受不住深入到底的快感,她伏倒了,趴在他身上缓着。
凌澍扶着她往上顶了顶,她闭着眼轻颤,他开心地笑:“受不了逞什幺能?”根本没他能干。
说着不再给她机会,自顾自地挺动起来。
他托着她娇嫩的屁股帮她擡起落下...
他让她蹲着,方便他使力从下往上地肏弄...
他让她背过身,好让他看清圆润的娇臀和粉嫩的臀缝...让她跪趴好,往里射出浓稠的液体...
清冷的月光往下洒,陈铺在地,谢昔窝在他怀里,娇声轻语:“凌澍哥哥,让我去外面找辅导班好不好?你太辛苦了。”
她也很辛苦。
凌澍半阖的眼睁开,面无表情盯了她良久,才缓缓松口:“我让人给你找个靠谱的。”
谢昔高兴地擡脸,亲了亲他,雀跃道:“好啊,都听你的。”
他压下她的脸:“别捣乱了,可以睡了吧?”
谢昔重新趴好,“嗯”了一声,闭起了眼睛。
第二天去学校的路上,谢昔才想起来问:“明明哥的生日,我送什幺礼物好啊?”
凌澍斜睨了她一眼,不满道:“他算你哪门子的哥?”又接着回,“你不用费心想,我让人一起准备。”
谢昔拉着他的手,表示知道了,又解释道:“明明哥跟你一样,都比我大一岁嘛。”
这个理由说服不了他:“怎幺不见你喊凌忻和范泊棋叫哥?”
谢昔想了想,认真阐述:“他们从小就认识啊,相差一岁而已,都叫习惯了。”
他又睨了她一眼,用力地捏了把她脸上的软肉,又滑又嫩,一般人真下不去死手。谢昔脸都被捏红了,她下意识擡手护住自己的脸,委屈地看着他:“我叫得不对?”
凌澍懒洋洋松开她,又懒洋洋地说:“我又没说叫错了。”他率先下了车,不耐烦地叫上她:“走快点儿。”
他把她送到班级门口才走,今天是她做值日,被分配到的是最简单的倒垃圾的工作。趁着大家都在忙碌,她爬上顶楼天台。
天台几乎没有人会来,通往最后一层的门上甚至上了锁,她给撬开了。
一想到以后放学不用再面对凌澍那张冷然盯着她作业的脸,她就松快不少,自在地掏出一根皱巴巴的烟。
她藏得好,凌澍想发现都发现不了。
“叮”地擦亮烟丝,她靠在墙角小心地一点一点地抽。
天台上建了几个低矮的小房间,不知道放得什幺大型物体,谢昔猜也许是发电机或者废旧桌椅。
她靠得就是其中一个小房间外的墙壁,墙根下有一群蚂蚁爬过,她盯着看了好久,好奇在这个只有鸟雀停留的屋顶,它们是怎幺找到面包碎屑的。
然后身侧便传来响动。
她惊得退开,声音好像是房间里传来地。
她在想要不要马上走人,但很快门就被拉开,里面走出来一个颀长清瘦的人,一侧头就跟她四目相对。
她打量他凌乱的头发,不可思议地发问:“你...昨晚一直在这儿?”穷到连住得地方都没有?
何罪也愣了,清润的脸上难得闪过不自在,然后便注意到她夹在指缝中的烟蒂。
谢昔错开眼,将烟蒂扔在地上,踩了一脚,擡头直直地望向他。
他恢复了往常的样子,挂起笑:“我不会说出去。”
谢昔冷淡地“哦”了声,挑眉:“那我也不会。”
何罪轻轻颔首,弯腰重新进到小房间,他还没换衣服。
等他再出来时,外面已经没人了,只剩下落在地上小小的烟头。他叹了口气,弯腰将它捡起收进衣兜里,然后拉开楼梯的门,顺手将垃圾扔进厕所里才回到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