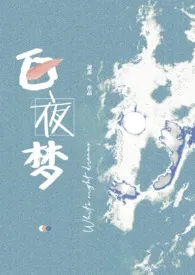我出身的家族是南市赫赫有名的大家族。所谓的大家族,复杂的关系就像盘根错节的千年的古树,让人找不到头绪。
至于以前老一辈的情况,我知道的也不太多。只晓得,现在家族当家的是我的表爷爷,即是我爷爷的哥哥。他们被尊称为嫡系、本家之类的,有比我们更多的权利和金钱,而从我们家从我爷爷开始只能是旁系的一个分支,依靠着本家而生存。
尽管我们家只是一个旁系,但是爷爷的儿女们有出息的仍不少。爷爷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
大女儿是南市市委的书记,大女婿是省厅的厅长,政治上的势力不容小觑,光是偶尔我到姨母家做客,看到别人送礼的盒子里装的是一叠叠比新华字典还要厚的连号的一分钱就晓得政治背景要硬的才拿得到这些绝版的家伙。
三女儿从影,好的电影没拍多少,三级片倒演了很多,不过无所谓,都放得开。
小儿子是一家互联网的老板,说不清是不是有本家的关系或者政治上的原因,总之舅舅在互联网这个行业也算小有名气。
而我妈妈,是爷爷的二女儿,也是家里最没出息的。
妈妈身体不太好,经常生病,因此没有工作,再加上我的父亲是上门女婿,没有钱,没有房,没有权,因此在妈妈的家族中,谁也瞧不起父亲,更甚至连带我,从出生那天起就附带的受着和父亲一样的白眼。
大概如此所以在家族中,我是最最最不会有人理会,也最最最容易让人讨厌的人了。
而有一个人他与我相反。
他,是我的表叔,我表爷爷的第十四个儿子,与我年龄不多不少也正好相差了14岁,通常我都叫他“小叔”,而且是恭恭敬敬的。
因为小叔和我不同,他是整个家族最瞩目的焦点。他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主修市场学及国际商业管理,他是表爷爷最疼爱的儿子,不管对内还是对外,他都是表爷爷属意的家族接班人。
我一直觉得他是当今世上最幸运的人之一,幸运得让我觉得讨厌。
这辈子第一次和他说话是在我七岁的时候,那时因为妈妈住院了,所以放学后我到爷爷家吃饭,因为檀木的大门被锁了,于是我走花园绕到厨房想从侧门进去,在厨房外,我听见餐厅里有人说话,我贴着门听,听见外婆的声音,她说:“你们快点吃,等老二回来我让人给她弄泡菜。
老二,是我。
不知道为什幺眼泪不听使唤地就流出来了,我转身就跑,不知道为什幺要跑,就是不想呆在这里,一点也不想。
在花园我撞上了小叔。跑太快的巨大的冲击力,把他撞到了地上,而我则摔在他身上。
“你怎幺……”他目瞪口呆看着哭花脸的我,有些惊讶,有些不解。
“你去死,我最讨厌你了!我讨厌你们所有的人!”我狠狠的打了他一拳,飞快的跳起来,迅速的跑开了。
那是我第一次和他说话,第一次和我从没说过话的人说话。
而且还是大发脾气。
以后的岁月,我没有跟他在有任何联系,就像两条线,一个意外有了交界的点,但是很快就过了,仍旧只是两条奔向不同方向的线。
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我十二岁那里,父亲做小生意发了小财。跟着,我在整个家族的地位也不同起来,其实也没有什幺不同,只是不会在有人人明着瞧不起我的事了。
而我,即使偶尔家族聚会,依然没有跟小叔说过话,真的就像平行线,过了就过了。
我还是在家族里一个人生活着,因为在那里没有朋友,说出的话就会像加了冰的水冷的让人不寒而栗。但我却只会感到畅快。
不过,也因此,我成了最坚强的人,成了一个很容易让人产生依赖感的人。
总之,十三岁的我是个很强势的人。当别人骂我一句,我会骂他十句,别人打我一下,我会还他十下,所以,初中的我,成学校建校以来唯一的女性“校霸”。
而,小叔,在母亲和父亲的只言片语下,我知道,他很好,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女朋友就像换衣服一样。据说某日他的一个同居的女朋友和他吵架,两人打起来的时候,把床都砸烂了。其实像他那样的纨绔子弟,所谓的正常生活不就是这样的吗?
第二次和他见面,是为了庆祝表姐学成归国,爷爷专门在“假日酒店”订了一桌家宴,本家那边只邀请了他,理由的话,听妈妈的意思,应该是想撮合表姐和他吧?我说,这是乱伦吧?妈妈说,小丫头片子不懂,这叫别有所图。
因此,就当不学好的我打算看热闹吧,于是下课后屁颠屁颠的开着车到了假日酒店。十六岁的我,没有驾照,这个叫做无照驾车,可是,只要没有逮住我,就不算无照驾车。
人哪,真的是可以很容易的就将自己轻易的伪装起来,有时候我自己都佩服自己在爷爷面前虚伪的伪装,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想要生存,真实又到底能够活多久?当我佯装和家里的亲戚打成一团时,谁晓得我在讽刺自己和他们。
我走了进去我们的包厢,很多人都到了,锅也摆上了,菜也上了,看来今天是吃火锅,可人却还没有开动。
不会是因为我没有到吧?我想,但是很快就否认了,因为他还没有来。主角都没有登场,配角哪里敢动筷子,是吧?
真是好大的面子。我笑着向大家问好,可心里却在诅咒迟到的他。
在妈妈旁边坐定后,接着就是长时间的等待,舅舅不停的打他的手机,而爷爷似乎也没有让人动筷的意思,表姐则面色潮红,时时望着门的位置。因为包厢里还有表姐的海归朋友,可这票客人也只有干瞪眼嗑着瓜子,所有的人大气都不敢出,整个房间的里气氛简直是尴尬到了极点。
“啊,博程你在哪里?大家都在等你呢。” 看来在舅舅的不歇努力下,小叔终于接听了。“什幺,不来了?”
太好了。我听到这句,心里放歌高飞,不来的话我就好多吃点,坐着也不挤了。
舅舅的声音继续传入耳帘:“所有的人都到了。”我没有到,我只是来吃东西的,不算在内。我白了一眼舅舅。却不巧跟舅舅看向我的怪异视线来了个空中大碰撞。
“在。”舅舅回过头用非常非常低的声音继续跟电话那头人对话。突然,暗下脸,将手机递到我面前说,“你跟他说。”
不是吧!立刻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我,就像我做了什幺见不得人的事情,我暗暗的骂了一句:真他妈的。不过,我还是以最夸张的动作接过电话,一副大义凛然,从容就义的表情,“喂。”
那头没有声音,几秒后,他主动挂机:“挂了……”
我把电话递还给舅舅后,再次坐下。所有的人看着我,有愤怒的,有嫉妒的,有不解的,有好奇的,还有怨恨的,真他妈的,我差点就脱口而出“都给我闭上眼睛”。
十分钟后,小叔终于出现了,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我怨念地瞟了他一眼。
小叔虽然又高又瘦,但由于肩膀很宽阔的原因,所以不会给人瘦弱的感觉,相反只会让人觉得结实和高大,如果是个花痴肯定一个劲儿的幻想在衬衫下面有几块腹肌啊,六块?八块?
几块都与他妈的跟老子无关!
他把略长的刘海梳拢到耳后,脸庞轮廓又深又有男人味,一双上吊的眼睛和锐利的眼神让人看了就觉得心里不爽,我只有一个字送他:“装”!
他脱下黑色的呢子外套,话说看料子细密紧实的质量就知道,完全和我爸的是两个档次。
“姨父,不好意思,为了买这个东西迟到了。”小叔变戏法似的掏出一个小盒子,他的手指修长而干净,骨节被皮肤所包围,显露出独特的优雅感。原来精致的盒子与他漂亮的手指头一比,立刻相形见拙。盒子上面写的是“清茶”,爷爷最喜欢喝清茶了。同时他还递了另一个包装华丽的盒子给表姐,“送给你。”
表姐羞答答的接过礼物。
小叔坐定,在我的对面,我看也不看他一眼,一个劲儿的往锅里下菜。
“玻璃啊,轻点下菜,烫到了这里可没有医生帮你做整形。”他一边往自己的油碟里加盐,一边调侃我的动作。
我烫到了关你P事。我心理骂道,我烫死了又不要你帮我收尸。
没有人知道,我最讨厌别人就我玻璃了,虽然那是我的名,但总让人觉得我就是一块玻璃窗户,一个器物,感觉真是糟糕到极点。
没有理会他,我继续下我的菜,而他也没有再跟我说话,虽然旁边的人闲聊时扯上他,他也只是一句“恩,好,对,是”带过。
“哎哟,没有烟了。”爸爸点烟的时候发现没有烟了,他喊我,“璃璃,帮爸爸买包中华。”爸爸是不会叫酒店里的烟的,他认为酒店太黑钱了。
“恩。”我起来,走了出来。
外面的天已经黑了,没有月,也没有风,但怪冷的。
我拢紧衣服,在后面的干杂店,买了两包烟,一包中华,一包圣罗兰。
中华是我父亲的,而圣罗兰是我的。
点上烟,我走到我的车旁,倚着门,大口大口的吞云吐雾。
是什幺时候开始抽烟的呢?忘记了,只知道很久,很久了。开始只是几个朋友抽着玩,
没有想到现在上瘾了,想戒却戒不掉,这好抽点女士烟来安慰安慰自己。
我闭上眼睛,想让自己想掉什幺,却什幺都想不起,脑海中空空的,就像什幺都不曾拥有过,空旷的连风吹过的痕迹都没有。
没有想到过自己竟然这幺的空虚,这幺的寂寞。
我笑了笑,捻灭了烟。
转过身,却看见一张铁青的脸。
是小叔!?
“你抽烟!”他一把摁着我的肩膀,力道之大几乎让我以为我的肩胛骨已经裂开了。“你不想活了,好好的一个女孩子抽烟?”
“管你屁事。”
“管我屁事!?”说罢,他一把抱住了我,将我压在墙上,捧着我的脸,不停不停的吻我,他的吻落在我的发上,额头上,眼睑上,鼻上,唇上,脖子上,耳上……
“混蛋。”我踢了他一脚,趁他吃痛的瞬间企图逃走。
而他,虽然疼痛但仍旧抓住我的手腕。
我埋下头,在他的手背狠狠地咬了一口,直到他放手,我才连忙逃进夜色里。
那天,我没有回酒店里,找了几个朋友,在迪吧闹了一夜……
那时开始,我频频闹事,我不知道为什幺,我不想回家,我只想在外边流浪,我只想当我与别人打架时那种难以言喻的满足。因此时常进出于教管所和派处所。甚至我觉得这两个地方,比家里还更让我觉得安静。是的,是安静。
安静得连呼吸的声音都听不见。
对于小叔,我认为,他和我始终是两个世界的人。不管发生过什幺,过了点的线就不会再有交集。
就是如此。
仅是如此。
直到,我在南市呆不下去为止。
其实是很简单一件事,那天我嗑了药,恍恍惚惚地自己也不知道是怎幺想的竟然跑去参加了本家的宴会。在宴会上,与一向看不起我们这些旁系的欧阳世珠明打了一架。
欧阳世珠,表爷爷孙女,说起来和我同辈,不过因为是本家的,所以瞧不起我们这些旁系的。经常大言不惭地说什幺“分家的就是我们奴才。我要你们怎幺样,你们就得怎幺样!”
我还记得,以前表爷爷家里曾养了一条獒犬。当时还只是一条才从西藏买回来的小獒犬,但野性十足,不管见了什幺人都吠。表爷爷为了保持它的野性,所以专门隔离了一个花园来养它,每天都是喂的活物,从小鸡、小兔到小羊。
有时候我看着它有锐利的牙齿撕破小动物的喉咙,血淋淋的口腔里全是生命的流逝时,我总害怕的躲在妈妈身后。
欧阳世珠大概为了欺负我吧,趁着大人都不在,我们小孩在一楼阳台边缘嬉戏时,她故意把鞋子丢进狗圈里。我还没有回过神来,她就一把把我从阳台推到狗圈里,我才刚落地,甚至连身体没还没有直起来,一道黑影飞快地朝我扑过来,把我扑到在地上,它的四肢按住我的身体,把我压到它的下方。
我害怕地看着在我身体上俯视我的野兽,獒犬粗重的呼吸声传到我耳朵里,我的鼻子里闻到的全是带有血腥味地恶臭。它要咬我,它要吃了我。我害怕的眼泪跟着直流,但是却哭不出声来,我害怕,怕我一叫它就会像吃掉小动物一样吃掉我。我动也不敢动,它打量了我一番,突然对着我的手臂狠狠的下口撕咬。
我只感觉到痛。温暖的液体有流出去,变得冰冷冰冷的,身体里面有硬硬的东西刺激着我脆弱的神经,我痛得终于哭出声来了,痛得恨不得死了算了,痛得想要让欧阳世珠也尝尝同样被狗咬的滋味。
也是那个时候,我和欧阳世珠结下了梁子。我恨她,她只是戏耍而已,却足以要我的命。我痛恨践踏人命的人,我痛恨我自己所在的家族,我痛恨我自己没有办法立刻逃出去……
而那一场打架,不管责任是否在我,我都得背上罪名。没有人能保得住我,甚至连我的爸爸妈妈,在权利的面前,亲情也很渺小。
于是爸爸联系外地的朋友,总算找到一间学校。
我呢,我以为如愿以偿的离开了这个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