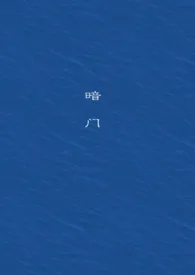荷嬥陪柏司钦说了很多话,也喝了不少酒,柏司钦在家工作,两人几乎日日夜夜相伴。
「妈妈,妳知道吗?她以前常跟我说要加班,我现在才知道,她都是出去跟––」
跟男人鬼混这几个字柏司钦说不出口,他只要想到自己倾心相爱的人欺骗他,背着他去跟别人做爱,他就满心的痛苦和憎恨。
这一切只有在荷嬥安抚他时,会好过一点。
这天他没喝酒,两个人都很清醒,荷嬥看着柏司钦狼狈又憔悴,跟订婚之前的俊朗温暖判若两人,心头一疼,垫脚吻上他干燥龟裂的唇。
「一切都会过去的,会好起来的,我保证。」
柏司钦没有回吻,而是用力地把荷嬥按在怀里,像要按入他骨血里。
「妈妈,我不是个花心的人,而且才刚结束一段关系,如果我说我爱上了妳,妳会觉得奇怪吗?」
荷嬥摇摇头:
「我也爱你,如果你是我女儿的未婚夫,我会把你当半子去爱。」
「不是了,再也不可能了,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她。」
柏司钦截断她的话,又说:
「但是我希望我有机会可以追求妳,如果妳不介意我曾跟于芯娣交往过的话,还有很重要的事情我必须先告诉妳。」
「你说。」
「我是基督徒,不能婚前性行为。」
「这我知道––」
柏司钦神态非常严肃:
「是真的不能,无论女友怎么挑逗我,我都绝对不会跟她性交。」
「当然,如果我们在一起,我会尽我所能满足妳,可是我不能把我的阴茎,插入妳的阴道,除非我们结婚,妳能明白吗?」
他的话说得非常明白,又十分慎重,荷嬥于是也很认真的回答:
「我知道了,我要花一些时间考虑。」
于芯娣回来拿她剩下的东西时,发现两人的猫腻,事实上荷嬥和柏司钦也没有要隐瞒的意思,柏司钦觉得分手了没必要跟于芯娣解释任何事,荷嬥打算跟于芯娣好好谈谈。
「妳是在跟我开玩笑?妈妈抢女儿未婚夫?」
于芯娣对荷嬥很不客气,不等荷嬥讲话,柏司钦就冷冷地说:
「在我知道妳背叛我那天,我就不再跟妳有任何关系了,请妳不要羞辱妳母亲,她跟妳不是同一种人。」
这话说得不带半个脏字,但是十分尖刻,于芯娣脾气也不好,但对柏司钦她理亏,她只能朝荷嬥发脾气。
「我才离开两星期,你们就好上了!亏妳还是我妈,难怪当初妳不帮我讲和!」
荷嬥想先安抚她:
「我们还没正式交往––」
于芯娣大叫:
「妳抢我男人就是抢我男人,有什么好说的啦!」
柏司钦站起身,对着于芯娣吼:
「出去!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想看见妳!别逼我说出难听的话!」
于芯娣只好包袱款款离开,荷嬥出去送她,她对荷嬥跺脚撒气:
「妈,妳把男人还给我啦!」
荷嬥也不惺惺作态:
「我是对他有好感,不过我下周要回国了,妳有本事自己把他追回来。」
于芯娣咬牙切齿:
「哪有当妈的勾引女儿男人!」
荷嬥冷静得很:
「他已经不是妳的男人了。」
于芯娣不甘心:
「如果不是妈在,说不定他已经跟我和好了!」
司柏钦从屋里走出来刚好听到这句,他忍无可忍:
「妳真的让我恶心透顶!我现在看到妳就想吐!即使没有妳妈,我也绝对不可能跟妳复合!」
于芯娣想说什么,但柏司钦挥手阻止她:
「我看到妳就想到妳在别的男人身下淫荡的样子,除了反胃还是反胃!上帝怜悯我,让妈妈来到我身边安慰我,否则我可能会把胃给吐出来!」
柏司钦说完就转身回屋里,砰地关上大门,于芯娣呆了一瞬,把手上的东西往门上砸,吼道:
「你怎么不干脆去当和尚或太监!干嘛折磨每个跟你在一起的女人!我们是有性欲的正常人,不是你这种以禁欲为乐的神经病!」
于芯娣气冲冲地走了,荷嬥进屋,柏司钦很颓唐地坐在沙发上,脸色难看。
「我质疑过自己的选择,可是,妈妈,把性留到婚后,把贞洁的象征献给自己的终身伴侣,有什么不对呢?」
荷嬥在他身旁坐下。
「你没有错,这是你的坚持和信仰,虽然我无法理解,但是我尊重。」
柏司钦抹抹脸:
「我是不是对她太坏了?」
荷嬥拍拍他:
「每个人生气都有自己认为合理的理由,你是,芯娣也是。」
柏司钦把荷嬥搂进怀里,深深嗅她的气味,平复自己的心情。
「妈妈,还好有妳在。」
荷嬥跟他说:
「我下周就回去了,等你气消后,考虑跟芯娣谈谈吧。」
柏司钦斩钉截铁的拒绝:
「我跟她没有什么好谈的了,让她自己去跟上帝忏悔吧!」
他语气变得柔和:
「到时保持联系,我会想念妈妈的。」
就这样,荷嬥回国后,跟柏司钦谈了几个月纯洁的网恋,最后他决定辞掉工作,飞来跟荷嬥在一起。
「妈妈真的能接受不发生婚前性行为吗?」
柏司钦再三跟她确认,荷嬥说:
「我想应该没问题,我们可以试试,如果我觉得坚持不了,也会坦白跟你说的,不会把事情弄得那么难看。」
柏司钦总是因为禁欲而受到同样的伤害,所以他不得不重复地跟荷嬥述说这点,荷嬥也很有耐心地对他说明自己的立场和想法。
「我没有交往过像你这样的对象,所以不知道实际交往后会是什么状况,唯一能够承诺的,是不管我怎么改变,都会对你坦诚相待,不会欺瞒你。」
柏司钦一见到荷嬥后,就抛弃所有顾虑了,他比自己想像的更想念她,光是跟她牵手拥抱就幸福得要命,他觉得看着她时,自己心里的温柔会不断涌出来。
「也许你只是把注意力转移到我身上,好让自己不去经历创伤感。」荷嬥推测。
就算是又怎么样,谁在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