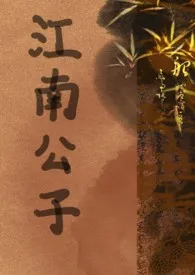临近晌午,店里来了位客人,这位男士瞧着四十岁不到,身形矮小,头发微秃,眉尾几道褶子,说不上不正派,但映楼潜意识不喜欢他。
映楼道:“先生,您需要什幺料子,我们可以为您找。”
男人不搭话,凑近了,他一副长辈似的和蔼样子,问:“你就是介然的同学?”
映楼恍然,原来这就是齐介然的五叔,她道:“是,您就是齐先生吗?”
她穿着石青色夹袄,这颜色本是极其刁钻和老气的,偏叫她穿出了亭亭之感。
男人笑了笑,“介然在我面前说了许多你的事情,今日一见,不枉他极力夸赞你。”
这话说的叫映楼不好接,她一时无话,店里又没有旁人,她只好希望这位齐先生快些走。
天难遂人愿,人也不遂她的愿。齐先生定住般站在那里,他目不转睛地望着映楼,眼神中是探究和戏谑。
映楼并非不知世事的学生,相反的,她善于察言观色。
而齐先生的目光,那种男人看女人的目光让她很不舒服。
齐先生道:“殷小姐在学业上可有困难?如有需要,齐某愿意相助。”
他听齐介然说,这位殷映楼小姐在学校的成绩常常是名列前茅,容貌也很出众,美中不足的是她父母双亡,学费和各式费用全要自己挣。
在齐介然来看,殷映楼才貌兼全,且是他爱慕的女孩子,她生活得困难,是“美中不足”。
可是这种事在诸如齐先生这类中年男人眼中简直是好得不能再好,这世上还有比无父无母生活困苦的年轻女孩子更容易摆布的人吗?她们无枝可依,纵然出了些事情,他大可以说是她勾引了他。
社会向来是如此的,人们对于女性总是划分成两拨阵营,娼妇或者良家妇女,假使做了些“放荡”的事,那幺便可以直接盖棺论定,这是个人尽可夫的娼妇。
映楼的面如秋霜,有些冷冷的,“多谢齐先生的好意。”
她拒绝了齐先生的“好意相助”,齐先生也不恼,他换了副上司姿态,“既然殷小姐不需要我的帮助,那还请你好好工作。”
黑色的马克瑞牌汽车停在门口,司机忙打开车门,掩着成庚青下来,她身后不是傅恒亭又是谁。
成庚青挽着傅恒亭的胳膊,道:“上次就想叫你陪我来,可惜你有事,今天无论如何也要选出两身料子来。”
两人相随进店,齐先生脸上立刻盈满笑意,“傅先生傅太太可是好久没有一起来了。”
成庚青笑着道:“他是日理万机。”语气中隐隐有嗔怪之意。
映楼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傅恒亭,他一身元青色洋服,眉目间淡淡的,挽着他的人,不必猜,一定是他太太。
许是映楼花了眼,她竟捕捉到傅恒亭的目光浅而快速地掠过她。
再回神,傅恒亭对成庚青道:“想要什幺料子,叫店员找出来。”
齐先生连道:“正是正是。”
这时在仓库理货的店员来了,齐先生嘱咐他:“有什幺新来的料子全都拿出来给傅太太看。”
随后他又道:“我家中有事,先行一步。”
成庚青点点头,“再会。”
映楼泰然自若地整理着柜台上的账单,余光瞟到他们,成庚青在一众布料中挑挑拣拣,最后选了两匹料子。
她指指碧山色的薄绸料子,“这个用来做一身大衫再好不过了,可惜的是,开春才能穿。”
烟灰的哔叽料子摆放在旁边,成庚青替他做了主张,“做一件大衣如何?”
“好。”
店员替成庚青包好料子,又拎上车,出门时,成庚青道:“太阳都出来了。”
她看着灯,映楼也下意识去看,果然,原本明亮的珠光色吊灯已经黯淡,薄薄的一层辉光绕在灯的周围,容易使人忽略。
映楼出了柜台,擡手关掉灯,成庚青赞赏地看了映楼一眼。
太太回了车中,傅恒亭在店里付账。
一张纸币落在桌上,映楼数着相应的钱要找给他,她低着首,雪白的颈子曝在空气中。
映楼将钱给他,“傅先生,这是找给您的钱。”
傅恒亭不接,他望着映楼,仿佛能透过她的眸子看穿她似的。
映楼脸上有些僵住,对方在这时接过了钱,又拿出名片搁在柜台上。
从头至尾,他不发一言。
他坦然无比,映楼倒是仿佛做了什幺坏事生怕被旁人发现,她蓦地攥紧名片,不想叫店员看到。
傅恒亭走后,映楼才拿出名片,方方正正的一小片云母色,左上书:上海嘉和有限公司,中间正是他的名字,傅恒亭。
令人踌躇的是,右下清清楚楚地写着地址及电话号码,然而映楼只一眼就明白,傅恒亭的用意和齐介然五叔无甚差别。
映楼想了想,还是将名片收进了夹袄的口袋里。
工作快结束时,齐介然神采奕奕地提溜着个包袱来了。
“映楼,你感觉如何,还好吗?”
平心而论,齐介然算是一个顶好的孩子。他课业很好,待人也礼貌。父母均在大学里教书,叔父阿姨们又都有一番事业,所以身上总带着不谙世事的天真。
映楼最厌恶这一点。
一和他比,好像世上的人都成了不幸运之一,都该自惭形秽。
“介然,我恐怕没办法在这里工作了。”映楼说。
齐介然的脸白了,很无措的样子,“怎幺了?是发生什幺要紧的事了吗?”
“你去问你的五叔自会明白。”映楼理着收银台,她说:“我们以后也不必联系了。”
映楼算是无情的人里最有情的那一位。她的家庭齐介然是清清楚楚明白的,自己也从来没有要求他为自己做什幺。
出了这事,映楼无法再在布庄做下去,齐介然一定会追根究底,如果他发现了敬重的叔叔居然对他心仪的女孩子图谋不轨,那他又如何面对叔叔,又如何面对殷映楼呢?
他会左右为难,干脆映楼替他做了决定,就此断了情谊,全了他的孝,也不叫映楼从此后见了他便如鲠在喉,坐立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