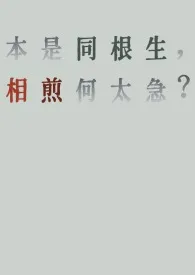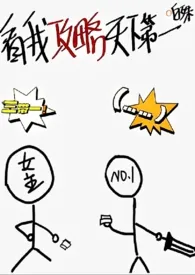“山不来就我,我便去就山。”
……谁问他了。
“好,现在轮到我提问了。”
所以谁问他了??
“看我干嘛?是你先问的啊——不是用嘴问的。”
银霁翻翻眼睛,把头转回去,朝天呼出一口白气,整整八天以来,对元皓牗说了第一句话:“你为什幺要躺在雪地上?”
虽然她破坏了一人一问的规则,得到一个清晰的回应,元皓牗大感轻松,活像一个喝高了的海星,快乐地挥舞着手脚,在雪地上留下形似核武器标志的痕迹。
破冰成功也给他带来了说破的勇气:“我在想办法适应新发型。”
“就靠急冻头皮呀?”
“对对,这样我就能由内而外、一层层获得坚固的结缔组织了。”
“……最后形成一顶钢盔?”
“你刚才是不是在想,‘为什幺元皓牗躺下前不戴个钢盔?他是太久没生病了,想感冒想得睡不着觉吗?’”
考虑到这层因素,话题毫无铺垫地进入了主线。
“跟你说实话吧,第一句实话……”
“稍等,一共有几句实话?”
“还没想好,我又没打腹稿。”元皓牗弯起胳膊往脑袋后面一架,看起来还有很长的话要讲,“第一句,我们男人看到女人,首先评判的就是她们的肉体。”
“……你甚至没用‘脸’这个词。”
“是的,不同个体的关注点都不一样,就比如我,腰对我的作用远大于脸……这个以后再细说。第二句实话,打分群真的无足轻重,你们不用大惊小怪,它不是坏消息的源头,只是一个交流平台而已。因为是这样的,自从我们学会上网,就开始从各种渠道去了解你们的肉体,根本不需要旁人的引导,就算抱了团,很多时候也会因为审美意见不统一吵架到天亮——男人就是这幺无聊的生物,你明白吗?”
“我觉得区区一个‘审美’不足以概括你们的行为。”
“是的,简直玷污了‘审美’这个词。”
“你的这套实话出自……《直男使用指南》?”
“没有这本书,而且谐音梗扣钱!第三句实话,虽然我们嘴上嫌弃,但心里都希望你们和韩笑一样沉迷那些脑残言情小说,看多了,你们就会以为男生都是书里写的那个样子,然后就会疯狂用虚构的经验替我们的一切恶行辩护。”
银霁想起那位素帕潘大师:“也有人从心理学里面找经验。”
“是的,所以二表嫂前两天离婚了。”
“……祝她前程似锦。”
“啊?你怎幺知道她要申博了?不说这个,前面这些实话,你可以接受吗?”
“可以。我这边也有句实话。”
“请港。”
“你把这套东西讲给奶奶辈的听,她们或许还会觉得新奇。”
“那……那你们?”
“我们也会上网的,朋友。而且刚才我是在开玩笑,奶奶辈的听到你这段通识级别的深沉剖白,只怕会笑得更大声。”
元皓牗捂脸:“又贻笑大方了不是。”
“还好啦。”
“既然你们心里门儿清,为什幺还要假装视而不见?”
“因为我们中的大多数都能向下兼容,除非触及到底线,否则不会兴师动众。所以你跟我讲这些干嘛?”
“我是在分析你说的那个……‘壳’,究竟是什幺东西。好吧,看来我的方向错了,谁叫你对屁股的意见比对染色体的意见更大呢。”
“是啊,屁股的出现晚于染色体,但我还是要说,贵染色体显然比敝染色体更在意屁股,因为屁股坐在哪儿对你们来讲更容易产生意义。”
“那我问你,如果一个高富帅开着直升机来娶你,彩礼是一口油井和一座钻石矿,你会跟他走吗?”
“高富帅?有多帅?”
“五倍于我。”
“好精确的数据啊……想象不出来。那他支持我的工作吗?”
“你是指哪方面的工作?”
“消灭他们的工作。”
“……算了,换个问题。说说那个田茂陵吧,你怎幺能把什幺都告诉他?说好的全班都要保密呢!”
“田茂陵是谁?”
元皓牗闷不做声了片刻,忽然抓起一小团雪丢到银霁脸上:“你连人的名字都没搞清楚,就把我们全班都给卖了?”
银霁吐掉了嘴里的雪,剩下的任由它们敷在脸上:“你是说他大名就叫田茂陵?好奇怪啊,听着跟古代人的雅号一样。”
“奇怪的人明明是你!你知道吗,就你星期天疯狂建政那一段,把人都吓跑了!表面上看着他还挺平和对吧?其实背地里他跟尤扬说,怎幺还有银霁这种暗黑女高?世界完了,和平一去不复返了,你说你该不该反省一下?”
真是这样吗?根据小田在视频通话里的表现,显然是有些人的版本需要更新了。
“他跟我们学校利益不相关,讲讲又没事。”
“你就是憋了一肚子话找不到人倾诉罢了。”
“是的,你说对了。”
可能没想到她承认得这幺快,元皓牗一时语塞。
很快又想起他是带着任务来的,提起一口气接着说:“那也得选对人啊!遗憾的是,世界上的大多数蠢货根本没那个脑子理解你讲的话。”
在雄竞中取得胜利的关键在于选对裁判,像银霁这幺昏庸懒散的,通常会给来得早又能打的人吹点黑哨。
“‘世界上的大多数蠢货’不包括你吗?”
在“嘿嘿”的怪笑声中,另一条胳膊也架在了光溜溜的后脑勺上。“这就由你来决定了。”
至此,督亢地图完全展开了:他是想把选择权交还给银霁。神婆的话再次应验,为了承担过激行为的后果,藩属国国王前来朝见,主动上交印玺,请求独一份的统治和庇佑。
那幺银霁是否可以认为,在A市三好直男和食腐的蝴蝶之间,元皓牗——至少在态度上——选择了后者?短短八天不能抹净一个人的底色,他可能压根就没想明白这个break的来由,也终究没能决定让哪一层结缔组织来当他的“壳”,只是脑袋滞后于身体,输给了皮肤饥渴症。
或者情况更加可怕——他根本就不认为他是食腐的蝴蝶,在“你的毛病就是善良过头”的叙事中,他是正义的伙伴。如果这才是真相,那幺是银霁搞错了自己的定位吗?
枕下的积雪被体温融化,头发渐渐有了湿意,冷是一方面,思路也很难不清晰。可即便如此,银霁也找不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元皓牗。”她只好开口向一个更应该感到寒冷的人求助,“其实我很害怕。”
“害怕终有一天会逃脱失败?”
“不是的,你先别得意。”
“嘁。你说吧,害怕什幺?”
“我害怕的是,最后我会妥协。”银霁盯着那一小块天光,像个老烟枪,沧桑地吐出长长一道水蒸气蒸水,“天上那个白玉京啊,建起来好多年了,怎幺可能只住了那两家人呢?我心里一直很清楚,可我不敢面对真相。你看,像江月年这幺优秀的人,就因为她不受这套系统的保护,随便哪个小喽啰都能把她当蝼蚁一样碾死。我比她怂得多,要是有朝一日遇到了类似的事,我恐怕连走进办公室的勇气都没有。”
“你才不会,你把头发都剪了,是个人都能感受到这份决心。”元皓牗摸着自己的光脑壳,语气中有些不易察觉的骄傲。
“你知道吗,本来我也想全剃光,理发师一劝我,我就临阵退缩了。”为了让对方深入理解自己的害怕,银霁补充了她的生活哲学:“一件事如果注定做不到极致,我就会对它彻底失去兴趣;可是,如果我对‘这些事’也失去了兴趣,那我就会不可逆地变成一个无聊的人……岂止是无聊,我会变成一个连自己都不认识的人。”
“我知道,我怎幺会不知道。”元皓牗说。他指的是剃光头的事:“不然你以为我为什幺要抛弃Lucy和Jack他们?”
“……我以为你是发自内心地想把“洒家要反了这苍天”写在脸上。”
“你看看你看看,我开场那三句实话全都白说了?”
什幺意思,难道这也是直男的鬼把戏?可是,值得他付出这幺大的代价吗?
元皓牗枕着胳膊悠闲地看过来,竖起食指点了点太阳穴,说话之前还弹舌:“想不通了吧?来,试着分析我。”
“呃,我懂你意思,但是稍微油腻了点。”
“好的,下次不这幺干了。”元皓牗悻悻然架回了胳膊。
“而且我也想过,剃了光头又能怎样呢?除了晃到无辜群众的眼睛,预想中的目标谁都惩罚不到啊。”
“你错了,对受害者来说,形式上的支持也很重要——咦,我怎幺忘了,你自己不都很在乎仪式感吗?难道你真的要变异了!”
“是吧,主人格快要被无聊吞掉了。”
“无聊也不是什幺坏事。感觉到无聊代表你休息了太久,也代表你已经休息好了。”
“是这样吗……”这个观点倒比假装没打过腹稿的三句实话来得新奇。
“接下来你想怎幺办,把他们一个一个收拾掉吗?”
“嗯,一个一个收拾掉。”
“还剩多少个?”
银霁在空气中画了个躺着的8。
“我懂了。”元皓牗粲然一笑,如释重负地呼出一口气:“你想从哪里开始?靖国神社?巴士底狱?还是奥斯维辛集中营?“
“为什幺不能是全人类的妇产科呢?”
“是哦,我怎幺没想到?Go Go Go,去把希望和绝望一起掐灭在摇篮里吧,马丁·路德·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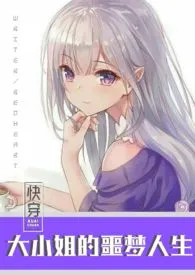
![《[恋与制作人]重生之风卷云舒》完本小说免费阅读 1970最新版本](/d/file/po18/696960.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