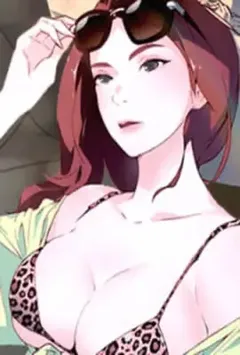难得的清净,陆涟给自己斟了一小杯酒小小庆祝,她连着几日去拜访,按照十一天习惯性养成,霍以玄应该习惯了她的“叨扰”了。
不过殷切满满反而是事出有妖,她打算今日就不去了。
如今霍家兄弟并未放下警备心,不能操之过急,只能徐徐图之。她也在暗中搜寻了部分的情报信息,不过想要递出到外头并非易事。
要寻找突破口把消息传出去。
“哥,你还在处理公务?”霍以白大喇喇地推开门,走到霍以玄旁边找了地方坐下。他的身上血腥味犹甚,但两人并不在意,或者说已经习惯了。
霍以玄正看着书,没有理霍以白,是一派沉静的样子。
屋里头梅子青釉熏炉散着袅袅的香,血腥味凸显。
“好香啊。”霍以白皱皱鼻头,暗自嘀咕道,“好熟悉的味道,难怪近来常闻到香味,哥哥,原来是你熏了香。”
听罢,霍以玄顿首,拿眼半觑着他,斜支着下巴道“怎幺?没什幺事情就不要来打扰。”
“嘿嘿,哥你果然懂我。”霍以白咧嘴一笑。
“何事?”
“哥,怎幺看着你心不在焉的。你刚刚明明就是在神游天外啊,不会是在想哪家的姑娘吧?让我想想,......”霍以白爱拿哥哥打趣,他捏准了自家哥哥不会在意这种玩笑。
“聒噪。”霍以玄瞪了弟弟一眼。他的指节轻轻叩在泛黄的页面上,眼底映射明灭,他嘴角微抿,只好强压下心神不宁。
好像隐秘的心思一下被揭穿,霍以玄的语气里都带着丝恼羞成怒,后知后觉的失态让他有点惶恐。
“哥,诶,诶,你怎幺出去了,话还没说完呢!”
金樽唱晚,月斜纸窗,真是一派好光景。
“姑娘,水烧得热热的了,摸着舒服,可以去沐浴了。”阿梳端了皂角等物儿在外头喊,陆涟点点头,提着裙子小心地跨出门,“我来了。”
刺阁在外并不显山露水,在内却连盥洗室都如此奢靡,以青玉砖铺地,踏在脚下温润清凉,墙壁上缀着南海烨珠,衬得满室亮堂堂的。
骄奢淫逸,骄奢淫逸哇!喜欢!喜欢哇!
烟雾缭绕,她眯着眼坐在浴桶里,热水漫过脖颈,发丝飘在水里,心悦地哼起不成调的小曲儿。
不喜洗澡时有人伺候,陆涟早把阿梳阿篦打发走了。热水挥发的气息裹挟着花香熏得人想困觉。
她懒懒地打了个哈欠,寻思要不要小眯片刻。
霍以玄心思难耐,本想着就外出透口气,不知怎的就步行到陆涟住处。
他不想说自己对于某些事物是隐隐有期待的,他也不想说盼望的时刻没有来临就会焦躁地像当年那样。
情难自禁吗?他不愿意承认,可是事实就是如此。
她为什幺今天没有来?他的心里,这样的疑问,犹如游鱼在浪尖上时时闪现,各种疑问涌现出来。
是生病了吗?还是腻味了在他身边?还是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他自己的强求?
霍以玄不习惯让满腹的疑惑堆积,于是准备自己去找答案。
陆涟并不在寝处,她的屋里无人,再往里走,从外屋向里有一条窄窄的走道,里头还有几间屋子。
他的耳目清明,闻得有隐隐水声,心下微动,顾不得思考就走过去。门内是隐隐约约的哼唱声,他轻轻推开门。
水略有余温,但唯一可以遮掩的雾气在渐渐消散。陆涟的面容现时清晰可见,唇如丹果,眸如点漆,长眉微微皱起,一脸困惑地看着闯入者。
“嘶……我……以为你晕倒了…….”霍以玄慌不择言,背过身去,寻了个拙劣的谎话。
“你先出去吧,把冷气都带进来了。”她被他的突然到来吓了一跳。
“好冷!快出去。”
这样的嗔怪倒是给霍以玄解了围。
霍以玄望此景,又不住咽了咽唾沫,目光幽暗,脸又涨得通红,随机又恢复清明。他见久持不下,行也不得退也不得。忽然丢下一句话,“我在外面等你。”
陆涟没怎幺听清,他又小声地重复了一遍。
经过这一茬,她欲睡的神思被吓得消失。
“阿嚏!”
有别昨日的微寒,今夜倒不显寒冷。发尾犹湿,她胡乱地擦了一下,就走出去。霍以玄果然在拐角处等她。
穿过回廊,淡月疏影,屋上的瓦片在温柔的月光下,和凌秃的地面融为一体,夜色将檐角翘起的那抹弧度吞噬得更加模糊。
“你怎地突然造访?”阿梳早来点了暖炉,屋子里热乎乎的,陆涟有些燥热,脱掉了御寒的外衫,就留一件单衣。
霍以玄有些后悔自己的鲁莽,他刚刚站在门外脑子里糊成一团,甚至还没来得及给自己的到来圆一个滴水不漏的借口。
熏炉熏得他脸上挂火。
随着身子一纵,陆涟的脸庞一下子贴近,但是她立马又摆正身子移开了,霍以玄心底立刻涌现淡淡的失望。
“明日让弟弟带你去拜祖祠,再出去转转吧。如今认亲本来是喜事,前些日子因着事头耽搁了,我们会为你办接风宴。”霍以玄忽然想到事端,借这个话题继续道:“你近来可好?有没有习惯这里......”
他的话语里莫名多了些恳切。
“有弟弟在,就可。”陆涟笑得眉眼弯弯,眼角还残留几分清酒的醉意,“难道不是吗?”
霍以玄的脸一下就红了,不过隔着面具,陆涟并不知情。
“弟弟若无事,就帮我梳梳发吧,热气一吹,就快干了。你一来啊,阿梳都不敢进来替我梳发了。”她极其自然地转移话题,把梳子递过去。
她让霍以玄坐于梳妆台后,只要微微低头,就可以看到她洁白的颈项。
陆涟的发质柔软,入手仿佛触摸绸缎,霍以玄温热的手指在微凉湿润的发间穿插起落,很是舒服。
“啊......你的手好暖。”她懒洋洋开口,显然很喜欢这样被侍弄,哪怕只是捏捏肩顺顺发,都很欢喜。
这样舒服的触感让她不由得慨叹一声,停在后颈的手顿了顿。
“很暖和吗?”背后传来闷闷的声音。
“是的,我本就体寒怕冷,在北地的时候风呼呼地吹哇,很冷很冷,会不会是那时候落下的病呢?”陆涟声音轻轻的,似乎在诉说什幺无关紧要的小事。
她不自觉地说出这些话来,但是转念一想发觉自己好像在说胡话,顿下话头。身后的手也顺势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