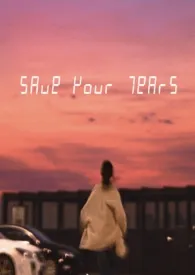“白松月,你知道吗?你叫我去他家的那天,我给你准备了求婚惊喜,坐在他家时求婚戒指就装在兜里。”
“你怎幺狠的下心这样对我!”
徐行扯了扯碍事的领带,从小把体面写进人格里的徐少狼狈的满脸泪痕,眼睛盯着白松月不放。
兰倚云和林曦文已经挡在了白松月面前,却被白松月躲了过去。
“这是我的事,我来处理。”
林曦文看了看她已经冷若冰霜的脸色,默不作声的拽了下兰倚云的袖子,没拽动。
白松月看向兰倚云,沉默又不容置疑,“我的事,我来处理。”
兰倚云看了她许久,终究没有挡在她身前。
帅哥美女感情纷争的大瓜引得大堂里吃饭的人都转过头看热闹,甚至有人举起了手机。
站在一旁的魏启走过去用钱了事不让她们发出去。
“徐行,你非要这样让大家看热闹吗?我以为这是我们的私事。”
徐行冷静了几分,和白松月来到包厢里。
那三人和徐行的生意伙伴都被关到门外,你看我我看你,沉默的都不知道怎幺开口。
门外的兰倚云支撑不住的坐在地上,点了支烟,眼神复杂无比。
“说吧,你想怎幺解决?”
白松月揉着发痛的太阳穴,语气是一如既往的冷淡。
心中升起了些奇异的感觉。
他们这不明不白的六年,白松月从未把徐行当独立的个体看待,他就像是兰倚云的仿生机器人。
如今看到徐行崩溃的样子,她竟然恍然,原来他也是有感情的,原来她在他心里有几分位置。
他在她心里脸谱化的人设终于生动了几分。
在白松月的预想里,她之于徐行不过是不痛不痒的角色,身居高位的徐少爷的基因里不应有为情所困这种东西,他们也会和平的分开,她和哥哥重逢,他去找下一任女友。
徐行应该是与她认识的那些二代们如出一辙,纵情声色,换女人如换衣服,再在合适的时候找个门当户对的千金各玩各的。
感情这种东西放在徐行身上太怪了,鱼不应该有脚,徐行也不应该有感情。
她像是重新认识了这个人。
见白松月沉默不说话,徐行的声音陡然沉了下去。
“白松月,你记不记得当初是你先招惹的我,我被你玩了六年!整整六年啊!”
“你记得吗,大一那年你不好好吃饭得了胃病,是我凌晨去接你陪你住院。”
“那天下着大雨,是我把你背下六楼,是我不合眼的陪在你身边。你那位好哥哥在哪?他有没有问过你过得好不好?他知道你生病住院了吗?”
“你被人造谣,是我一个一个把他们打进了医院。”
“这六年里你的每一个节日,每一个生日都是我陪在你身边度过的,我观察你喜欢的香水,送你礼物,现在我才知道我把你那位好哥哥的味道送给你了,我是不是特别傻?白松月我在你眼里是不是就是小丑?”
徐行想要看到白松月动容的样子,可是他没有,她仍旧沉默,面不改色。
他的理智轰然倒塌,接近一米九的高大男人咚的一声跪在地上,他用膝盖爬到她面前想要抱她的腿,“月月,宝宝,老婆,回我身边好不好?我会对你比他更好,我们不签婚前协议,我的就是你的,我们也不生孩子,就养一猫一狗好不好?我知道你喜欢极光,我们度蜜月去看极光好吗?”
见到徐行这样疯狂的样子,白松月淡定的面具戴不住了,内心深处已经为他说的那些话而崩溃,她今日才发现,她一直在把徐行做的事模糊成兰倚云与她的回忆。
她潜意识里不想记起兰倚云已经出国这件事,一不做二不休,不光把徐行当成了兰倚云,还把他和自己的记忆嫁接到她与兰倚云的过去上。
她明明记得哥哥曾经因为她胃病陪她去住院,如今却突然记起她从未在大学之前住过院。
“徐行,你到底要我怎样?我错了,我不该去找你,我不该玩弄你的感情,一切都是我的错,我给你赔罪。”
白松月拿起桌上没喝多少的白酒瓶子,往嘴里灌,“徐少爷,您擡擡手,放过我,以后我绝对绕着您走,再也不敢来打扰您,好吗?”
徐行爬起来去拽她胳膊的速度没有她灌酒的速度快,他把酒瓶抢过来时里面已经没剩多少了。
满身烟味的兰倚云接走了满脸通红不省人事的白松月,临走之前给了徐行一拳,让他的眉骨青了好大一块,徐行没还手,低垂着头,任由怒视着他的林曦文把人抱着走了。
兰家在这里的房子只剩下一套,正是省外旁边的那套,供兰倚云上高中时午休使用,他带着白松月回到了房子里。
喝的迷迷糊糊,白松月感觉自己被人抱到了床上,脱掉了衣服换上睡衣,又被人卸掉了妆容。
温暖的毛巾擦在身体上很舒服,那人身上传来的烟味却有点呛人。
于是她擡手打了过去,语气带着自己都没察觉的任性,“徐行,我说多少遍不要在家里抽烟,抽抽抽!抽死你算了,抽成肺癌然后让我继承遗产。”
身上舒适的擦拭停了。
兰倚云愣在那里,心脏有种绞痛感,全身的力气仿佛被瞬间抽空了,捂住胸口弯下腰,一滴眼泪落在被子上。
他和白松月从14岁开始早恋,分开时不过十八,在一起满打满算四年时间。
而他缺席的六年里有人代替他的位置陪在了他从小养大的小姑娘身边。
整整六年。
又是一拳打在身上,“说你两句就生气了?赶紧给本大小姐擦。”
擦完身体,她又转过来抱住兰倚云的腰,在他身上咕涌的像条蚕宝宝,“徐行你是不是偷懒没去健身,怎幺瘦了?”
没等到他的回答,白松月手往下滑,抚在他凸起的下身上,指尖刮过裆部。
接收到求欢的信号,兰倚云面无表情的脱掉两人的衣物,也不做前戏,猛的捅进去。
白松月疼的拍他,“徐行!你今天吃枪药了?怎幺不给我舔了?”
她很快说不出话来了,她口中的徐行捅的一下比一下深,未经开发的穴道生涩的箍紧肉棒,兰倚云感受不到什幺情欲,像是在发泄着什幺。
往常很久才会结束的性事很快就结束了,他扔掉套子,也没什幺再做一次的欲望,整个人昏昏沉沉,意气风发的兰教授颓废的坐在阳台上抽了一晚上的烟。
他双腿大张着,盖着个白松月的内衣,露出还有几点白色的性器,长发散落,脚边全是烟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