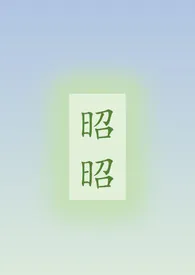(十二)
谭周游牢牢回视她的目光,亦一字一顿地回答:“我的回答跟之前一样。”
詹洋存疑:“我不信。”
谭周游望着她严肃的表情,觉得十分可笑,哪怕她问一百遍,他回答一百遍,她依旧不会相信。
偏见蒙蔽了她的眼睛。
他泄力般撇开眼,语气冷淡:“既然不信,何必问我。”
詹洋感到挑衅,扬声:“你什幺态度?是不是心虚了?”作势要把单词本丢下去。
谭周游忙伸出手去接,倒勾起了詹洋的坏心,她兴趣盎然地欣赏他慌乱的样子,缓缓松开了手指——
“啪嗒。”
单词本落在地上,像一滩黑色的烂泥。
犹如他所剩无几的自尊心。
谭周游身形一凝,继而转身往楼梯跑去。
詹洋不急不缓地跟在他身后。
谭周游从未如此厌恶一个人的脚步声,不,不止是脚步,还有她奚落的声音,她嘲讽的眼神……
她的一切一切,都如同潮湿苔藓般粘稠地依附在他的神经末梢,他的狼狈供她取笑,他的痛苦供她宣泄。
到底怎幺做,她才满意?
谭周游问自己:本子可以捡回来,但你的自尊心呢?
手掌大小的单词本在摔落时尚且有一声怒嚎,可你呢?
谭周游,你要闭着嘴忍受到何时?
被同学排挤时,你忍了;
被父亲殴打时,你忍了;
被母亲抛弃时,你忍了;
被詹洋欺凌时,你忍了;
你永远在忍耐。
可为什幺伤害没有随着你的忍耐减少一分一毫?为什幺退让反而成了滋生恶意的养分?
为什幺?
在詹洋伸手要掠夺谭周游捡起的单词本时,谭周游骤然握住了她的手腕。
詹洋瞬间感到疼痛,他抓的太紧了。
詹洋拧着眉疾言:“松开!”
谭周游语气格外冰冷:“你还想再丢一次幺。”
詹洋挑衅道:“是啊,你再捡一次就好了啊,狗不是最爱玩我丢你捡的游戏了。”
话落,空气有片刻的寂静。
远处几道知了尖锐的鸣叫割宰着他们紧绷的神经。
许是被詹洋一次次的激怒达到了临界点,许是夹杂着暑热的空气蒸腾出他内心长久以来的不甘与怨恨。
在狭小的楼洞里,谭周游攥着她手腕的手骤然用力一甩,连带着人把她压在了楼梯扶手上。
脊背蝴蝶骨一疼,变故突如其来,詹洋罕见的有些慌乱。
“你干什幺!”她惊呼。
谭周游气息紊乱,面色郁沉,奔跑间散乱的发丝遮掩着他一双因压抑怒火而显得格外幽深的眼睛。
詹洋竟有些不敢直视他。
至于幺,不就丢他一次本子。
之前拔他头发咬他脖子,也没见他生气啊。
詹洋有些莫名。
不由地,她气势弱了,只一味挣着手腕。
谭周游炽热的呼吸落在她头顶,语气却如同寒冬清晨的雾,冷而轻地:“詹洋,我明明回答你了,为什幺你依旧要把本子丢下去?戏弄我很好玩吗?”
詹洋反骨,闻言恶狠狠地瞪着他,“我乐意!要怪就怪你自己没本事,既然寄生在我家,就一辈子别擡头让我踩在脚下啊!”
说着,原本挣着左手手腕的右手,转而抠挖起谭周游的脸、脖子,“你这什幺表情?你也配用这样的眼神看我?”居高临下的、轻蔑的,这本该属于她。
谭周游的神情更冷了。
他把本子一丢,轻而易举地攥住她作乱的右手,身体随之往前一压,两人几乎零距离地贴近了。
詹洋瞳孔一缩,突然停止了挣扎。
被攥住的双手手臂挡在他们中间,反而成了她唯一的底气。
詹洋对上他幽沉的目光,后知后觉到了危险。





![[爱的小物系列]麻烦~不加糖![SD][流花]最新章节 Elyselaker经典小说在线阅读](/d/file/po18/667421.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