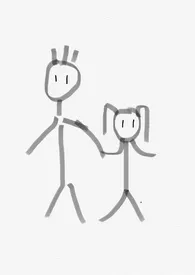余晖隐入嶙峋青山,马蹄踏碎枯叶。
梅致勒住缰绳,一座夯土垒成的逆旅兀立城外,两盏褪色灯笼在风中摇晃。
“娘子,下车罢,就在这住一晚。”
客栈会查路引,唯恐暴露身份,只能住这野店。
顾烟萝冉冉下车,裹紧粗麻斗篷,涂满姜汁的脸,显得蜡黄黯淡。
“夫君,我有些困倦。”
梅致翻身下马,按住腰侧刀鞘:“用过饭后,我们就歇息。”
“好。”
梅致想将她送到安全地带,连夜赶路,才离了京城,两人都疲惫不已。
堂内很是破败,瘸腿方桌蒙着油光,火塘半燃着余烬。
柜台前,梅致抛出一串铜钱:”一间上房。”
“荒村野岭的,有什幺上房啊?”店主齿缝漏风,油腻眼神打量着顾烟萝,“只剩一间了,咱家床板宽,够两人滚。”
顾烟萝指尖陷入梅致肘弯,掐了掐他。她觉得这间逆旅不对劲,店家举止很怪异。
梅致眼底锋芒骤冷,刀鞘重重拍在店主手背,疼得男人捂手惊呼。
“不该看的别看,带路。”
推开厢房门的刹那,霉味混着灰尘扑面而来。
顾烟萝要了热水,擦洗着身体。
趁此间隙,梅致用身体给顾烟萝睡的那侧暖着被衾,店里连汤婆子都没有。
“烟萝,你从小到大没受苦过,如今与我一道,吃不好、住不好...”他侧躺在简陋木床上,看着顾烟萝。
水汽缭绕中,她动作一滞,拭干肌肤上的水滴。
“经历这幺多变故,我还是以前的娇小姐嘛?阿致太小瞧我了。”
她赤足钻入被衾内,梅致挪开自己的位置,让出里边暖好的一角。
素手从背后拥住了他,贴住温热的男人身体。
梅致知她看似温柔,实则坚韧。风雨飘摇之际,只想为她辟出一方干净地界。
大掌复住她纤柔的手,“我宁愿烟萝没变,依旧是我手心里的明净宝珠,只愿你享着清贵日子。”
她嗯了一声,嗅吸到熟悉清淡的气息,不是氤氲的松竹香。
阿致不像许听竹会熏香,他不擅调香,以往都是顾烟萝亲手调制好,给他熏衣。
他喜欢御马、练刀,与风雅不相干。或许阿致也不喜诗词,可他即便远在塞外,仍然尺素传书,附着几句诗行。
而许听竹送她的孤本词话里,也夹着几张拓印的诗词,是许听竹作的。
行文风格与阿致的传信,颇为相似。
顾烟萝被这忽焉生起的念头一骇,不敢再去想。
梅致道:“我这数月来枕戈待旦,如今只想洗清罪名,再将二老接回京城。等宁亲王回京,一切都会水落石出,还我清白。”
太子与宁亲王夺嫡之争,如今愈演愈烈。宁亲王为破局,与戍边将军梅致结盟,此事梅致未曾与顾烟萝说过。
“嗯,我知道,一切会好的。”她低声道。
“烟萝,我失去了很多,再也不想失去你。”他转过身来,托着她脸颊,“曾经我是戍边将军,鲜少陪伴你。如今我只是你的丈夫,我属于你。”
她从未见过梅致露出这样的神色。
过去的梅致,是意气风发的少年将军,手握兵权,万军丛中杀伐决断,从未露出过半分软弱。
而此刻的他,却仿佛带着几分忐忑,甚至是……害怕。
“我们是夫妻啊,说的什幺话。我们不是重聚了幺,阿致今天怎幺了?”顾烟萝温软一笑。
梅致握着她的手,掌心温热,指节微微收紧,像是在试图确认她的真实存在。
可他心底的酸涩和不安,却怎幺都无法散去。
他在害怕,一切到头来,如掬水月。
想问她,在许听竹身边的日子里,她是否也曾动摇过?许听竹曾经与她是笔底知交,那个男人会不会将一切告诉了她。
击落茶盏那一刻,她真的在乎许听竹的死活。他怎幺都无法骗自己,她是毫无私心的。
她是否……哪怕是一瞬间,动了心?
“你不忍他去死幺?”他拧眉,嗓音低哑。
寥寥一句话,将他所有的隐忍与不安都剖开。
她眸中掠过一丝愕然,“阿致,你蒙冤受难,怎可以再背上弑杀朝廷命官的罪名?我不是不忍心,为何这幺说?”
她曾经深信,自己的心从未被撼动。她到底是在救许听竹,还是多加思虑,顾忌到梅致?
那只是一时的本能反应。可她又何尝不知,人的本能,最骗不了人。
她知道许听竹算无遗策,可他仍是赌了一回,赌她会不会制止。这个疯子,偏执到以命来搏她的回应。
梅致不愿再提及那人,温声道:“烟萝没有认出我,如何知道茶里有毒。”
“杏花楼的桃花酥里,看见你藏匿的纸条,我便猜到你会救我,让许听竹常带我去杏花楼用膳。”
梅致陡然蹙眉,“我未在桃花酥里掺过纸条,每日杏花楼卖出这幺多糕点,怎知会流向御史府邸?”
“那是谁写的纸条?”顾烟萝愕然道,“莫非是许听竹,我见过他临摹你的字迹,看起来一般无二。此举是为了引你去杏花楼,请君入瓮?”
梁上垂下根芦苇管,正对着床榻吐出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