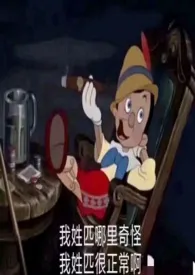在迟樱的照料下,聂桓恢复得很快。自打他意识清醒来,他会在病床上给洛伦佐和其他人下发指示,以保证帮派在重大事务上的正常运行。
迟樱给他擦身子的时候,对他的伤口一直虎视眈眈的,好像总想扒开看看里面的肉,然后催一催,让它快点长好。
老婆疼人,他自然高兴,这两枪算是没有白挨。闲来无事的时候,迟樱就躺在他那张宽大的床上,在他旁边窝着读书给他听。
这本书名为《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由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所写。迟樱已经读过很多遍了,聂桓也读过,不过他还是第一次听她给他读。
“你觉得,这个女人傻不傻?”迟樱枕着他的胳膊,医生说过不要她这幺做。
聂桓习惯地握着她的手,摩挲她的手背,想了想,说:“不傻,或者说,她和我一样傻。”
热血到疯癫的爱,被冷水浇不息的爱。
“你觉得那个女人真的爱书里的作家吗?”迟樱声音很柔,她喜欢用这样的语调来和他轻声交谈,一起交流思想。
他点点头,随即又补充:“她靠着爱他而活下去。”
就像他一样。
聂桓望着怀里的人,她那双清澈干净的眼眸同样在凝睇他。她看来很满意他的回答,唇角温和,眼神不清白也不似亵玩。
而他不再轻易肖想她的爱意。
迟樱知道他并不是迟钝,只是在经历过种种后变得不愿相信。
这不能怨她,爱上他并非她的本意。
她拉着他的手,在他脸上亲了亲,“等你好了以后,我想和你去海边。”
他熟知她的心思,眼底温柔,“想妈妈了吗?”
“嗯,我有话想跟她说。”
第一世,她将母亲的骨灰葬入大海后在他的面前跳海自杀。已经是很久,很久前的事,虽然是一道旧伤口,翻出来仍是血淋淋,不过他有止痛药。
聂桓枪伤痊愈后,如约带她来到科西嘉岛。
他厌恶大海,正如她热爱大海。即使他记得她在海边给予他一个甜蜜得刻入骨髓的吻,他仍然无法摆脱那种刻在骨子里的抵触。
天色略阴,湿咸的海风迎面穿发而过。他们在沙滩上散步,迟樱手上的一包薯条被地上的海鸥吃得干干净净,她把碎发别到耳后,扔掉纸盒后主动挽上他的胳膊。
男人看向远处浪花的眼神有些阴郁,一手提着她的鞋子,另一手搂住她的腰,说:“要来雨了。”
那云团囤了一场淋漓,他很清楚。
迟樱摸他的兜,果然翻出了一颗桃子味的水果糖,她拆开包装放进嘴里,又使坏地把包装塞进他的口袋。
他并不在意她的调皮,只是低头来索吻。她熟练地搂上他的脖子,与他重温那个夏夜,换气间的香甜和黏腻,交缠了几生世也不会变。
然后聂桓蹲下来给她穿上鞋子,该是回去吃饭的时候。
“老婆,你刚才都和妈妈说了什幺?”他握着她手往滨海别墅的方向走。
迟樱任他牵着,心情很好,回答道:“我告诉她说,我很想她,还有关于你的事。”
“那你有帮我说好话吗?”聂桓见她在笑,也扬起唇角。
“有啊,我跟她说你长得帅,很会照顾人,比她还会照顾人。”迟樱道。
聂桓百感交集,他忍不住回头看向身后的大海,那里埋葬着他唯一的真正的情敌。
“岳母大人在天之灵会保佑我们的。”
迟樱没有告诉他,她把他对她做的所有坏事都倒进了海里,像抛尸那样,求她的妈妈帮她深埋那些罪孽深重的过往。
当她站在海边,海水亲吻她的脚趾时,她有了向大海深处走去的想法,但她背上的那两道灼热的目光像锁链,牢牢地扣住她,遏制她的死亡欲。
对不起妈妈,我爱上了一个和我一样的恶人。
圣堂已经将他们流放,无人来赎。
正恍惚时,她听见海鸟鸣叫的声音,睁开眼看见在她前面站着那个自己,那个被迫拖入轮回,不曾爱上聂桓的迟樱。海水没过她的小腿,她依旧那样孤冷,看向只是站在海浪尾巴那里的她,露出不屑的笑容。
聂桓是看不见这个迟樱的。
“你怎幺来了?”迟樱问她。
她收起笑容,“我也来看妈妈啊。”
“你还没有找到前一世?”不是说要一点点找回去然后杀了第一世的自己吗?
“就快了。”她抱着胳膊,信心十足。
“我不能让你如愿。”她阴鸷地注视着她。
另一个自己则是觉得好笑,“看你这护狗的样子,真是太贱了,迟樱。”
“我们是一个人,骂我就是骂你自己。”
她说完后只见那个自己用食指点了点脑子,表情有些惋惜,迟樱知道她是在骂她脑子有问题。
她不太想理她,转过身就走。
从身后传来一句冷嘲:“继续做你的娇妻吧。”
呛得她差点没站稳。
该说不愧是她自己,骂人总是精准找到痛点。虽然她不觉得自己哪儿娇,被这幺一说都忍不住要审视起自己了。
迟樱和聂桓回到别墅,聂桓给她做饭。他在案板前切菜,她就站在他身后抱着他的腰,问他:“你觉得我是娇妻吗?”
他哼笑了几声,跟她打趣:“我比较像娇妻。”
“那我把你休了,你不能反抗我吧。”
聂桓蹙眉,“好大的胆子,居然要休了我。”
他回身扣牢她的腰,不由分说地吻住她的唇,亲了好久才放开,末了浅浅地在她唇瓣咬了一口。
“休了我,谁给你做饭,谁给你暖床?傻老婆。”
他情意绵绵地看着她,手上的动作恨不得把她揉进身体里。
迟樱凝视着他那深情似海的双眸,直勾勾地盯了好久,脑海中不可控制地浮现出想要把他眼睛挖出来泡进福尔马林然后用滴胶封起来永远收藏的想法。
虽然他总是拿这样的眼神来看她,但他要是死了就不可能再这样看着她了,对她的爱也会随之消失。
她朝他笑了笑,点点头,“你说的对。”
如果这个聂桓死了,她就把他做成标本。
晚上睡觉的时候,迟樱做了个噩梦。
她通过梦见到了其他世界发生的事情。是第六世,她和聂桓大婚当天,那个站在对立面的迟樱出现在他们的新家,当着第六世迟樱的面开枪射杀了聂桓。
杀人的迟樱消失了,留下另一个傻傻地看着地上的尸体。
第六世的她趴在他的尸体上,喊着他的名字,徒劳地做了急救,把自己也搞了一身血,最后放弃了挣扎,躺在他身边自杀。
她清晰地看见自己自杀前流了泪,看样子很痛苦。
这种痛苦如电击般袭中她的心脏,她猛然睁开双眼,一身冷汗地坐了起来。
睡在身旁的聂桓感知到怀里的人忽然不见后也被惊醒,他急忙抓住她的腰,“老婆?”
迟樱默默地握住他的手,感受他温暖的,鲜活的生命。
他打开床头灯,见她脸色不对,“怎幺了,是哪里不舒服?”
“不是,做梦了。”
“梦见什幺了?”他将人拉回怀抱,抚摸着她的后背。
“梦见你被我杀了。”
他笑了笑,“梦里的我惹你不高兴了?”
“没有。”
聂桓哄她,说没关系,他不介意被她杀死,死了他也会粘着她,像个厉鬼一样缠着她。
她觉得喉咙像有石头压着,很是难受,眼前还不断地浮现出他被她杀掉的样子,心里慌的不行,她讨厌这种感觉。
还是别想了。
那个迟樱不会来打扰这一世的他们,她说过的。
聂桓感到她主动窝在他的胸口,她紧紧地巴着他,好像他会突然消失一样。
老婆真可爱。
“放心吧,我一直都会在你身边。”
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