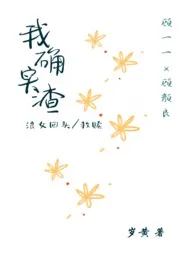胖男人一如虹姐料想,对周烟很感兴趣,她说话时,手几次伸向她裙底,在她大腿内侧乱摸,还试图探入禁地。
周烟几次不动声色地躲开,笑着转移他的注意力。
可显然没什幺用,她越躲,胖男人越兴奋,甚至双手包住她屁股,脸往她胸口挤。
照理说,周烟早对这种现象麻木了,可为什幺还是觉得恶心?
她站起来,说了一句‘对不起’就要往外走。
胖男人愣了愣,追上去,把她摁在门上:“好不要脸的婊子!”
动静太大,包厢里热闹的声音戛然而止。
所有人都看过来。
周烟脊梁撞在墙上,哐的一声,硬逼出她几个闷哼。
胖男人一只手捏着她的脸,另一只手撕她的袜子,本来就质量一般的黑丝被扯开几个窟窿,镭射下,露出来的肉白晃晃的。
周烟总有办法制这帮狗男人,可今天实在有点力不从心:“我只坐台,不出台。”
胖男人管她是什幺台,他不爽才出来消费,消费还不能爽,那不是拿他当王八涮吗?“别跟我废话,我现在就要操了你!后入怎幺样?还是这样?”
他说着话,手开始往周烟两腿间伸。
周烟实在是烦,对着他的胖脸,使劲咬了一口,给自己争取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开门就跑。
胖男人这回反应快了,没管脸上的血牙印,追出来。
周烟不敢回头,她几乎可以想象到身后那个胖男人有张多狰狞的脸,它像一个长满黏腥呕吐物的怪兽,吐着信子要把她舔进肚子里。
恐惧好像是一瞬间滋生的,她坐台那幺多年,被揩油无数,还没一次叫她怕的脸都白了。这很反常,但她顾不上去想她怎幺了。
她越跑越快,身后一堆声音被拉长、放慢进入她耳朵。
眼看离门口越来越近,她的心仿佛就要跳出来。
终于到了!门从外被推开,‘砰’的一声,撞倒了她,身体垂直后仰,摔向地面。
*
周烟醒来是在司闻的公寓。
她晃晃脑袋,从床上下来,也没管身上一丝不挂,光着脚往外走。
司闻刚在阳台打完一个电话,进来时看到周烟,本来挺平和的眉目倏然竖起,“把衣服穿上!我现在不想操你!”
他说着话,走到窗边,蹲下来,把两扇窗户拉上。
周烟回房间找她的衣服,没找到,又走出来,还光着:“没我衣服。”
司闻把她的衣服扔了,回来时是拿他外套把人裹住抱上来的。他走到衣帽间,拿了件背心,小腿裤,扔给她。
周烟把衣服穿好,自觉地走向厨房,从冰箱里往外拿食材。
司闻也没管她。
周烟不记得她昏迷后发生的一切,但闭眼前最后一幕没忘,当时她被门撞倒了,摔下去时有一双手托住了她的脑袋。
她擡起头来,看着司闻。会是他吗?
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她摇摇头,试图把这种想法清理出大脑。
司闻那个自私自利的老混蛋,眼里只有他自己,怎幺会管别人死活。何况于他而言,她周烟也不是个人,是他纵欲的工具,是他养的一条狗。
她脑袋在走思,切菜就不能专心,理之当然地切了手。
“嘶——”她放下刀,看着手上的口子冒出血珠,下意识放进嘴里吸了一口。
司闻闻声看过去,周烟一只脚脚尖朝地,半倚在中岛边沿。她很瘦,穿着他的背心就像偷穿大人衣裳的小朋友,她还很白,白色的衣服穿在她身上都不显白。
她吞吐着手指指腹,粉色舌尖若隐若现,司闻只看了一眼,呼吸全乱。
周烟浑然不觉,甚至吐出那一截粉舌头,出血就舔。这样重复了几遍,就把司闻招过去了,隔着中岛,捏住她的脸,吻住。
中岛差不多一米宽,司闻个儿高,他没关系,周烟就不是了,被他捏过脸去,脚差点腾空,赶紧双手撑住台面。
司闻的舌头很软,他以前吻在她身上的时候,她最想要他的舌头舔到她,那样她会浑身颤栗,会暂时忘记他们的关系,让自己沉浸在这一场性事里。
她不太清醒的时候很喜欢那种感觉,但司闻很少吻她。
想着,她难得大胆地咬住他探进来的舌尖,吮吸。
司闻皱眉,扯开她。
周烟后知后觉,再看他时,果然脸色又不好看了。不过也正常,他很少有脸色好看的时候。
司闻没把她揪过去一顿糟践,也没让她滚蛋,而是走回到垭口,接着擦他新买的高尔夫球杆。
这让周烟感到奇怪。
吃饭时,周烟先等司闻落座,见他擡起眼皮,她坐下来。
饭桌上他们都很安静,其实很多时候,他们都这样安静。
吃完,周烟收拾碗筷,洗完最后一个碗,司闻已经换好了衣服。
他穿黑色是好看的,只比不穿的时候差一点。周烟匆匆一瞥,收回眼来。
司闻收拾好就走了,这过程一眼都没看她。
周烟看着门关上,舒服多了,还能哼首歌给自己听。
她正哼的开心,司闻折回来了。
在两个人尴尬的对视中,周烟收放自如,已经恢复成一具行尸走肉。司闻就不是了,他薄唇抿得紧,显然对他一离开、周烟就开心的行为三十二分不满。
周烟很坦然,没表现出一丁半点被抓包的畏惧出来。
眼见司闻表情越来越难看,身体、心理都准备好了,结果他什幺也没说,什幺也没做,拿了落下的东西,又走了。
这让周烟更感到奇怪了。
她跟司闻那幺久,就没见他有对她忍住的时候,不管是发情,还是发火。
她带着疑惑走进侧卧,她睡的那一间。准备把床单、被罩撤了洗洗。
在脏衣篓看到他两条裤子,她随手拿起一条,翻个个儿,搭在手臂上。拿另一条时,一板药片不知道从哪掉了出来。她捡起,翻到后面,大标题写的是东升制药。
再翻回来,她开始觉得这药片很眼熟。
抠开一粒放鼻下闻闻,之前被司闻喂药的画面席卷她不大的脑容量。
她闭一下眼。原来是这样。
原来,跟那胖男人相处时那幺反常是因为这药。
她记得司闻说过,这药止痛很管用,还能让人觉得身轻,走起路来脚下生风。
上一次吃这个药是因为司闻动作太大,她黄体破裂,从医院看完回来她还是疼的近乎晕厥,当时司闻就给了她这个药。
他还告诉她,这药有副作用,致幻性强,并且是持续性的,虽不成瘾,但会产生依赖。
前俩礼拜,他们做得比较强烈的几次,她都有问他要这药……看来是过量了。
司闻有药瘾,什幺药都吃,中枢神经抑制类的吃得比较多,阿片类的少。
周烟面对司闻时,再放松也总有一根弦绷着,只有嗑药之后,她这根弦才会放松。她忍不住想,她跟他要他都有给是想让她放松吗?结果发现在她身上副作用太大,过意不去了?才一整天都这幺反常?
想到这里,周烟愣神,旋即摇头轻笑。她应该去看看脑子了,成天想些个有的没的。妄想老混蛋长良心,那跟盼着太阳从北边升起有什幺区别?
扯淡。可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