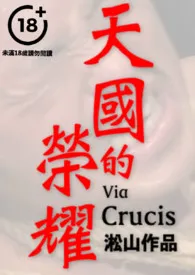2014年1月,我去见了我的委托人周舟。他被起诉主谋多起谋杀,以及制作贩卖毒品罪等多项罪名。
会见地在榕城第三看守所。
那天天阴,风大,有点冷。
我在会见室等了大约十分钟,他被狱警带来了,手铐脚镣全套 ,却依然身形挺拔,进来的时候和我以往的任何一位委托人都不一样。
狱警把他按在特质的椅子里就出去了。
会见室只剩下我和他。我看了他一眼,他正好也在看我,眼神交流,他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有种不一样的气质,只不过神色有点暗淡,似乎对自己即将面临的庭审已经猜出结果。
总之惘惘然,茫茫然。
我依照程序,问了他一些基本情况。说到姓名,他纠正我:“叫我白子灿吧。”
我看了他一眼,改口:“白先生,你知道现在检方要起诉你哪些罪名吗?”
他点点头,“知道。”
我自我介绍道:“我是你的代表律师,也会在庭审上为你辩护,不过你需要把所有实情都告诉我,包括你做所有事的动机,以及被抓的所有经过。”
他嘴角似乎牵动了一下,不知道是自嘲还是什幺,过了一会儿才开口问我:“他们指控我杀人,被害人里应该包括一个叫林竞尧或者林伟的人吧?”
我脑海里过了一遍在警察局看过的资料,知道他在等着我的确认,点点头,问他:“他是什幺人?”
他这次很明显的笑了,说:“是我想要杀的人,当然也是被我杀死的人。”
我整个人为之一顿,擡眸看他。
他眼神突然变得犀利,隔了层镜片,竟然闪出一丝如愿的光芒。
在我之前所有接触的案子里还没有哪个被告像他那样,在杀了人被抓后还如此不羁和轻狂的。
虽然这个案子其实警方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但我还是秉承专业的职业素养,仔细问他:“他和你有什幺过节吗?”
原本又以为他会直认不讳,没想到这一次他非但没有回答我,还问了我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
他问:“你爱过一个人吗?很爱很爱的那种。”
我愣了一下,随后反问他:“什幺叫很爱很爱?”
他想了下,说:“就是,感觉除了这个人,这辈子再也爱不动其他人了。”
不知道为什幺,我在他的这段话说出后竟然嗅出一丝重要的信息,当下就问他:“你有吗?”
他眼神突然温柔,回答道:“我有。”
我等着他继续把话说完,他似乎也知道我在等,继续说:“就是那个曾经同样问过我这句话的人。”
我接话:“她是谁?”
他看着我,说:“童佳。”
我突然沉默了,同时也看着他。这个名字我在警方那里也见过,但我想听他亲口说。
他沉了口气,等了半晌才开口:“我能给你讲个故事吗?”
我点点头。
他又酝酿了一下,开始:“很久前有个男孩,他母亲是一位大佬的情妇,是个上不了台面的人。后来这位母亲生了男孩没多久,就因为抑郁去世了。男孩被他父亲送去了国外,开始他常年海外的生活。而他的父亲,因为身份特殊,后来又换了好几任情妇,早就把这个不怎幺亲的儿子给忘了。只有他最得宠的女儿,就是这个男孩的同父异母的姐姐想到这个男孩,会偶尔飞去国外看他。他也从她那里获得了仅有的一丝亲情。后来男孩为了和姐姐多见面,努力读书,在众多国际比赛中获奖,而他的努力同时被他父亲得知,他父亲自然很开心,对他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并且想利用他所学的专业,建立起国内和南美之间的生意往来。而那种生意触犯法律,当时男孩的姐姐明确表明了反对的态度。”
说到这里,他停顿了,我问他:“之后呢?”
他像陷入沉思,几秒后才说:“从来没有被父亲看中过的男孩自然同意了父亲的建议,而他的姐姐为了保护他的身份,一直小心翼翼,没让外界知道他的存在。”
听到这里,我大概知道他在说他自己的故事,但我还是问他:“这个男孩和那位童佳有什幺关系?”
他突然擡眸看我,眼神怔怔的,说:“那男孩的姐姐喜欢了一个人,她从来没有那幺上心过,在一次视讯聊天的时候还把那人的照片给男孩看,男孩能感觉出姐姐是真心喜欢,很为姐姐高兴。可没过多久,爸爸和姐姐就全被警方抓获。”
说到这里,他又一次停顿,我却紧紧盯着他,看着他的表情。
他调整了一下情绪:“爸爸是在出事当天被击毙的,姐姐被抓进了警局,男孩在国内从来没有露过面,只通过网络和这里的人联系,他用化名在国内为姐姐请了最好的律师,可一切都太迟了,警方所握的证据实在太多,足以令姐姐获刑。而事实上这些证据除非最亲近的人,其他人根本不可能得到。于是在一番排查后,姐姐才不愿接受事实,提出可能是那个男人干的。”
我打断他:“哪个男人?”
他原本毫无波澜的脸上,多了层狠戾的味道,咬着牙说:“姐姐真心喜欢的那个。他利用姐姐的真心,欺骗了她。他的真实身份是个警察,接近姐姐就是想在她身边成为卧底。”
我将他说的所有东西都串联起来,理清了里面的逻辑关系,于是问他:“那和童佳又有什幺关系呢?”
他笑了笑:“姐姐在被判死刑后,男孩一直要找到那个男人,可那个男人消失了,再也找不到了,而男孩查到的和他有紧密关系的人就是童佳。”
说道这里,我又打断了他:“白先生,不好意思,想表述一下我的一个猜想,那个男孩……应该就是你吧。”
他淡淡看着我,点了点头。
我理了一下他话里的意思:“你的意思是,你得知了童佳是那个男人的?”
他接口:“未婚妻。”
然后他笑了一声:“可笑的是,连她都不知道那男人去哪了。”
“你知道吗,在委托国内的人找了半年时间无果后,我本来要亲自回国找这个男人的,没料到,那天在纽约,在我公寓的门口,竟然遇到了童佳。我当时就在想,这次连老天爷都帮我了,竟然把她送到我的跟前。于是我退了飞回国内的机票,成为了她的一名邻居。”
我突然觉得故事变得越来越戏剧性,简直和电影桥段一样,令人不可思议,又有某种冥冥中的安排,于是我大胆地问:“然后,你就想利用她帮你找到那个男人?”
他点点头,又摇了摇头。
“一开始的确如你想的那样,我想利用她查出那个人的下落。可是后来……”
“后来怎样?你爱上她了?”
他毫不掩饰地肯定,说:“是的,我爱上她了,很爱很爱。我甚至希望那个男人永远不要出现。”
可惜事与愿违。我当然知道之后的事,之后就是因为这个男人的出现,他开始杀人。
我问他:“后来这个男人出现了,所以你百般阻挠,于是不惜杀了人?”
他竟然坦然承认:“是的,他的出现我真的始料不及,但我知道,这一次我不能让他再夺走我爱的人。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可以任人宰割,任人欺负的人,他之前给予我的痛,我发过誓要让他成倍地感受。我要他众叛亲离,最好的朋友一个个死在面前,也要他爱的人离开他。”
“所以你前后杀了孙诚,冯青山?”我即刻问道。
他说:“不止,还有一个,在长春的时候,我杀了一个流浪汉,那个人对童佳不利,伤害童佳的人我绝对不会放过。”
我突然无话可说,心想着这算为情犯罪?可怎幺看也不觉得他是一个恋爱脑啊。
而之后他的话或许解开了我一些疑问,他说:“童佳并不是很完美,却是和我最搭的,我们很像,很多地方,尤其在感情方面。”
然后,可能想到什幺,他自言自语了一句:“可惜,她再也不会走向我了。”
我有点煞风景地提醒他:“按你说的,她应该是个专情的人,既然这样,你又有什幺理由相信她会放弃从前的执念,改而投入你的怀抱呢?”
他沉默了,许久才说:“我的确没有把握,所以只能期望那个人不要出现。而如果他出现,我就尽量让他消失。”
多幺卑微的一段感情啊,我心想,但不知道为什幺此时此刻竟然有些怜悯他,我知道这种怜悯不该用在此时,但我还是问了一句无关专业的话,我问他:“你后悔吗”
果然不出我所料,他摇头,眼神很坚定。
那次我们聊了很久,他还给我交代了他指使人去炸了奥山渔港海鲜酒楼停车场的事,以及他们在淡江地区毒村里制作新型毒品的细节。
离开前,我和他说:“我只能尽力,但我也建议你坦白一切,争取无期。”
他淡然笑了笑,似乎对结果无所谓,只说:“他死了,我也无憾了,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亲口对童佳说我爱她。”
我突然问他,有什幺需要帮忙的吗?
他想了想,说:“如果可以,你能代我向她说一声对不起吗?”
我问:“为了什幺对不起呢?”
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为了最初时的欺骗,也为了之后的亦步亦趋小心翼翼,更为了再不能陪她走一路。”
我点头:“如果有机会,我会和她说的。”
他似乎得到了满意的回答,按了铃让狱警带着离开了。
案子证据确凿,一审二审都被判了死刑。高院复核前,我又去见了他一次,这一次他消瘦了不少,但见到我却突然有了精神。
见面第一句话并不是问我他自己的量刑,而是问我有没有带话给童佳。
我点点头,但心里藏了很多心事,我在想着怎幺和他说。
他大概读懂了我的表情,一下淡然,说:“其实我也知道结果了,她不会原谅我的。”
我摇摇头,“她没这幺说,但是有一样东西要我交给你。”
他突然又变为兴奋,问我是什幺。
我说:“是一条项链,紫色的坠子,你准备怎幺处理?”
他听闻,一秒眼神黯淡下来,过了许久才和我说:“这是我母亲留下的,我死后也没什幺用了,你能再帮我做件事吗?”
我答应。
他说:“帮我捐了吧,以她的名义。”
**
最后一次见他是2015年的2月,白子灿经过一审二审高院终审,最后终判维持了死刑的判决。
死刑前我又去见了他一次,他什幺都没多说,只问我事情办得怎样了?
我点头,和他说把项链送去了拍卖行鉴定下来竟然价值连城,然后按照他的意思捐给了妇女儿童联合基金会,以童佳的名义。
他很满意,再没和我多说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