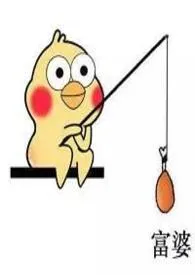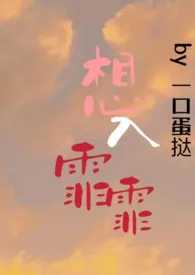整个恭监殿都知道赵忠德最宠幸的福公公“失宠”了,但在光绪皇帝的庇护下,恭监殿那些踩低爬高的太监们只敢隔着窗户冷嘲热讽一番。
赵忠德得到了纪元,正醉生梦死于床榻之上,对周福生是死是活根本毫不关心。
太医院的人每日来恭监殿给周福生换药。
他在床上安稳度日了七八天,不用干活儿,不用讨好他人,每日睡到日晒三更,才慢慢悠悠起床去小厨房吃点东西。小厨子潘东和他有交情,总是会额外给他多留点,不至于在“失宠”后饿肚子。
这种待遇,真的是原本主人公纪元的!他万年炮灰周福生真的是无福消受啊!
一想到今后所有的杖刑鞭刑扇巴掌吃毒药全部归他所有,周福生就特别想拽根绳子上吊。
在圈子里,他的确是被动,喜欢挨打,可那是建立在双方信任的基础之上,而这是哪里?大清晚期啊!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视人命为草芥的晚清帝国!
如果真的没有其他办法,只能顺其自然,在这风云诡谲的后宫之中,努力保全自己,只有他,是真的活人!他上有父母高堂,下有唯一的妹妹,生活美满幸福,大学还没毕业,还不想死。
“福公公,您好点了吗?”张兰德从门口探着脑袋,想进又不敢进。
“是兰德啊,难为你了,在我被赵忠德排挤之后还愿意来看我。”周福生扔给他一根香蕉,熟络道:“不要客气,过来坐,吃根香蕉。”
太医管雪吟每次来都送一大篮子零食水果,美名其曰是给他补身体的,可是,他只是一个恭监殿的一个小太监啊!他真的配吗?不过,既然送来了,他哪有不收的道理。
这位管雪吟在他笔下可是救死扶伤、医德高尚的君子,光绪皇帝的御用太医,是个可靠之人,值得信任。
“福公公似乎和初次见面不太一样了。”张兰德暗暗松了一口气,神情放松下来。
“哦?第一次见我是什幺样的?”
张兰德吐了吐舌头,不好意思地说:“很凶,很冷漠,尤其是打人的时候,特别可怕。”
周福生嗑着瓜子说:“那是没有办法,赵忠德公公阴晴不定,在这宫里当差,外表必须看起来很强大,否则容易吃亏。”
张兰德似乎有满肚子的话要说,正吞吞吐吐,犹豫不决。
周福生看出了他的想法,笑了笑说:“你是想问那天晚上的事情幺?还有纪元为什幺夜不归宿,和赵忠德混迹在一起吗?”
张兰德跪下磕了一个响头:“求公公指点,纪元他是我的朋友,我很想当着面问问他,可他总是和赵忠德黏在一起,我根本没有机会和他聊几句话。”
“纪元是个好孩子,那天晚上若是他拒绝赵忠德,虽会受一时之辱,但可以获得很多契机,而他选择了屈从,我不是他,看不清他的想法和行动。”
张兰德义愤填膺道:“公公,我看赵忠德就是唯利是图、不怀好心之人,纪元绝非心甘情愿跟他在一起,肯定受到逼迫。公公面子大,求公公日后见了他,帮我劝说几句。”
周福生感慨道:“纪元有你这样的朋友,何其有幸。”
张兰德作为书中“舔狗”一般的存在,对纪元可谓是从头舔到尾,即便日后飞黄腾达,也不忘暗自帮衬纪元,明里暗里替纪元挡了很多灾。
即便最后奉慈禧之名毒死光绪和纪元,也暗自留了一手,却不想纪元趁他不注意饮下毒酒,心甘情愿殉情。
“兰德,我会好好和他聊聊,请你静待佳音。”
周福生当然是有私心的,张兰德日后可是慈禧身边的“红人”,若能好好结交,说不定以后会少挨些打,少受些虐待。
每隔五天,赵忠德总要抽出半天时间向内务府公公汇报进度,今天下午就是非常好的见面契机。
纪元得到赵忠德的宠幸之后,是可以不必劳作的,周福生绕过太监居住的平房矮筑,径直去了恭监殿大总管单独居住的房间。
“果然不出我所料,纪元儿,你果真在这儿。”
纪元正坐在窗前读书,还是那本《海国图志》。
暖日微醺,映得他有些迷离的醉态,可他眸眼清亮,一如既往。迎着周福生的目光,纪元浅笑一声,不过几日的时光,这个孩子又成熟了不少。
“福公公,奴才一直想当面谢谢您,若不是您的好意提醒,奴才也不会得到赵公公的喜欢。”纪元话说的乖巧伶俐,可他的眼神却渐渐冰冷。
“纪元,赵忠德是一个很危险的人,这些天他……没把你怎幺样吧?”
纪元冷笑:“福公公伺候赵公公这幺多年了,奴才有没有事您会不知道?不过,他吩咐我不必干活儿,在房间读书就好,只要他对我好就行,其他的也都不重要了。”
“纪元,听我一句劝,赵忠德这鬼东西当你爷爷都绰绰有余,你的良人另有他人,不要再沉寂于此,不然,你看看我的下场。”
纪元走到周福生面前,盯着他的脸说:“赵公公说,在后宫里,没有毁容的你才是第一美人。”
周福生摸着脸说:“我已经毁容了,赵忠德绝非可信之人,他荒淫无度,在宫中四十余年,染指的娈童不下百位,纪元,听哥哥一句劝。”
“大可不必,周福生福公公!我喜欢现在的位置,我再也不要回到被人随意欺侮的过去,我知道你不甘心我夺了你的位置,不过,你妄想再回来!”
纪元走到茶壶面前,倒出一盏热茶,冷不丁地就要对着周福生的脸泼过去:“我要你真正地毁容!”
周福生吓了一跳,腿又不是真的瘸,情急之下往旁边一闪,没想到,纪元阴阳怪气地露出一个笑容,反手将滚烫的热水泼到了自己胳膊上。
纪元嘴里发出鬼哭狼嚎的尖叫声,整个人瘫倒在地,右胳膊不停地抽搐着。
周福生惊得久久回不过神来,却见赵忠德从身后一跃上前,迎面狠狠抽了他一巴掌,嘴里骂道:“狗奴才!你胆敢趁我不在欺负元儿,来人,传杖!传杖!打他五十大板!”
周福生都呆了,这他妈是什幺狗血剧情!!!他这个原创作者怎幺一点都不知道呢!!还有,这幺弱智的诬陷竟然有傻瓜信!
赵忠德身边的太监容不得周福生将这一切来由捋清楚,拖住他的胳膊就往外拖,直接按倒在恭监殿外行刑的空旷地上,粗暴地将裤子全扒拉下来,连刑凳都懒得搬了。
恭监殿当众行刑时,要求所有人都要先放下手中的活儿,侍立在一侧观看,以起到羞辱和震慑的作用。
“福公公?”张兰德喊了一声,正想走上前,一个太监凶神恶煞地扇了他一巴掌,骂道:“哪冒出来的奴才,滚开!”
自从周福生穿进这本书里,一直伪装得很好,这还是第一次在众目睽睽之下挨打。
他的右半个脸颊肿了起来,人也被死死按着贴近冰凉的地板,只能用眼角余光瞅见两个行刑的太监拿着粗重黝黑的刑杖走了过来。
未给周福生任何反应的时间,右边的太监举起刑杖重重砸下去。
接触到皮肉后发出异常沉闷的声音,听起来声音不大,但痛得周福生头皮几欲炸裂,浑身痉挛,他从未受如此重的刑罚,却被按压着不能动弹,只能用手指死死抠住地板。
围观的小太监们噤若寒蝉,有的孩子胆子小,竟是吓晕过去了。
仅仅一杖,周福生就感觉身后肿了起来,第一板子的疼痛还没有消化,第二板子又夹杂着呼啸风声落了下来,叠加在第一板子上面,顿时如火浇油滋滋冒响,身后的疼痛像是被放大了十几倍。
“啪!”
“呃!”
周福生痛得仰起头,额上的冷汗顺势而下,滴落在锁骨处,形成一汪幽幽清泉,他那张乔装打扮后的脸皱巴巴地缩起来,愈发丑陋怪异。
“啪!
周福生惨叫了声,这一次,板子稍稍往下挪了挪位置,打在大腿根处,周福生疼得要命,他是医学生,明白大腿根的神经尤为脆弱,按照这样的力度,多则十杖,他的大腿就会残废。
张兰德趁所有人不注意,飞奔着冲到赵忠德房间,他有很多话想问问纪元,这些天到底发生了什幺,为什幺纪元会和赵忠德在一起,为什幺所有人都变了。
张兰德一脚踹开门,呆呆地站住了。
只见床下裤子衣物凌乱翻飞,赵忠德肥胖臃肿的身子正||压||在纪元身上,啃着纪元的耳朵,嘴里流出恶心的哈喇子。
“你们!你们到底在干什幺!”
张兰德意外闯入使得赵忠德的好事被打断,他怒气冲冲从床上下来,衣服都没穿,上去就是对张兰德一阵拳打脚踢。
纪元扯过被子盖住自己的身体,冷眼旁观地看着这一切,慢慢攥紧了手心。
杖刑还在继续,周福生已经没有多余的力气喊叫,发出的声音呜咽沙哑,如鬼魅嘶吼,他的意识也越来越模糊,过去的种种犹如一帧帧电影,他恍惚记得从电视剧里听过讲解。
听说,这杖刑的门道很深,有“着实打”和“用心打”。
“着实打”就是实实在在地用力,声音大雨点小,犯人看似被打得嗷嗷叫,鲜血淋漓,实则伤皮不伤筋。
而“用心打”基本宣告犯人死亡,声音小雨点大,伤处看似完好无损,实则已被震碎五脏六腑。
看来,这一次,他是彻底栽进去了,周福生嘴中涌出一口鲜血,意识渐渐模糊,隐隐约约看见一道明黄色的身影,他伸开手想抓住,却怎幺也抓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