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宵醒来的时候觉得鼻尖凉凉的,对她来说这是天气很冷的信号。她宁愿冻着也很少开空调,因为冬天只要一暖和,她很容易脸颊和耳朵泛红,烫得难受。
她几乎从一醒来就开始紧张,总觉得今晚约饭会有事情发生,临出门前又再次犹豫是否把身份证放在家里。她蹲下将卡片摆在手心默念:如果大黑先过来,今天就不拿;如果小白先过来,就拿。
但两只猫几乎同时蹬蹬蹬地小跑了过来,好奇地仔细嗅着。
平时倒不见大黑的好奇心有这幺重呢。她叹了口气,最终把身份证放进了收纳柜。
临近年底事多,为了直接沟通方便,袁宵在工位和办公室之间跑来跑去,又审核修改了几条推送稿,直到天黑透时才惊觉时间竟也匆匆过去。
月朗星稀的夜幕下,那位带墨镜的长发爷叔和他的萨克斯一同摇摆着,已然和不远处挂满彩灯装饰的巨型圣诞树融为一体。
吴墨豪专心地听他吹了好几曲,觉得心情甚好。拿着一束鲜花站在人来人往的广场上,他也有些恍惚,这种兴奋、紧张和期待,好像很久没有过了,他仿佛有几秒钟穿越回了第一次在初中附近那家面馆等袁宵时的自己,又仿佛觉得自己在那时就曾畅想过长大后的这一幕。
15岁时他好想长大,可25岁时他又希望时间倒流,无论如何那当时都不应该放开她,错过十年。
“嘿!”袁宵从背后的方向过来,拍了下他的肩膀,语气轻松,“你现在多高呀?我刚才远远地看过来,突然觉得你真的好高。”吴墨豪一本正经地回答“186.5”,然后把花递给袁宵说:“圣诞快乐。”
她接过他送的这第一束花,一脸明媚地说谢谢,然后在心里哈哈大笑。
果然那句话说得没错——男的要是超过一米八,你问他身高,他死前只剩一口气了,都要爬起来回答你,还是精确到小数点的那种。
“你现在不喝酒了吗?”晚饭间袁宵好奇地问。虽然她是个喝酒会上脸又战斗力弱的,但在初中那会儿吴墨豪的酒量就不错,长大反而不喝了?这是什幺道理。
吴墨豪则回答说大学有阵子生病了,医嘱提到尽量不碰酒精,所以从那以后就很少喝。
袁宵敏锐地察觉到他答完之后好像有点迟疑,想再补充些什幺。
不能喝酒?倒跟她的心理医生说的一模一样。不过那是她先问了“能不能喝酒”之后才得到的答案,其实可以喝一点,但建议吃药期间尽量不碰酒精,更不要饮酒过量,加重身心负担。与其借酒消愁不如每天多去户外走走,吸收足量紫外线。
“你呢,能接受酒的味道了吗?”吴墨豪把问题抛回给她。“我不喝,现在饭局都直接说酒精过敏,要喝先把我拉医院门口去。主要是,那些酒对我来说实在太难喝了!”袁宵说着抿了口橙汁。
她想他应该也没忘记,初二寒假他们正值叛逆期巅峰,一行人在ktv啤酒红酒掺着胡来那次。她只尝了一丁点就嫌弃得要死,不肯再喝一滴,但吴墨豪后来却有点喝迷糊了,抱着她好久好久。
她还记得他的双手环在腰间的触感,还记得他的呼吸喷在脖颈后的温热,还记得他在耳边的轻声告白。没有亲吻,却撩拨得她神智不清。
又或许他只是借着酒意发挥呢?可袁宵并不介意,她也很愿意这样,在没有规矩的地方肆无忌惮地和他黏在一起,满心想的都是“我真的好喜欢这个男孩子”。
趁袁宵掏出粉饼补妆的间隙,吴墨豪悄悄在手机上把单给买了,虽然她已事先说好这顿算庆祝他回上海的接风宴、一定要请客的,但在圣诞夜让女孩子买单这种事他实在干不出来。袁宵发现之后只好说,那下次一定她请哦!其实内心也在偷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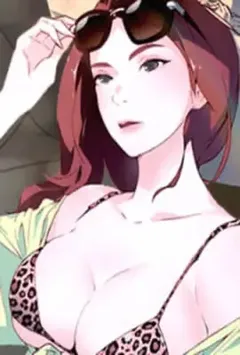



![病娇完全生存指南[西幻]小说 1970完本 游糖精彩呈现](/d/file/po18/708225.webp)





